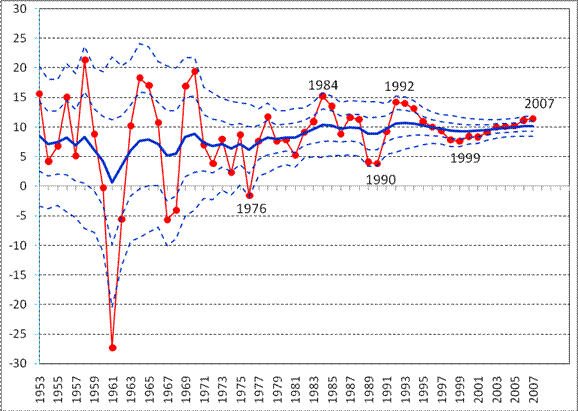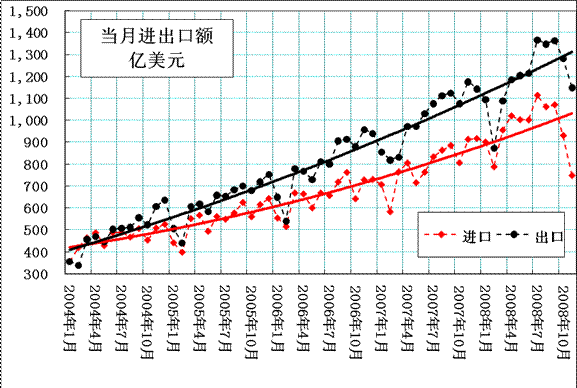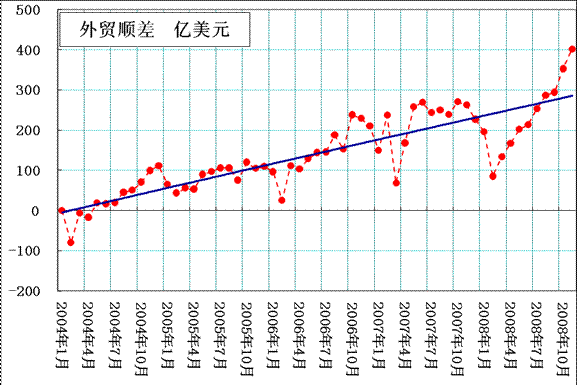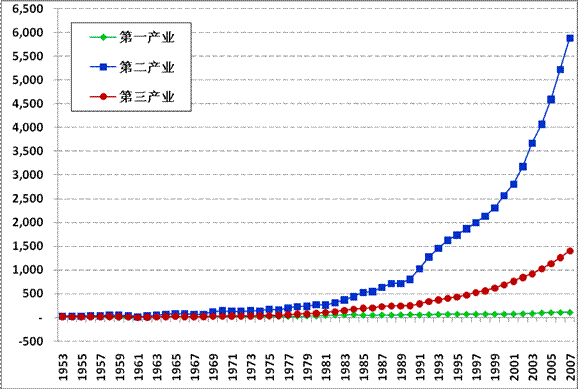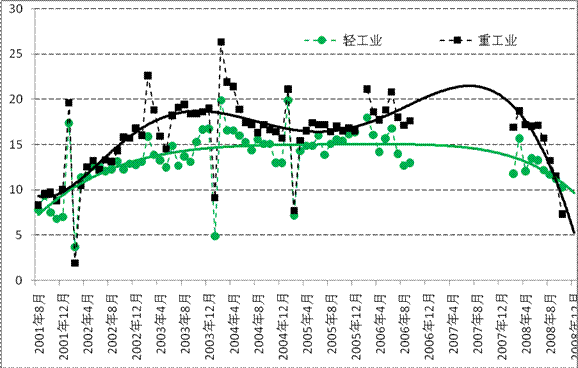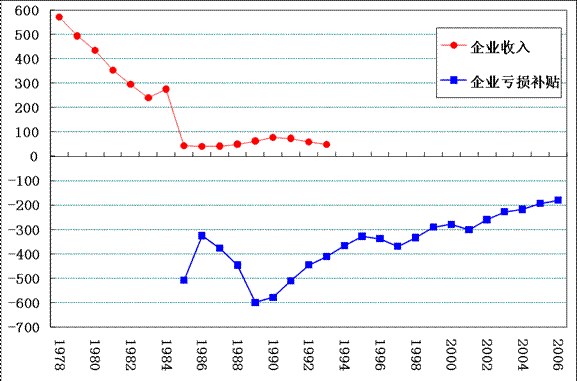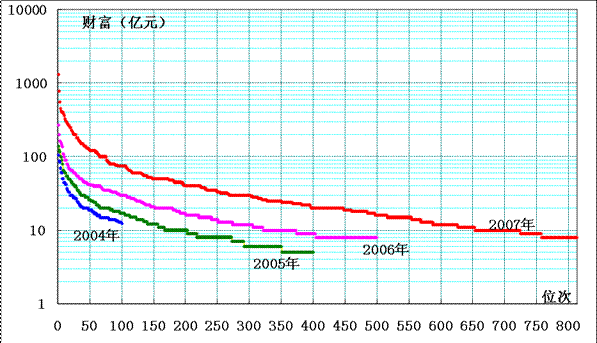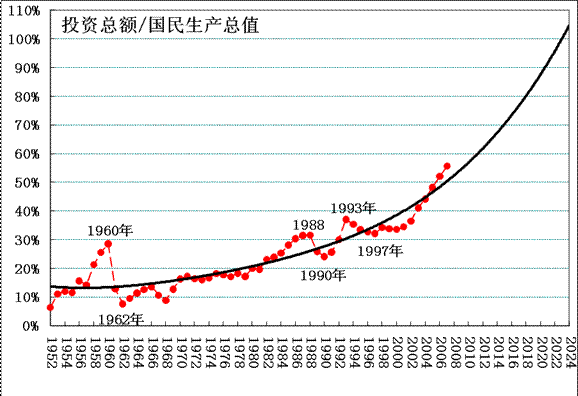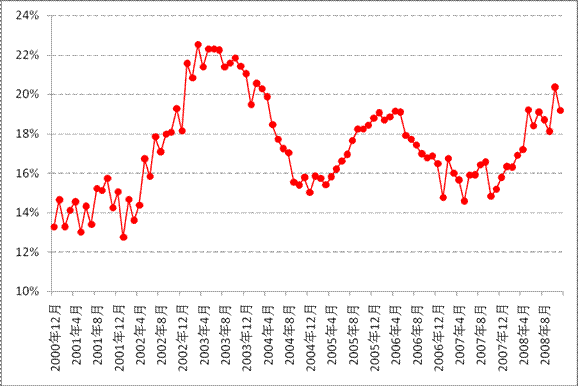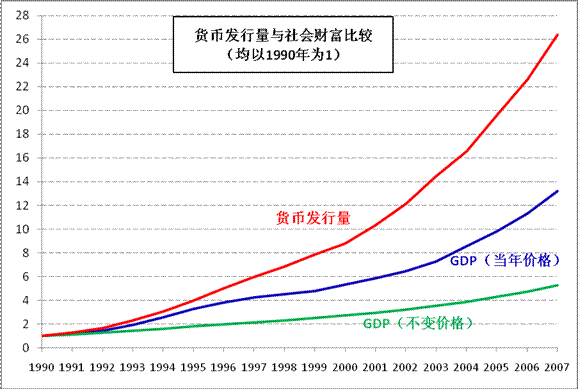直面現實還是諱疾忌醫—金融海嘯中的選擇
王中宇
金融海嘯洶洶而來,最先感到實質性壓力的是工業。2008年12月12日,組建不久的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在國務院新聞辦的訪談中列舉了大量統計數據,指出:
“工業增長速度直線下滑,現在還看不到拐點,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然而,2008年12月05日深圳晚報報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與深圳市政協委員座談時稱:
“來勢洶洶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影響基本已至谷底了。”
他還指出:
“危機中蘊含著機遇,中國企業如能抓住機遇,就能在經濟危機的陰云中找到陽光。”
筆者向一位專業經濟學者請教,中國處境如何?他告訴我:圈內觀點不一,但多數人不太擔憂,很多人視其為機遇,思考中國如何利用它獲得發展。
“三角形整理”與“突破”
如果觀察建國以來的經濟增長率,似乎可以佐證經濟學界這種樂觀的看法(見圖一)。
圖一:中國GDP增長率
數據顯示,建國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持續保持在高位,除個別時段外,GDP增長率波動的平衡位置大多在7-10%之間,90年代以來,更保持在10%附近。一個大國,如此長期地保持這樣高的增長率,舉世罕見。另一個顯著的特征是:GDP增長率的波動明顯收縮,顯示經濟運行日趨穩健。1997年朱镕基提出“保八”,當時波動通道的下沿為7.15%,而歷史經驗表明,當GDP增長率接近通道上沿后一定會下行到通道下沿附近,據此,筆者曾質疑“保八”不可行,實際上后來的谷底為7.6%(1999年)。2007年,GDP增長率再次接近通道上沿,而此時的通道下沿為8.44%,由此似可判斷:此輪“保八”有把握。
金融海嘯對中國的最大威脅是出口,因為中國經濟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度太高。然而海關總局的數據暗示我們,問題似乎不大。直到2008年11月,出口數據仍沒有明顯脫離上升軌道的正常波動范圍,倒是進口數據下滑更明顯(見圖二)。
圖二:進出口月度數據
與之相應,今年外貿順差逐月擴大(見圖三)
圖三:外貿順差
然而,注意到進口構成的變化,就令人憂慮了。2007年,進口總額中,與加工貿易相關的各項(進料加工貿易、來料加工裝配貿易、保稅區倉儲轉口貨物、保稅倉庫進出境貨物、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投資進口的設備/物品、租賃貿易、出口加工區進口設備、加工貿易進口設備)等占整個進口金額的54.3%,可見進口的絕大部分是為出口服務的。2008年1至11月,這個比例降到48.5%,在進口總量下降的背景下,這意味著為出口而發生的進口大幅下降。換而言之,進口下降是出口下降的前兆。
事實上,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長率為9.9%,從圖一中去年的上沿附近直接跌到了的波動平衡位置(10.18%)以下,表明生產已經大幅下降了。
從三次產業的角度看,第二產業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見圖四)。
圖四:三次產業對GDP年增長的貢獻(億元.1952年價)
在第二產業的產值中,工業占到絕對多數(建國以來,平均份額為88.8%)。統計局從2001年8月起逐月對社會公布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見圖五)。
圖五:當月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同月增長率
令人不解的是,統計局網站中空缺了2006年10月到2008年1月的數據。筆者只能用多項式擬合統計數據,由此大體揣測這一時段數據可能的范圍。數據顯示,這一輪經濟周期,其頂點可能在2007年8月左右,而進入今年以來,工業增加值增長率急速下行,到10月已低于整條趨勢線的最低值。
從輕、重工業角度看,本輪經濟周期以重工業領跑,而今年重工業的跌幅遠大于輕工業,且顯出“M頂”的形態(見圖六)。
圖六:當月輕、重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同月增長率
從訂單→原材料進口→生產→出口的流程看,出口下降最后對海外市場萎縮做出反應,由此可以預期,出口數據大幅下降還在后邊。
回到圖一,50--60年代,GDP最高增長率21.3%(1958)年,最低增長率-27.3%(1961年),波幅高達48.6%。此后,70年代、80年代逐步縮小。轉向“與國際接軌”后,全面學習西方的管理體制與手段,到90年代波幅降至10.8%,進入本世紀后,到2007年為止,最大波幅為3%,整個圖一顯現出“三角形整理”且走到頂端的態勢。
有證券市場經驗的人都知道“三角形整理”。當數據波動幅度漸次收縮,最后指向一個頂點時,意味著極有可能發生“突破”。“突破”意味著以前決定數據波動的機制失效,新的機制將取而代之。這時的關鍵是判斷突破的方向,即新機制的性質。數據短期內如此急劇下降,似乎在暗示,向下突破的可能性遠大于向上突破。
從機制看“突破”方向
那么歷史上決定中國經濟運行的核心機制是什么?
圖二顯示,建國以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始終是第二產業,這提示我們:工業化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回顧歷史,是西方列強用戰爭逼迫中國選擇工業化道路的,無論是晚清的洋務運動、國民政府的戰時經濟體制還是毛澤東時代的三線建設,其背后都是嚴酷的國際環境。
在一個人口眾多、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實現工業化,資源何來?在毛澤東時代,一方面靠剪刀差從國民的絕大多數--農民手中聚集,一方面靠低工資降低工業建設的成本。而改革開放后,吸引外商、招商引資成了各級政府的要務,將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寄望于外部資本家。
于是無論是當年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還是后來的“與國際接軌”階段,積累工業化資金都是經濟主管當局的首要目標。當轉向“與國際接軌”后,統計數據證和大量事實證實了資本利潤極大化是中國經濟體系最核心的要素配置機制(見王中宇《利潤極大化與滯脹》科學時報2007年12月30日 五、六版)。而資本利潤極大化必然導致產能與社會購買力的失衡。于是自1998年起,“有效需求不足”成了令經濟管理當局頭痛的頑癥。
在古典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利潤極大化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方才導致無法克服的社會矛盾。而在中國,經濟運行機制基本完成“與國際接軌”應是1994-1998年間(見王中宇《宏觀調控:向左轉?向右轉?》科學時報 2008年9月2日 2版)。卻在短短十余年間各種典型的矛盾就集中、大規模出現,根源何在?
中西方是從不同的出發點走上工商文明的,西方學者將中國的傳統社會稱為“東方專制主義”,馬克思曾用“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原始共產主義”描述東方的傳統社會,翻譯《資本論》的王亞南則寫了《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從秦漢到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分析了中國官僚政治發生與演變的歷程及其系統動態。
從歷史上看,行政權力獨大,官僚體系一家通吃是我們社會的悠久傳統,它最大的特征是高效,因為它不受其他力量的有效制衡,可以自由揮灑。這種高效在歷史上表現出鮮明的兩面性:當官僚體系中理想主義占主流地位時,它可以相對廉潔,從而高效地實現主政者的目標;而當官僚體系中個人經濟理性占主流地位時,各級官員可以高效地實現自己的私利。
觀察過去十余年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性經濟人”是如何把持政策選擇,為利潤極大化原則“保駕護航”的。
企業視角:推動資本向大型壟斷企業集中
承包、優化組合;抓大放小、做大做強;提高產業集中度,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動資本向大企業集中,向少數人集中。貴族化的金融體系靠行政權力壟斷了從儲蓄到的投資通道,而它只熱衷于向大型壟斷企業注資,連理論上定位于農村的農業銀行都是如此。《中國農業銀行2005年年度報告》告訴我們:
中國農業銀行“貸款主要投向”是:能源石化、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重點優勢行業。其“積極營銷和拓展”的對象是“系統性、集團性客戶、跨國公司、事業法人客戶以及重點優質項目”。其重點關注的客戶有: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華潤集團等優質集團性客戶,各大電力公司、電網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聯合通信集團公司、首鋼總公司等優質集團性客戶,以及福建、重慶、大連等省市政府。
在“做大做強”和“抓大放小”戰略思想推動下,國有寡頭企業憑借壟斷優勢發育迅速。
在《中國統計年鑒.1991》中還被稱為“全民所有”的企業,到了《中國統計年鑒.1994》中就改稱“國有”了。可見“國有”取代“全民所有”不早于1992年、不晚于1994年。
“全民所有”至少在名義上要對全體人民負責,而“國有”則是政府內部事務,與“全民”無干。于是社會看到地方國有企業被大量轉化為有官方背景人士的私營企業。而央企一方面靠行政權力聚集巨量資源,以“做大作強”;一方面在“現代企業制度”的旗號下,讓馬明哲們合法獲取6000萬元年薪;一方面將大量員工拋向社會,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從1994年起,國有企業未向財政提交一毛錢的利潤,而從1985年起,就一直從財政領取大量的“虧損補貼”(見圖七)。財政的錢來自“全民”,而“國企”的利潤又流向了何方?
圖七:財政與國企的經濟關系
被“國有”拋棄了的“全民”,只好就業于中小企業和個體戶,而它們在各衙門的嚴厲管制下,動輒得咎。以至于民諺云“十幾個大蓋帽,管一個破草帽”。貴族化的正規金融系統根本看不上這些草根,而草根金融卻得不到合法的生存空間,于是中小企業和個體戶只能靠“內源融資”和“地下金融”艱難地謀求生存。
這樣的政策傾向使資本向大型企業集中,資源和權力向大型企業的管理層集中。廣大國民賴以為生的中小企業只好自生自滅。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告訴我們:
“國家工商總局前幾年發布的一組數據表明,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凈減少81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35萬戶。另外一項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間,全國有770萬家個體戶消失。”
而靠此為生的“全民”,其工資收入正是社會購買力的基礎。
地域視角:推動資源向中心城市集中
區域傾斜、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限制“低素質人口”、創建“**城市”(這**會隨時變化、與時俱進,諸如“數字化”、“國際化”、“學習型”、“衛生”、“文明”、“綠色”、“宜居”……)。其核心作用是使資本向大城市集中。
從全國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獲得的資源遠超過各地,促成這些地方志得意滿地提出:“率先實現現代化”。隨著這些城市的超前發展,人口大量向這些城市聚集,導致這些城市的兩會年年討論“控制人口規模”、“限制低素質人口”。這些城市的“現代化”場景,使有能力影響到國家決策的群體,誤以為這就是整個國家的面貌,從而誤導國家的公共事務決策,因為這個群體主要住在這些城市中。
上行下效,各省紛紛將提高省會城市的“首位度”作為發展戰略,從自己的管轄范圍內,向省會聚斂資源。盛極一時的“市管縣”改革,讓各地的城市都有了可以搜刮的地盤,以至于被基層譏之為“市刮縣”。
中心城市脫離國情、國力的超前發展,在觀察者眼前展現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
一個與歐美不遑多讓,形象工程與政府建筑之奢豪(同時難免粗俗)傲視全球。今年四川抗震救災中,成都新的行政辦公中心曝光,舉國國嘩然(見圖八)。
一個凋敝敗落,污染遍地,學校等公共建筑弱不禁風。即便“天子腳下”的 “直隸”,類似圖九的景觀也隨處可見。
圖八:從衛星照片上看成都新行政辦公中心
來源:GoogleEaerh
圖九:河北石津灌渠一景
當年的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曾感嘆:“城市建設得像歐洲,農村發展得像非洲”。問題在于,“非洲”才是大背景,“歐洲”不過是這背景上的一塊塊“飛地”,而飛地上的人們卻以“主流”社會自居,控制著國家的輿論和公共事務決策。
社會視角:推動資本向富裕群體集中
多年來,“親商”成了各級政府自覺的政策選擇,甚至“親”到官商不分,官商一體的地步。“政策優惠”、“劃撥”、“特事特辦”、“三零政策”(以零資產、零稅賦、零地價吸引客商),讓前官員化身的商人,以極低的代價將大量名義上的公共資源轉化為現實的私有財產,并立法保護之,稱之為“產權明晰”。另一方面,減員增效、拉開收入差距則讓多數國民為之付出代價。
結果是國民中的少數人口依賴行政權力,聚集大量資產,以實現利潤極大化;而導致多數人口缺乏基本的生產資料。在我們數千年的古籍中,有兩個詞匯描述這一過程--“聚斂”、“兼并”,這歷來被視為國家的亂源。這種聚斂的效率有多高?看看歷年的胡潤榜就知道了(見圖十),請注意:圖中表征財富的縱坐標是對數坐標,相鄰兩條主刻度線間差一個數量級。
圖十:歷年胡潤富豪榜
事實上,胡潤的調查線索主要來自上市公司的公開報表,而許多富豪的財富見不得光。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干部和家屬財產、收入申報機制胎死腹中,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有太多的高官,其擁有的財富無法面對社會公眾。可見聚斂的真實效率只能比圖十顯示的更高。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聚斂起來的財富統統需要進行投資、以追逐利潤。以前,學界曾將投資饑渴歸之為計劃經濟的頑癥。事實證明,在“主流”經濟中,投資饑渴遠超過“接軌”前。進入本世紀后,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的飆升速度遠超出任何歷史時期,在2007年,國民創造財富的55.65%轉化為固定資產投資,追逐著未來的利潤(見圖十一)。這個比值的平衡位置顯示出持續的加速上升態勢,如果這個大趨勢不轉變,十六年后(2023年),全部GDP都得轉化為投資,而留給社會消費的份額將趨于零!這樣的經濟系統可能運行下去嗎?
圖十一: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
然而投資長期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出口萎縮的前景下,更是不得不依賴投資。于是我們很可能看到經濟繼續沿圖十一展示的趨勢發展,直到無以為繼之時。
為什么無法啟動內需呢?
啟動內需在邏輯上唯一可能的出路是降低投資份額,增加消費份額。然而經濟系統一次分配的現實決定了工薪所得過低,而資本(以國有資本為主、民間資本中又以外資為主)所得過高。資本所得的本能是轉化為投資。工薪所得中,高收入者所得過多,低收入者所得過少。高收入者的收入,相當部分渴望轉化為資本,以獲取未來的利潤。社會成員的絕大多數是低收入者,他們所得之低,使其客觀需求的大部分不可能成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就是整個社會“內需不足”的根源。
只要一次分配的這個格局不改變,投資高速增長而內需疲弱的趨勢就不可能改變。有人冀望于政府的二次分配,然而這只能被“理性經濟人”(他們充斥于行政機構內外)當作最現實的發財機會。凡是由政府部門發放資金的事項,必定有政府內外相互配合,以各種冠冕堂皇的說詞套取資金的事件,此類個案不勝枚舉,圈內盡人皆知。其宏觀效果是:政府發放的資金大量轉化為新的資本,而本擬救助的對象所得無幾。
這樣的系統運行機制難于應對海外市場萎縮,于是向下“突破”的幾率遠大于維持原有運行狀態的幾率。而一旦發生向下“突破”,“保八”就成了泡影。
揚湯止沸的“救市方略”
質而言之,當前的困境源于強勢官本位系統追逐的利潤極大化原則。它心目中的“發展”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將國民創造的社會財富轉化為追逐未來利潤的資本;而國民的發展從來就不曾是它的真實目標。由此方可理解高速增長的GDP與國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間強烈的反差。
面對金融海嘯,各國紛紛求助于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的本質是向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額外的貨幣。當年羅斯福應對“大蕭條”的措施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是遏制資本積累的速度,包括:要求資本家們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實行以資產占有量為稅基的累進稅、嚴格限制金融機構經營范圍;其二是增進社會公眾的有效需求,包括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力促中小企業的復興、大興公共工程。
2008年8月19日,摩根大通(亞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龔方雄在他的一份報告中披露,中國高層領導人正在考慮一個2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2008年11月5日,中央政府推出4萬億投資的兩年經濟振興計劃,比龔方雄披露的高出一個數量級。4萬億相當于2007年GDP的16.2%,2006年財政收入的103.2%,力度之大舉世震驚。
現就職于世界銀行的林毅夫表示:
“中國4萬億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計劃有助于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到8%~9%的水平,這就是中國為全球經濟能做出的最大的貢獻。”
從媒體報道看,這四萬億指向三個方面:
其一:增加居民收入,減輕居民負擔,包括:
1、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糧食最低收購價格,提高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等標準,增加農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體等社保對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農村低保補助,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和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
2、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加快中西部農村初中校舍改造,推進中西部地區特殊教育學校和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
3、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對廉租住房建設支持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實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擴大農村危房改造試點。
其二:公共工程,包括:
1、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建設一批客運專線、煤運通道項目和西部干線鐵路,完善高速公路網,安排中西部干線機場和支線機場建設,加快城市電網改造。
2、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強重點防護林和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建設,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
3、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農村公路建設力度,完善農村電網,加快南水北調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加強大型灌區節水改造。加大扶貧開發力度。
4、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
其三:支持企業,促進轉型,包括:
1、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鼓勵企業技術改造,減輕企業負擔1200億元。
2、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支持高技術產業化建設和產業技術進步,支持服務業發展。
為此,要求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加大對重點工程、“三農”、中小企業和技術改造、兼并重組的信貸支持,有針對性地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
第一個方向針對不足的有效需求,無疑是正確的。此次金融海嘯中,不少國家和地區由政府直接向居民發放“消費券”,直指要害。然而這種“補貼”性的支出能否解決經濟體系根本機制造成的問題,值得懷疑。最有可能的是,它能救急于一時,將矛盾推到以后。另外需要指出:對其中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當地部分民眾和生態學者、文化學者持有強烈的異議,宜謹慎行事。
第二個方向從長遠看為國家發展所需,但它能否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值得懷疑。投入工程的資金中,行政體系勢必吸收一部分,工程最后由企業實施,企業必定要首先確保自己的利潤,最后才可能是工資。只要經濟系統運行機制依舊,這三部分的分配格局就不可能改變,而正是這種分配格局導致了今天的困境。大型工程中,單位投入創造的就業機會是很有限的,而它卻有超強的能力創造富豪。事實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就采取過由政府舉國債大搞工程的對策。正是這期間,中國的兩極分化急劇拉大,產能與購買力嚴重失衡,造成了今天這種難以處置的局面。
第三個方向本質上是政府與企業間的利益調整。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相當熱衷。既有站在企業立場上希望壓縮政府在經濟領域活動空間的,也有站在政府立場上要求控制經濟命脈的。這種爭論的背后往往摻雜著“主義”之爭。然而從整個社會的視角觀察,這不過是精英集團內部的勢力范圍之爭而已,根本不涉及問題的癥結--社會公眾疲弱的購買力。理論界還有相當多的聲音將希望寄托于技術升級和創新。事實上,導致今天困局的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經濟運行機制問題。在市場不景氣的環境下,企業最理性的行為是窖藏現金(無論來自那個渠道)以備過冬,而非投入前景莫測、風險極大的技術改造。從全世界看,今天的技術水平遠超過的1929年,卻發生了與之類似的危機。可見指望技術發展能解決經濟運行機制造成的問題,無異于緣木求魚。
從問題癥結的角度看,只有第一個方向對癥,可能生短期救急之效;第二個方向利弊參半、弊大于利;第三個方向基本不對癥。注意:當年羅斯福從遏制資本積累的速度和增進社會公眾的有效需求兩個角度下手。而今我們完全沒有遏制資本積累的速度的舉措,相反卻為加速資本積累打開新的渠道。由此可感受到,在社會公共事務決策上,特殊利益集團影響力之巨大。這種揚湯止沸的藥方,療效可想而知。
心猿意馬的“流動性”
這三個方向的措施需要巨量的資金,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財政收入肯定會受到巨大的影響,政府支出的錢從哪里來?
12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創造適度寬松的貨幣信貸環境,以高于GDP增長與物價上漲之和約3至4個百分點的增長幅度作為2009年貨幣供應總量目標,爭取全年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7%左右。
這一政策的背后是相信貨幣發行量能影響經濟增長,希望用多發貨幣帶動疲弱的經濟。然而,這一期望卻得不到事實的支持。圖十二是貨幣發行總量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關系對比。數據顯示,在1999年之前,兩者間存在某種同步關系,而此后基本上是各走各的。相關性分析表明,1999年之前,GDP 增長率與貨幣發行量增長率的相關系數為0.9587(不變價格)、0.9189(當年價格);而此后GDP 增長率與貨幣發行量增長率的相關系數降為0.1295(不變價格)、0.3391(當年價格)。
圖十二:貨幣發行總量增長率與GDP增長率
這暗示我們,貨幣總量已經不再是經濟增長的制約性因素,靠控制貨幣總量來調控經濟速度已經不現實。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對“流動性過剩”極度憂慮,決定2008年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以防止通貨膨脹。而事實上,整個2008年貨幣發行總量一改2006年5月以來的增幅下降趨勢,轉而上升(見圖十三),而經濟增速卻明顯下滑。
圖十三:貨幣發行總量年增幅
理論界爭論“流動性過剩”已有多年,至今未見明確結論,連什么是“流動性”都眾說紛紜。經濟現實告訴我們,社會上并不缺少貨幣,貨幣發行量已經遠遠超出了社會生產的財富。貨幣發行量不僅遠超過了以不變價格計算的真實財富,也明顯超過了以當年價格計算的、不斷“注水”后的財富。而且,這種“超越”的速度進入本世紀后明顯加快(圖十四)。
圖十四:貨幣發行量與社會財富比較
問題的癥結在于,大量的貨幣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他們的目標是“以錢生錢”,以獲取“財產性收入”,而這種收入最終建立在商業利潤的基礎上。商業利潤依賴社會購買力,即不是指望利潤而是滿足消費需求的貨幣,而這類貨幣已經遠不能滿足期望獲得利潤的貨幣的胃口。
于是食利者群體的心態成了決定經濟速度的關鍵因素。
當他們判斷有可能掙得利潤時,勢必蜂擁而出,將資金投向一切他們看中的方向,這就是我們在2004—2007年間看到的“流動性過剩”。理論界則在這種需求的驅動下,論證投資優于儲備貨幣,手持貨幣無異于坐等貶值(見高善文《貨幣過剩與資產重估》中國市場出版社)。
反之,當他們嗅到嚴冬的味道時,立刻轉而信奉“現金為王”,緊攥錢包,準備貓冬,同時大叫“受不了了”,以博取社會的關注和政府的補貼,至少要也降低其承擔的基本社會義務(如工資、稅賦支出)。
于是經濟體系的宏觀管理本質上是與食利者群體的心態博弈。古人云“心猿意馬”,在真實利潤空間與利潤需求量之間嚴重失衡的環境下,食利者群體的心態勢必高度不穩定,在“貪婪”與“恐懼”間跳躍,他們已經讓全社會在短短一年內體驗到了什么叫“冰火兩重天”。
大量超額發行貨幣,是為了讓他們重拾信心。當前,中國30%-40%的產能直接依賴海外市場,二十余年的經濟進程形成的這一局面不可能在數年內轉變。于是我們看到,源自外部的金融海嘯,正好撞上了中國經濟體系的“阿里基斯之踵”。只要這些產能放空,食利者群體追逐的利潤就成了無源之水,其信心如何恢復?
而一旦他們的信心恢復,這些超額發行的貨幣勢必成為新一輪通脹的巨大推力,那時宏觀經濟管理班子勢必體驗到比200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更嚴峻的通脹壓力。
9月14日,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稱:美國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言下之意,當前的麻煩,其程度不次于1929年美國的“大蕭條”。而當年的“大蕭條”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了將近半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
我們經濟系統的深層問題以前可能難于認識,而今統計數據和經濟現實已經將其凸顯出來。為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現在是直面現實,嚴謹、客觀、深入地開展研究的時候了。
(注:文中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人民銀行網站、海關總署網站)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