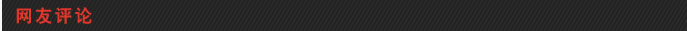胡新民:基辛格為何激動得手發抖?

“余于尼克松訪華之后,得機返大陸探母,從南到北之大小干部,無不歌誦‘偉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聞之實不勝悲楚。蓋余深知該次中美關系之回旋,全出于狡猾之尼克松,一手之安排。北京之聯合國席次,全系尼大總統之恩賜,毛氏得之而不臉紅,還大吹其‘不稱霸’,亦誠厚顏之甚矣。”----摘自唐德剛《晚清七十年》
1971年6月2日晚,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在白宮會見外賓,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來,交給他兩頁打字紙,說,這是剛由巴基斯坦外交郵袋帶來的,是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拉利趕著送過來的。基辛格太激動了,當時手都在發抖。這便是他們正在焦急等待的周恩來發給尼克松的回信,信是用第三人稱寫的:
周恩來總理認真地研究了尼克松總統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興地將尼克松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諸位領導人舉行直接交談一事報告了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表示歡迎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并且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好與總統閣下進行直接交談,自由地提出各自關心的主要問題。不言而喻,首先要解決中美之間的關鍵問題,也就是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的具體辦法問題。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作為與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議的美方代表,提前來華為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北京做準備工作并進行必要的安排。……周恩來總理熱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來北京的會晤。
這是一個讓人期待已久的信息,它標志著中美兩國領導人兩年以來精心澆灌的和解之花終于吐出了花蕾。這時候,不管是久經政壇的尼克松,還是經綸滿腹的基辛格,都無法抑制內心巨大的喜悅和自得。“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基辛格不無夸大地評價道,尼克松則對基辛格說:“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樣,晚飯后從不喝酒,并且時間很晚了。但是我認為這次我們應該破一下例……”他從私人小廚房里拿出一瓶從未打開過的陳年白蘭地酒,舉杯道:“讓我們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們可能會由于我們所采取的行動而有了更好的機會過上和平的生活。”
這個消息確實來之不易!難怪基辛格都激動得手在發抖。
新中國成立后,不但美國自己采取了敵視新中國的態度,并且還對北約國家和英聯邦國家,繼續盡一切可能施加影響:“非共產黨國家現在不必急于考慮承認(新中國)”這種局面實際上已早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美國當時最關心的是印度和英國這兩個國家的態度。印度是中國的近鄰,是亞洲第二大國,它在亞洲民族主義國家中的影響不可低估;英國是美國的頭號盟友,是英聯邦國家的盟主。但是,美國的如意算盤很快就被打破了。印度成了第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其首任駐新中國大使潘尼迦先生是原來駐中華民國大使,當時印度的報刊就有一幅漫畫:潘尼迦先生全身涂著紅漆站在南京的馬路上歡迎解放軍打著腰鼓進城。但最值得一提的還是英國問題,筆者在《撒切爾夫人、蔣介石與毛澤東》一文中已有詳述。簡言之,就是毛澤東早在1946年就謀劃如何用好香港這個棋子,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華包圍封鎖。歷史也證明了這是一個有遠見的布局。接下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盡管經歷了艱難曲折,中共執政也犯了一些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不管怎樣,新中國不但“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見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現在社會上有些人一談到新中國的前29年,就只著眼那段歷史中的消極方面,似乎新社會是一片黑暗,中國(大陸)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不過章伯鈞等人也一度承認新中國的成就是累累碩果------可參見拙文《真實的反右 深刻的教訓》)。似乎當年舉國上下的奮發圖強艱苦奮斗的建設新社會和新國家那些激動人心的往事沒有發生過一樣,似乎全國就是在搞一個接著一個的運動,就是整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黎民百姓也飽受苦難煎熬。似乎真的就象臺灣當局1962年發布的呼吁書所言:“(大陸中共)逞兇肆暴,人民被淪為奴隸牛馬,都要在黑暗地獄和饑餓死亡線上度日”。他們也不想一想,如果沒有新中國成立后的舉世矚目社會治理和國家建設成就,美國會有后來的對華態度的變化嗎?!當然,中美關系的變化的發展還有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即中美蘇三國各自的戰略考慮。但絕對不能忘記的是,二戰期間美英蘇又是怎樣對待它們的盟友中華民國的呢? “甚至富蘭克林.羅斯福通過在各國國會為中國建立‘大國’地位來試圖迎合美國人對局勢需要的努力”,“也沒有消除蔣介石被怠慢的感覺”(見哈羅德《美國的中國形象》)。“中國雖為同盟國之一,命運依然由強國決定。”(見臺灣著名史學家、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還是這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他的兒子小羅斯福在談到嚴重侵犯中國利益和主權的《雅爾塔協定》時指出,“盡管羅斯福在與斯大林談判時一再表示他不能代表中國人說話,但事實上卻扮演了越俎代庖的角色。”為什么頭上頂著“四強”“五強”的中華民國還這樣無可奈何飽受委屈?原因很簡單,那時的中國是一個積弱積貧的舊中國,“弱國無外交”的普世價值還是很適用的。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中國的某些人仍然就是“想不通”這個問題,就是要堅持新中國的前二十九年,特別是1957-1976年,是“罄竹難書”的年代。這樣的人怎樣認為是他們的獨立之思想言論之自由。但是就在1957年后不久,作為那時,也是現在的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卻不是這樣認為的。當然,其它的西方國家比美國的認識就更深刻一些,比如法國,就不在此文中詳述。總之,新中國成立后的直至改革開放前的成就,同樣也是舉世矚目的,因為她那時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
從1950年代未開始,面對新中國的不斷強大,美國社會上開始出現了一種要求改變美國僵硬的對華政策的思潮。這種思潮的比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臺的《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美國康侖公司研究報告》,后來被簡稱為《康侖報告》。《康侖報告》在有關中國和對華政策的分析中指出,美國應該確認兩個基本事實,其一是中國的政權是穩固的,而不是像當時許多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報告稱“大部分跡象表明,現政府是近代中國歷來最堅強、最團結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國作戰,中國共產黨政府長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迅速增長,“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紀后期作為一個主要世界強國而出現”(此預見比較靠譜---筆者注)。所以報告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不管具體形式怎樣”,都應該根據上述“假設來實施”。
在隨后的歲月里,美國終于不斷加深了對新中國發展的認識。當時的一些研究報告也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關于中國經濟,當時公認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系教授亞歷山大.艾克斯坦(Alexader.Eckstein)在“大躍進”、三年困難和蘇聯撤走專家之后寫出報告。他詳細研究、分析了中國自1949年建國以來的成敗得失,發展的動力和模式,每次變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對外經濟關系的情況等等,得出的結論是:總的說來,中國已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足以保證高生產、高收入和高消費,卻足以維持其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保持能在亞洲推行其“野心”的軍事力量。總之沒有任何根據足以支持中國經濟要“垮臺”之說。后來,他們總的結論是“中國對世界事務的重要影響這一主要因素是美國無法逃避的”。至于那個階段蔣介石反復宣傳的中國大陸“餓殍遍地、民怨沸騰,遍布干柴、一點即燃”的說法,隨著一股股潛入大陸的武裝特務在大陸軍民的合圍下紛紛落網,也就成了歷史的笑談。
1964年10月16日,我國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政府的反應是在盡可能地貶低其影響的同時,拒絕接受中國成為核俱樂部的成員。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在當天發表的聲明中聲稱,中國的核試驗并不“出乎意料”,美國和西方國家會“認識到這種爆炸的有限意義”,而且不必擔心“立即導致發生戰爭的危險”。但是,在美國政府內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國愿意不愿意,中國因為握有核武器而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和參與核裁軍等國際事務的談判,只是個時間問題了。現在我們中國還有些人對新中國成立后的任何戰略舉措都喜歡指指點點,什么抗美援朝是錯的、什么兩彈一星也不對,等等。這種思維發展到今天,演變成保衛釣魚島也不對,建航母也不對.....。但是,我們絕大多數人民應該感到慶幸,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中國共產黨還是不糊涂的!
當時中美接觸的主要渠道是華沙會談。在1966年3月的第129次會談中出現了飛躍,美方走向承認新中國的第一次暗示,意味著一個強大繁榮的新中國已經使美國不得不刮目相看了。1967年,也就是中國十年內亂最嚴重的時候(是否美國當局擔心中國內亂會波及美國或者美國是否準備高舉人權高于主權的旗幟對中國開戰就不得而知了--筆者注),一向以強硬反共立場著稱的右翼政治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從長遠的觀點看,我們負擔不起永遠把中國留在各國大家庭之外……” 。1969年尼克松在大選中獲勝,當選美國總統。在就職演說中,他再次含蓄地表達了緩和對華關系的主張:“我們謀求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大小國家的人民都不會怒氣沖沖地處于與世隔絕的地位。” 入主白宮后不久,他便指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同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1969年3月,在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一次會談中,尼克松提出希望與中國開展對話,并請求法國向中國轉達他的這個意向。
1969年12月3日,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終于找到了與中國
外交官接觸的機會。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時裝博覽會上發現廠幾位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為了完成尼克松交辦的工作,他甚至不顧外交禮節,跑著追趕中方人員,請求會晤中國駐波蘭大使,轉達尼克松總統改善中美關系的信息。收到匯報后.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有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拿到敲門磚了。”1969年12月19日,基辛格向巴基斯坦大使表示.美國希望同中國建立比華沙會談更為安全的聯系渠道以便討論更為嚴肅的問題。
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在接受《時代》周刊的采訪時就新中國的作用發表意見,他說:“也許在五年時間里,或甚至十年時間里還不可能起這種作用。但是,在二十年內,它應該也能起這種作用,否則的話,世界就會處于致命的危險境地。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明確地向公眾表達了改善中美關系的愿望。順便提一下,尼克松此時說的20年內,即是1990年以前。毛澤東在1976年新年到來之際,召見了來華訪問的尼克松女兒女婿,對他們說:“你們是年輕的,再到中國來訪問吧。十年以后它將是了不起的。”此時毛澤東所指的,是1986年以后。歸納起來,就是到1986-1990年間,中國將會是一個更為強大的國家。智者所見略同,歷史已經證明,他們都在1970-1976年間根本看不到新中國有什么崩潰之兆!當時的全世界的“高人一籌”的預言家中恐怕只有蔣介石拔得了頭籌,他老人家信心滿滿地指點江山:“整個共產「主義」與「制度」(指大陸---筆者注),也正在向瓦解的過程馳進!”(見1975年《中華民國六十四年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筆者亦相信。至今臺海兩岸依然有人推崇“先總統蔣公”這種英明預見。特別是在大陸,什么中國共產黨不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合法,十年之內中華民國的“國旗”將在大陸飄揚的說法還時有所聞。如果有人質疑,他們就把質疑者打成“腦殘”,也真的不知道誰的腦殘?還是言歸正傳。尼克松在發表了關于新中國重要作用談話后,他和基辛格所委以重托的“巴基斯坦渠道”發揮出了更加積極的作用。1970年12月9日,周思來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遞的口信到達了白宮。基辛格后來寫道:“我當時實在太忙,無法表達我所感到的激動心情(此時的激動尚未到手發抖狀態--筆者注)……這是周恩來發給理查德.尼克松的權威性的個人信息。” 尼克松也表示,他從這些口信以及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中獲得了“極大的鼓舞”。1970年12月16日,尼克松和基辛格很快向中國回復了一個口信:“美國政府相信,為促進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而開始討論將是有益的。”
接下來的“乒乓外交”稱為中美外交史上的精彩一筆,而主要執筆者就是毛澤東。1971年3月30日上午,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代去大會開幕。當晚9時20分,中國代表團向國內匯報了情況和討論的結果:“美國乒乓隊想來華訪問……在今天的國際乒聯代表大會上,我們又點了美國的名。但美國乒乓球隊代表仍與我接觸,并表示美國人民是要同中國人民友好的……”4月3日,外交部和國家體委將關于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問題的請示送呈周恩來,其結論是:現在,美國隊訪華的時機還不成熟。4日,周恩來將文件送毛澤東審批。4月6日,在第31屆世乒賽即將結束的時候,毛澤東在外交部關于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時機不成熟”的文件上畫了個圈。但在當天晚上,毛澤東改變了主意,重新作出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國政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的消息迅速在中美兩國以及世界各地引起強烈的反應。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報告后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又驚又喜”,隨即毫不猶豫地批準乒乓球隊的訪問,他們心里十分清楚,這決不是一個單純的體育事件,而是一個重大的外交轉折即將發生的信號。在“乒乓外交”的鼓舞下,尼克松再次公開表達了他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及他個人到中國訪問的愿望。4月16日,在復活節與女兒女婿談及蜜月旅行的時候,尼克松說道:“我希望你們這一生中有一天能夠到中國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看看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早一點去比晚一點去好。”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攜夫人、國務卿羅杰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等飛越大洋,開始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問。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在任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訪問,也是有史以來美國總統第一次對一個還沒有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進行訪問。到達北京后下午2時左右,在尼克松剛剛收拾停當,正準備洗澡時,周恩來趕到賓館通知說,毛澤東主席想很快會見尼克松總統。40分鐘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走進了毛澤東堆滿著書籍的大書房,“他伸出手來,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一分鐘之久”,尼克松記錄下了這個“動人的時刻”。在將近80分鐘的會談中,毛澤東超凡的魅力給客人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基辛格在回憶錄中用了整整兩頁的篇幅記述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承認,在面對毛澤東的時候,他感覺到了一種類似年輕人聽“搖滾樂”時感覺到的“顫流”--“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與毛澤東的會談是尼克松一生中最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之一。在后來的歲月中,他似乎從未停息過與毛澤東在哲學領域的對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們發現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書中,首先提到毛澤東,說毛澤東是“富有領袖魅力的共產黨領導人,曾運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動了一個國家并改變了這個世界。”
中美關系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山重水復疑無路”之后,終于迎來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基辛格能夠不激動嗎?不用說基辛格,尼克松又何嘗不如此。在與毛澤東會見后那晚參加周恩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尼克松號召中美兩國“一起開始一次長征”,并且引用毛澤東的詩句“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來描述他改善中美關系的急迫心情。
作為一個堅定的反共分子和臺灣的支持者,尼克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右翼分子。最典型的就是他1964年訪問亞洲時發表的一番言論。他說,美國承認紅色中國“對于自由事業來說將是災難性的”,而最終卻恰恰是他承認了中國。對尼克松來說,這是一次堪稱“華麗”的轉身,也是被美國的學者稱之為“美國歷史上最大也是最棒的一次轉變”。1972年2月28日離開中國前,尼克松在歡送他的宴會上說:“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從此,中美蘇三角鼎立的國際格局開始形成。這難道是能簡簡單單就否認得了的嗎?這難道也是不講理的嗎?這難道不是發生在1972年的真實歷史嗎?
溫故知新以史為鑒。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是否也應該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為實現“中國夢”多來點實干興邦呢?瞎扯淡式的空談、語不驚人死不休式的“重說歷史”等等,可能利于某些人賺點講座出場費,簽售得多一點而已,但對實干興邦實在起不到什么積極作用。新中國的前二十九年的發展歷程就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鄧小平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