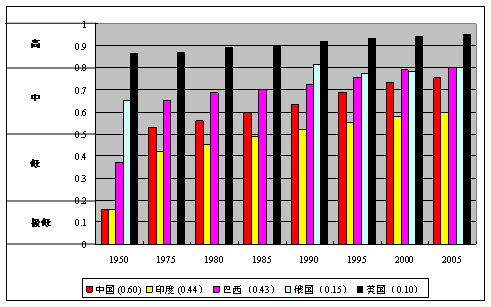推薦者按:這里對比發(fā)表兩篇文章。
堅守方向、探索道路:
中國社會主義實踐60年
王紹光
“一個幽靈,共產(chǎn)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當(dāng)《共產(chǎn)黨宣言》最初用德文在1848年出版時,“共產(chǎn)主義同盟”還是一個秘密團(tuán)體,其影響局限在英、法等歐洲國家。過了半個世紀(jì),到19世紀(jì)末葉,這個“幽靈”出現(xiàn)在中華廣袤的大地上。又過了半個世紀(jì),到20世紀(jì)中葉,社會主義已經(jīng)變成滾滾洪流,席卷全球。以共產(chǎn)主義為最終奮斗目標(biāo)的中國共產(chǎn)黨也在此時奪取了全國政權(quán),神州大地開始英姿勃發(fā)地邁向社會主義。再過半個世紀(jì),到20世紀(jì)末葉,一度紅紅火火的社會主義陷入前所未有低谷,以至有人大膽斷言:歷史已經(jīng)終結(jié),人類社會只有資本主義一途,別無選擇。
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市場原教旨主義”甚囂塵上。它的許諾很簡單、也很誘人:只要將財產(chǎn)權(quán)交給私人,將決策權(quán)交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業(yè)主,將政府干預(yù)減至最低程度,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會源源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無盡的財富,“下溢效應(yīng)”最終會讓所有人受益。
然而,正如卡爾·波蘭尼指出的那樣,“這種自我調(diào)節(jié)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zhì),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否則,它將摧毀人類并將其環(huán)境變?yōu)橐黄囊啊薄?A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 name=_ftnref1>[1] 20世紀(jì)末,在“華盛頓共識”肆意蔓延的同時,窮國與富國、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越拉越大,致使貧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紛紛向左轉(zhuǎn)。到21世紀(jì)初,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害已變得如此明顯,以至于它一些有良知的信徒也看不過眼。香港《信報》創(chuàng)辦人林行止先生自稱寫了三十多年政經(jīng)評論,在2007年10月16日的專欄里,他開始對于自己“年輕時是盲目的自由市場信徒……一切講求經(jīng)濟(jì)效益,認(rèn)為企業(yè)的唯一功能在替股東牟取最大利潤”表示反省。[2] 2008年4月28日,他又發(fā)表專欄文章,重申“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hù)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準(zhǔn)’的理論則經(jīng)不起現(xiàn)實考驗”。他并懇切地希望“中國不要徹底走資”,認(rèn)為“社會主義的確能夠維系社會公平”。[3]
林行止轉(zhuǎn)向不久,一場嚴(yán)重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從美國蔓延至全世界,作為資本主義象征的大型企業(yè)一個接一個面臨破產(chǎn)倒閉的厄運(yùn)。迫不得已,從冰島到愛爾蘭,從澳大利亞到日本,從英國到美國,政府紛紛出手將銀行、保險公司、汽車業(yè)國有化。難怪美國《新聞周刊》封面文章不無揶揄地驚呼:“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了”![4]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雖然世界經(jīng)濟(jì)危機(jī)也拖累了中國經(jīng)濟(jì),但現(xiàn)在全世界都承認(rèn),社會主義的中國經(jīng)濟(jì)將維持正增長,成為全球經(jīng)濟(jì)復(fù)蘇的火車頭之一。在這種強(qiáng)烈的反差對比之下,重新審視中國堅守的方向和走過的道路,意義非同尋常。
前30年的探索
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就指明了新中國未來的方向,即“經(jīng)過人民共和國到達(dá)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到達(dá)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5]在他看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使中華民族不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而是一個“站起來”的民族。[6]
建立人民共和國以后,毛澤東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我們的總?cè)蝿?wù)是,“建設(shè)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實現(xiàn)社會主義工業(yè)化,要實現(xiàn)農(nóng)業(yè)的社會主義化、機(jī)械化”,[7] 要“改變我國在經(jīng)濟(jì)上和科學(xué)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dá)到世界上的先進(jìn)水平”。[8] 到1957年,他把這個目標(biāo)清楚地概括為“建設(shè)一個具有現(xiàn)代工業(yè)、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和現(xiàn)代科學(xué)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9] 為實現(xiàn)這個目標(biāo),首先必須大力發(fā)展生產(chǎn)力。20世紀(jì)50年代,中國還十分貧窮、十分落后,毛澤東非常重視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他指出:“韓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窮文》,我們要寫送窮文。中國要幾十年才能將窮鬼送走”。[10] 他還提醒全國人民“現(xiàn)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jī)、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jī)都不能造”。他認(rèn)為,要經(jīng)過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才可以打下一個基礎(chǔ);要經(jīng)過大約50年即十個五年計劃,才能建成一個富強(qiáng)的中國。[11] 當(dāng)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qiáng),是共同的強(qiáng),大家都有份”。[12]
既然方向是明確的,渡過1949—52年的國民經(jīng)濟(jì)恢復(fù)時期以后,毛澤東便開始探索了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如表1所示,1952年,公有經(jīng)濟(jì)在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大,非公有經(jīng)濟(jì)仍占統(tǒng)治地位。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將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的個體所有制改變?yōu)樯鐣髁x的集體所有制,將私營工商業(yè)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改變?yōu)樯鐣髁x的全民所有制,使生產(chǎn)資料的公有制成為我國唯一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放生產(chǎn)力,[13] 因為只有先解決所有制問題,才能使生產(chǎn)力大大地獲得解放,為發(fā)展新生產(chǎn)力開辟道路,為大大地發(fā)展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創(chuàng)造社會條件。[14]經(jīng)過四年,中國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公有經(jīng)濟(jì)已一躍占據(jù)國民經(jīng)濟(jì)的支配地位。
表1:各種經(jīng)濟(jì)成分比重變化表
|
公有經(jīng)濟(jì) |
非公有經(jīng)濟(jì) | ||||
|
年份 |
國有經(jīng)濟(jì) |
集體經(jīng)濟(jì) |
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 |
個體經(jīng)濟(jì) | |
|
合作經(jīng)濟(jì) |
公私合營 | ||||
|
1952 |
19.1 |
1.5 |
0.7 |
6.9 |
71.8 |
|
1957 |
33.2 |
56.4 |
7.6 |
0.0 |
2.8 |
|
1978 |
56.2 |
42.9 |
0.9 | ||
|
1997 |
41.9 |
33.9 |
24.2 | ||
|
2005 |
31.0 |
8.0 |
61.0 | ||
資料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偉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 1959年,第36頁; 中新社,“數(shù)字看變化:國有經(jīng)濟(jì)地位穩(wěn)固 非公經(jīng)濟(jì)比重上升”,2002年10月7日,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2/10/08/000532129.shtml;李成瑞,“關(guān)于我國目前公私經(jīng)濟(jì)比重的初步測算”,2006年5月23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605/6832.html
不少人認(rèn)為,1957年以前,中國曾完全照搬蘇聯(lián)模式。這完全是誤解。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很清醒,“我們信仰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們中國實際情況相結(jié)合,不是硬搬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硬搬蘇聯(lián)經(jīng)驗是錯誤的。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改造和農(nóng)業(yè)的合作化是跟蘇聯(lián)不同的”。[15] 蘇聯(lián)對資本家采取了剝奪政策,甚至試圖在肉體上消滅資本家;中國則通過贖買的方式將私人資本轉(zhuǎn)化為公有資本,力圖將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蘇聯(lián)采取命令主義和專橫的方式進(jìn)行農(nóng)業(yè)集體化,并對富農(nóng)采取以暴力手段徹底剝奪和消滅的政策;中國的農(nóng)業(yè)集體化則不帶有蘇聯(lián)那樣的強(qiáng)制性,過程也沒有蘇聯(lián)那么混亂。結(jié)果當(dāng)然也不一樣,“蘇聯(lián)農(nóng)業(yè)集體化后幾年是減產(chǎn)的,而我們農(nóng)業(yè)合作化后是增產(chǎn)的”。[16]
雖然毛澤東希望有朝一日實現(xiàn)所有生產(chǎn)資料全民所有制,但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在現(xiàn)階段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的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 “蘇聯(lián)宣布了土地國有,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斯大林不賣拖拉機(jī)等生產(chǎn)資料給集體農(nóng)莊,我們賣給人民公社。所以在我們這里,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chǎn)資料統(tǒng)統(tǒng)都是集體農(nóng)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chǎn)品也是集體所有的”。[17] 蘇聯(lián)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次年,國家所有制已占到全部工業(yè)成分的99.97%;國營農(nóng)業(yè)在農(nóng)業(yè)固定基金中所占的比重也高達(dá)79.2%。此后,在蘇聯(lián),這種生產(chǎn)資料高度集中于國家的狀況,不僅沒有削弱,反被不斷強(qiáng)化。[18] 而中國則不同,1956年以后,雖然國有企業(yè)在國民經(jīng)濟(jì)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直到改革開放前夜的1978年,國有企業(yè)在國民經(jīng)濟(jì)中的比重也才剛剛過半(表1)。同一年,在全國工業(yè)總產(chǎn)值中, 國有企業(yè)占77.16% , 集體企業(yè)占22.14%。但從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目上看,國有企業(yè)只有83,700個,而集體企業(yè)多達(dá)264,700個。[19] 除此之外,中國還在“大躍進(jìn)”和文革后期大力扶植一種新型企業(yè),即農(nóng)村“社隊企業(yè)”(1984年后改稱“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 1978年全國社隊企業(yè)達(dá)152萬個,社會總產(chǎn)值491億元,占全社會總產(chǎn)值的比重為7.17%,占農(nóng)村社會總產(chǎn)值的比重為24.10%,并安置農(nóng)村勞動力2,827萬人,占農(nóng)村勞動力總量的9.2%。[20] 企業(yè)數(shù)目如此之多,使得嚴(yán)格的中央計劃難以實現(xiàn),也為改革開放后出現(xiàn)競爭的局面奠定了基礎(chǔ)。
計劃方面的探索
如果說1956年以前有“照抄”蘇聯(lián)的地方,那主要是指在制定五年計劃方面。大規(guī)模推進(jìn)社會主義工業(yè)化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wù),牽涉到一系列復(fù)雜的問題。毛澤東承認(rèn):“對于政治、軍事,對于階級斗爭,我們有一套經(jīng)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于社會主義建設(shè),過去沒有干過,還沒有經(jīng)驗”。[21] 由于解放初新中國領(lǐng)導(dǎo)人對建設(shè)還是懵懵懂懂,唯一的出路便是向蘇聯(lián)學(xué)習(xí)。中國從1951年初就開始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前后共編制了5 次。期間,毛澤東還派出以周恩來為團(tuán)長、陳云、李富春為副團(tuán)長的政府代表團(tuán)到蘇聯(lián)取經(jīng)。周恩來和陳云在蘇聯(lián)長達(dá)一個多月時間,李富春則率代表團(tuán)在蘇聯(lián)逗留達(dá)10個月之久。[22]
雖然“一五”是向蘇聯(lián)學(xué)習(xí)的產(chǎn)物,但它卻不是一個蘇式計劃。主持制定該計劃的陳云便坦承:“這個計劃,有比較準(zhǔn)確的部分,即國營經(jīng)濟(jì)部分。也有很不準(zhǔn)確的部分,如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都只能做間接計劃【即不是指令性計劃】,而這些部分在我國國民經(jīng)濟(jì)中又占很大比重。我們編制計劃的經(jīng)驗很少,資料也不足,所以計劃帶有控制數(shù)字的性質(zhì),需要邊做邊改”。[23] 另外,這個1953年開始的計劃,直到1955年7月才經(jīng)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同年11月9日和12月19日,國務(wù)院才先后發(fā)布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門執(zhí)行它。而到1956年,計劃規(guī)定的任務(wù)已經(jīng)提前完成了。[24] 可見這個計劃并不像蘇式計劃那么死板。
基于他有關(guān)矛盾普遍性的哲學(xué)觀和對“一五”的觀察,毛澤東并不相信嚴(yán)格的蘇式計劃。他在讀蘇聯(lián)《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教科書》下冊時,對第26章“國民經(jīng)濟(jì)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的規(guī)律”批評最多。他認(rèn)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調(diào),才能促使我們更好地認(rèn)識規(guī)律。出了一點毛病,就以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這完全不是唯物主義者應(yīng)有的態(tài)度”。[25] 因此,“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26] 毛澤東更多的是強(qiáng)調(diào)統(tǒng)籌兼顧,綜合平衡,兩條腿走路,在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條件下,實現(xiàn)幾個同時并舉(包括工農(nóng)業(yè)同時并舉,輕重工業(yè)同時并舉,大中小企業(yè)同時并舉,洋法土法同時并舉,中央與地方同時并舉)。在這種指導(dǎo)思想下,“二五”(1958-1962)開始執(zhí)行不久就被接踵而來的“大躍進(jìn)”打亂。其后出現(xiàn)的國民經(jīng)濟(jì)主要比例關(guān)系失調(diào)使得經(jīng)濟(jì)建設(shè)不能按原來的部署繼續(xù)進(jìn)行,只得于1961年實行國民經(jīng)濟(jì)調(diào)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這次調(diào)整一直持續(xù)到1965年,致使“三五”延遲到1966年才開始。[27]
但“三五”(1966-1970)開始之際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之時。在翻天覆地的文革最初三年,任何計劃工作都難以進(jìn)行。1967年雖然訂出了年度計劃,但無法傳達(dá)到基層;1968年干脆就沒有計劃;而1969年,除原油產(chǎn)量外,幾乎完全沒有實現(xiàn)計劃指標(biāo)。[28]
“四五”計劃(1971-1975)指標(biāo)直到1971年4月才下達(dá)。而到1973年中,毛澤東認(rèn)為,計劃工作仍沒有走上正軌,有必要擬定《第四個五年國民經(jīng)濟(jì)計劃綱要(修正草案)》。[29]
由此可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體制遠(yuǎn)不像蘇聯(lián)體制那么僵化,而總是變動不居。不過,變動不居的代價是經(jīng)濟(jì)增長呈現(xiàn)劇烈的波動性(見圖2)
中國計劃體制與蘇聯(lián)更大的不同是其分權(quán)的程度。毛澤東從來不喜歡蘇式中央計劃體制,這主要是因為他從骨子里厭惡官僚體制。早在1953年,他就反對地方工業(yè)上繳利潤太多,因為這意味著“用于擴(kuò)大再生產(chǎn)的投資就太少了,不利于發(fā)揮地方的積極性”。[30] 到1956年談《論十大關(guān)系》時,他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lián)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jī)動權(quán)也沒有”。[31] 1958年2月,他又提出在中國搞“虛君共和”的設(shè)想。[32] 此后,只要一有機(jī)會,他就會極力推行權(quán)力下放。第一次是1957-1958年,中央大規(guī)模下放了財權(quán)、計劃管理權(quán)、企業(yè)管理權(quán)。[33] 由于“大躍進(jìn)”受挫,1961年后,在劉少奇、陳云主持下,中國恢復(fù)了對國民經(jīng)濟(jì)的集中統(tǒng)一管理,收回了前幾年下放的權(quán)力。然而對毛澤東來說,收權(quán)僅僅是擺脫暫時困難的權(quán)宜之計。一旦經(jīng)濟(jì)好轉(zhuǎn),他決心再一次打碎蘇式的中央計劃體制。1966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提出“虛君共和”的口號,批評中央收權(quán)收得過了頭,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權(quán)力都要還給地方。用他的話說就是“連人帶馬全出去”。[34] 不過,幾個月后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延遲了他的分權(quán)計劃。 七十年代初,形勢剛剛穩(wěn)定下來,毛澤東再一次發(fā)起了分權(quán)運(yùn)動。這次,他要求所有“適合”地方管理的企業(yè)統(tǒng)統(tǒng)將管理權(quán)下放到地方,連鞍鋼、大慶油田、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開灤煤礦這些巨型企業(yè)也不例外。與此同時,財政收支權(quán)、物資管理權(quán)也再次下放。[35]
雖然,其后周恩來、鄧小平加強(qiáng)了中央政府的主導(dǎo)權(quán),但到文革結(jié)束時,中國已經(jīng)是一個相當(dāng)分權(quán)化的國家,與蘇式高度中央集權(quán)的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迥然不同。[36] 這種不同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是國家集中統(tǒng)一分配的物資遠(yuǎn)比蘇聯(lián)少得多。蘇聯(lián)把物資分為三種,即分配權(quán)限屬于國家計委的“基金化產(chǎn)品”,分配權(quán)限屬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計劃產(chǎn)品”,以及分配權(quán)限屬于各加盟共和國的“非集中計劃產(chǎn)品”。基金化產(chǎn)品在50年代初就達(dá)有2370種之多;而“非集中計劃產(chǎn)品”的份額很小。中國也把物資分為三類,即由國家計委統(tǒng)一分配的“統(tǒng)配物資”,由中央各部分配的“部管物資”,以及由地方分配的“三類物資”。如圖1所示,到文革后期,統(tǒng)配物資與部管物資加在一起只有217種。此外,幾次分權(quán)讓地方政府嘗到了甜頭,它們對完成國家調(diào)撥指標(biāo)的態(tài)度也未必總是唯唯諾諾;更有甚者拒絕按國家調(diào)撥價將本地物資賣給外地。[37]
圖1:國家統(tǒng)配物資與部管物資的種類
破除“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方面的探索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20世紀(jì)50年代中期以前集中在所有制上,5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轉(zhuǎn)移到計劃體制上。50年代后期他還開始了另一方面的探索,即破除“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改變?nèi)伺c人的關(guān)系,后來也被叫做“反修防修”。[38]
實際上,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提出,雖然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則沒有完成”。[39] 次年,在評論斯大林《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問題》一書時,他進(jìn)一步指出,“經(jīng)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chǎn)中的平等關(guān)系,是不會自然出現(xiàn)的。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guān)系的形成和發(fā)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中存在著的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yán),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quán)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guān)系和父子關(guān)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40]那時,他用來破除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的手段是搞整風(fēng),搞試驗田,批判等級制,下放干部,兩參一改(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國城鄉(xiāng)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yùn)動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他看來,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消除“資本主義復(fù)辟”的危險。
毛澤東于文革前夕發(fā)表的《五七指示》[41]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憧憬的是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工農(nóng)、城鄉(xiāng)、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的扁平化社會,其目標(biāo)是實現(xiàn)人們在勞動、文化、教育、政治、物質(zhì)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對所謂“走資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對“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革命樣板戲,工農(nóng)兵上大學(xué)、管大學(xué),工宣隊,貧宣隊,赤腳醫(yī)生,合作醫(yī)療,老中青三結(jié)合,工人-干部-知識分子三結(jié)合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實現(xiàn)他理想的途徑。
不過,經(jīng)過8年文革后,毛澤東認(rèn)為,靠一次文革還不能實現(xiàn)他的目標(biāo)。在1974年關(guān)于理論問題的談話中,他透露出壯志未酬的感慨:“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xiàn)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xiàn)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42] 這也成為他“繼續(xù)革命”的理論依據(jù)。毛澤東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又多次談到“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問題,他的結(jié)論是:一百年后還要革命,一千年后還要革命。[43]
簡而言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集中在三個方面:在所有制問題上,中國沒有偏重純而又純的大型國有企業(yè),而是造就了上百萬集體所有制的中小企業(yè);在計劃問題上,中國沒有實行中央集權(quán)的計劃體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將財政收支權(quán)、計劃權(quán)、物資管理權(quán)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在“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問題上,中國沒有形成森嚴(yán)的等級制,而是用種種方式促進(jìn)人們在經(jīng)濟(jì)、社會、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當(dāng)然“階級敵人”除外。
圖2:中國GDP增長率,1953-2008
前30年探索的成就
與蘇式體制相比,中國成百萬中小企業(yè)的存在、各地相對完整的產(chǎn)業(yè)體系、以及分權(quán)的計劃體制為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競爭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制度條件。除此之外,盡管歷經(jīng)波折,毛澤東時代不僅取得的不俗的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1953-1978年間,GDP年均增長速度達(dá)6.5%,見圖2),[44] 也為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經(jīng)濟(jì)增長奠定了堅實的“硬件”與“軟件”基礎(chǔ)。
從“硬件”方面講,毛澤東時代為中國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包括國防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jīng)濟(jì)體系,一個由鐵路、公路、內(nèi)河航運(yùn)、民航空運(yùn)構(gòu)成的交通運(yùn)輸網(wǎng)絡(luò),為80年代以后的經(jīng)濟(jì)起飛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長達(dá)20多萬公里的防洪堤壩和8.6萬個水庫,大大減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澇災(zāi)害;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農(nóng)田基本建設(shè),使灌溉面積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證了10億中國人吃飯、穿衣的需求。[45]
從“軟件”方面講,首先,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限制“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的種種措施使中國變成一個十分扁平化的社會,不存在任何勢力強(qiáng)大的“分利集團(tuán)”。
直到80年代初,中國的不平等程度仍遠(yuǎn)遠(yuǎn)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 大量跨國實證性研究證明,平等往往有利于經(jīng)濟(jì)增長,而不平等往往導(dǎo)致經(jīng)濟(jì)停滯不前。[47] 因此,平等的社會結(jié)構(gòu)是改革開放后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的制度保障之一。
“分利集團(tuán)”是美國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曼庫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在1982年出版的《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提出的概念。他認(rèn)為,過于穩(wěn)定的政體容易滋生出勢力強(qiáng)大的“分利集團(tuán)”,它們不關(guān)心社會總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尋租”,想方設(shè)法要從現(xiàn)有社會總收益中多分幾杯羹。[48] 奧爾森的潛臺詞是,隔一段時間來場“運(yùn)動”是件好事,可以打爛“分利集團(tuán)”,有利于其后的經(jīng)濟(jì)增長。在2000年出版的遺著《權(quán)力與繁榮》中,奧爾森更直接拿中國與前蘇聯(lián)作比較,認(rèn)為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澤東的文革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當(dāng)時的中國不存在任何強(qiáng)勢“分利集團(tuán)”,為日后的改革掃平了道路。[49]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耶魯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蘇珊•蘿絲-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 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奧爾森是不是個毛主義者”?[50]
此外,毛澤東時代強(qiáng)調(diào)公共消費,而不是個人消費,尤其是在醫(yī)療與教育領(lǐng)域。[51] 那時,中國還很窮,但幾乎所有的城鄉(xiāng)人口都享有某種形式的醫(yī)療保障,使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biāo)大幅改善,平均預(yù)期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加到1980年的68歲,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約250‰減少到1980年的50‰以下。當(dāng)時中國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wù)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聯(lián)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世界衛(wèi)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高度贊譽(yù)。[52] 中國低成本、廣覆蓋的衛(wèi)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圖會議上受到推崇,成為世界衛(wèi)生組織在全球范圍內(nèi)推廣初級衛(wèi)生服務(wù)運(yùn)動的樣板。[53] 在毛澤東時代,各級教育也高速發(fā)展。學(xué)齡兒童入學(xué)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劇下降至1982年的22.8%。[54] 表2顯示,共和國前30年,基礎(chǔ)教育發(fā)展很快。小學(xué)在校生人數(shù)增長了6倍,初中生增長了55倍,高中生增長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辦的大學(xué)在校生人數(shù)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幾倍。[55]
表2:主要年份各級各類學(xué)校在校學(xué)生數(shù)
|
大學(xué) |
高中 |
初中 |
小學(xué) | |
|
1949 |
11.7 |
20.7 |
83.2 |
2439.1 |
|
1959 |
81.2 |
143.5 |
774.3 |
9119.9 |
|
1969 |
10.9 |
189.1 |
1832.4 |
10066.8 |
|
1979 |
102.0 |
1292.0 |
4613.0 |
14662.9 |
|
1989 |
208.2 |
716.1 |
3837.9 |
12373.1 |
|
1999 |
413.4 |
1049.7 |
5721.6 |
13548.0 |
|
2007 |
1884.9 |
2522.4 |
5720.9 |
10564.0 |
讓人們活得健康、有知識不僅是發(fā)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識也提高了人力資本的素質(zhì),反過來有利于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56] 對于經(jīng)濟(jì)增長,這種“軟”基礎(chǔ)設(shè)施與“硬”基礎(chǔ)設(shè)施一樣重要。假如沒有共和國前30年在“軟”、“硬”兩方面打下的堅實基礎(chǔ),后30年經(jīng)濟(jì)的騰飛是難以想象的。這一點,印度裔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得主阿瑪?shù)賮啞ど吹煤芮宄K私猓?949年政治變革時中國的生活條件與當(dāng)時印度的情況大致相差無幾。兩個國家都屬于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列,死亡率、營養(yǎng)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57] 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國所處的相對地位就決定性地確立了”,因為中國在初級教育和初級衛(wèi)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尋常的進(jìn)步。[58] 因此,他得出結(jié)論:“改革前中國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方面的成就,對改革后的成績做出了巨大的積極貢獻(xiàn),使中國不僅保持了高預(yù)期壽命和其他相關(guān)成就,還為基于市場改革的經(jīng)濟(jì)擴(kuò)展提供了堅定支持”。[59]剛剛?cè)ナ赖膯倘f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國數(shù)據(jù)證明,后30年,中國經(jīng)濟(jì)之所以能夠快速增長,其奧妙就在于中國的勞動力素質(zhì)比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高。[60]
近年來,人們往往用聯(lián)合國開發(fā)署的“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作為衡量各國社會發(fā)展水平的綜合指標(biāo)。如圖3所示,1950年,中國是世界上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最低的國家之一,僅為0.16,與印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國的指數(shù)已提升至0.53,遠(yuǎn)遠(yuǎn)超過印度的0.42(圖3)。
圖3: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的變化:五大國比較
注釋:國家名稱后面的數(shù)字代表1950年至2005年間,該國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的增加值。
萬丈高樓平地起,最關(guān)鍵的是要打牢基礎(chǔ)。北宋的蘇轍在《新論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話:“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61] 共和國的前30年就是打基礎(chǔ)的30年。打基礎(chǔ)是很艱苦、耗費時日的,而且打基礎(chǔ)的人當(dāng)時未必能馬上享受高樓大廈的舒適。但是,如果沒有前30年打下的堅固基礎(chǔ),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偉樓群。
后30年的探索
盡管共和國前30年取得的成就超過以往任何時代,[62] 到第二個30年開始的時候,中國還是一個窮國。1978年,全國7.9億農(nóng)村居民中有2.5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人均年收入100元),相當(dāng)于當(dāng)時農(nóng)村人口的30.7%。當(dāng)年,農(nóng)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33.6元,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也不過區(qū)區(qū)343.4元。[63] 這種狀況離社會主義的理想顯然相去甚遠(yuǎn),用鄧小平的話說,“現(xiàn)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64]
鄧小平的探索
毛澤東逝世后,鄧小平在總結(jié)前30年經(jīng)驗教訓(xùn)的基礎(chǔ)上對社會主義道路進(jìn)行了新的探索。
為了替下一步的探索掃除思想障礙,在1978-1980年間,鄧小平首先強(qiáng)調(diào)解放思想、實事求是;[65] 強(qiáng)調(diào)馬克思主義也要發(fā)展,毛澤東思想也要發(fā)展,否則就會僵化。[66] 這與當(dāng)年毛澤東倡導(dǎo)擺脫蘇聯(lián)模式的桎梏有異曲同工之妙。鄧小平特別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67] 與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把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看作一個開放的過程;他不止一次坦承,“我們總結(jié)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jīng)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68]“什么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shè)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69]
不過,有一點從一開始就是清楚的,“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fā)達(dá)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使國家富強(qiáng)的社會主義”。[70] 既然“貧窮不是社會主義”,[71] 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wù)就是發(fā)展生產(chǎn)力,使社會物質(zhì)財富不斷增長,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72]
為了促進(jìn)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鄧小平從1980年起就開始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73] 同樣為了促進(jìn)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在鄧小平的帶領(lǐng)下,中國開始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基礎(chǔ)上將計劃與市場結(jié)合起來。[74]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在公有制基礎(chǔ)上實行計劃經(jīng)濟(jì),同時發(fā)揮市場調(diào)節(jié)的輔助作用”,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場調(diào)節(jié)的傳統(tǒng)計劃經(jīng)濟(jì)概念。1984 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又提出“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是公有制基礎(chǔ)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jīng)濟(jì)”,突出計劃與市場的內(nèi)在統(tǒng)一性。1992 年,鄧小平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概念。[75] 此后,市場逐步取代計劃,成為中國生產(chǎn)要素配置的基礎(chǔ)性機(jī)制。
對社會主義而言,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發(fā)展生產(chǎn)力畢竟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水嶺;市場也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那么除了實行市場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生產(chǎn)力外,社會主義最本質(zhì)的特點是什么呢?鄧小平認(rèn)為,第一是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改革開放初期,他強(qiáng)調(diào),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不能動搖的,否則就會產(chǎn)生一個新的資產(chǎn)階級。[76] 從1980年起,他不再強(qiáng)調(diào)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而是強(qiáng)調(diào)公有制為主體,[77]目的是為了給非公有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留出了足夠的空間。1985年他說,“我們允許個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jīng)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yè)發(fā)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78] 的確,那時公有制仍占整個經(jīng)濟(jì)的百分之九十以上。[79] 哪怕是七年后他南巡時,在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公有制仍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80] 即使到鄧小平去世的1997年,公有制在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中還占有四分之三的天地(表1)。
鄧小平認(rèn)為社會主義的第二個特點是共同富裕。在他看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81] 他強(qiáng)調(diào),“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chuàng)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chǎn)生新的資產(chǎn)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fā)展經(jīng)濟(jì),發(fā)展教育和科學(xué),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82] 他解釋道,“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qū)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qū)幫助落后的地區(qū)更好地發(fā)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同時他警告,“如果我們的政策導(dǎo)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chǎn)生了什么新的資產(chǎn)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83]
類似的話,他反復(fù)說了多次,為的是從理論上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區(qū)分開來。但在整個八十年代,他的關(guān)注點一直放在如何進(jìn)行市場改革,如何加快對外開放,如何推動非公有經(jīng)濟(jì)發(fā)展,如何激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裕起來上。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南巡以后,鄧小平的關(guān)注點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他更關(guān)注公有制為主體。在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他開始重提“兩個飛躍”的設(shè)想,即農(nóng)村在實行一段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后,還應(yīng)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用他的話說:“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以公有制為主體,農(nóng)村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84] 另一方面,他更關(guān)注共同富裕問題。1993年,在與弟弟鄧墾談話時,他感慨道:“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xiàn)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么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jīng)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fā)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shù)人沒有,這樣發(fā)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dǎo)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fā)展起來。現(xiàn)在看,發(fā)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fā)展時少”。[85] 這兩方面的變化表明,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zhì)的認(rèn)識進(jìn)一步深化了。以前他一度以為,只要把“餅”做大,就可以最終讓十二億人實現(xiàn)共同富裕。這時他認(rèn)識到,即使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大多數(shù)人也未必一定收益。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才有可能“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86] 不過,說這些話時,鄧小平已經(jīng)不管日常工作。他的這些觀點要等到十余年后才公布于世。
鄧小平在世時,公有制的一統(tǒng)天下已被打破。個體經(jīng)濟(jì)、私營經(jīng)濟(jì)、外資經(jīng)濟(jì)迅速發(fā)展,還出現(xiàn)了不同所有制互相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不過,那時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僅僅被看作公有制的“必要補(bǔ)充”,現(xiàn)存公有制企業(yè)也沒有改變性質(zhì)。這一點在圖4中看得很清楚:雖然公有制單位雇員占城鎮(zhèn)就業(yè)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99.8%降到1996年的71.6%,但公有制單位雇員的絕對數(shù)卻在同一時期內(nèi)從9500萬增加到了14260萬。
圖4:城鎮(zhèn)公有制單位就業(yè)人數(shù)的變化
十五大以來的探索
所有制格局的重大變革出現(xiàn)在鄧小平逝世之后。如表3所示,在歷次黨代會報告中,沒有哪次比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報告對所有制改革著墨更多。十五大報告對“公有制”和“公有制占主體”都提出了新的解釋。“公有制”不僅包括傳統(tǒng)的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還包括國家和集體控股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勞動者的勞動聯(lián)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lián)合為主的集體經(jīng)濟(jì)。而“公有制占主體”被解釋成“公有資產(chǎn)在社會總資產(chǎn)中占優(yōu)勢;國有經(jīng)濟(jì)控制國民經(jīng)濟(jì)命脈,對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主導(dǎo)作用”。反過來說,有的地方、有的產(chǎn)業(yè)公有資產(chǎn)不一定非占優(yōu)勢不可;對不是關(guān)系國民經(jīng)濟(jì)命脈的行業(yè)和領(lǐng)域,國有經(jīng)濟(jì)不必非占支配地位不可。如此說來,只要堅持這種“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jīng)濟(jì)和集體經(jīng)濟(jì)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zhì)。
表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guān)所有制改革的新提法
|
文件 |
提法 |
|
1981年,十一屆四中全會《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l 國營經(jīng)濟(jì)和集體經(jīng)濟(jì)是我國基本的經(jīng)濟(jì)形式, 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jīng)濟(jì)是公有制經(jīng)濟(jì)的必要補(bǔ)充 |
|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決定》 |
l 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礎(chǔ)上廣泛發(fā)展全民、集體、個體經(jīng)濟(jì)相互之間靈活多樣的合作經(jīng)營和經(jīng)濟(jì)聯(lián)合, 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業(yè)還可以租給或包給集體或勞動者個人經(jīng)營。 l 利用外資, 吸引外商來我國舉辦合資經(jīng)營企業(yè)、合作經(jīng)營企業(yè)和獨資企業(yè), 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必要的有益的補(bǔ)充。 |
|
1987年,十三大報告 |
l 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種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以外, 還應(yīng)發(fā)展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聯(lián)合建立的公有制企業(yè), 以及各地區(qū)、部門、企業(yè)互相參股等形式的公有制企業(yè)。 l 在不同的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 不同的地區(qū), 各種所有制經(jīng)濟(jì)所占的比重應(yīng)當(dāng)有所不同。 |
|
1992年,十四大報告 |
l 在所有制結(jié)構(gòu)上, 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 個體經(jīng)濟(jì)、私營經(jīng)濟(jì)、外資經(jīng)濟(jì)為補(bǔ)充, 多種經(jīng)濟(jì)成分長期共同發(fā)展, 不同經(jīng)濟(jì)成分還可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lián)合經(jīng)營。 l 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和其他企業(yè)都進(jìn)入市場, 通過平等競爭發(fā)揮國有企業(yè)的主導(dǎo)作用。 |
|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guān)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
l 隨著產(chǎn)權(quán)的流動和重組, 財產(chǎn)混合所有的經(jīng)濟(jì)單位越來越多,將會形成新的財產(chǎn)所有結(jié)構(gòu)。 l 就全國來說, 公有制應(yīng)在國民經(jīng)濟(jì)中占主體地位, 有的地方, 有的產(chǎn)業(yè)可以有所區(qū)別。 l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xiàn)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chǎn)在社會總資產(chǎn)中占優(yōu)勢, 國有經(jīng)濟(jì)控制國民經(jīng)濟(jì)命脈及對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主導(dǎo)作用等方面。 |
|
1997年,十五大報告 |
l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xiàn)在:公有資產(chǎn)在社會總資產(chǎn)中占優(yōu)勢;國有經(jīng)濟(jì)控制國民經(jīng)濟(jì)命脈,對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主導(dǎo)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產(chǎn)業(yè)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資產(chǎn)占優(yōu)勢,要有量的優(yōu)勢,更要注重質(zhì)的提高。國有經(jīng)濟(jì)起主導(dǎo)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控制力上。要從戰(zhàn)略上調(diào)整國有經(jīng)濟(jì)布局。對關(guān)系國民經(jīng)濟(jì)命脈的重要行業(yè)和關(guān)鍵領(lǐng)域,國有經(jīng)濟(jì)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lǐng)域,可以通過資產(chǎn)重組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以加強(qiáng)重點,提高國有資產(chǎn)的整體質(zhì)量。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jīng)濟(jì)命脈,國有經(jīng)濟(jì)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qiáng),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jīng)濟(jì)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zhì)。 u 公有制實現(xiàn)形式可以而且應(yīng)當(dāng)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chǎn)規(guī)律的經(jīng)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jìn)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公有制實現(xiàn)形式。 u 股份制是現(xiàn)代企業(yè)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yè)和資本的運(yùn)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tǒng)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guān)鍵看控股權(quán)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kuò)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qiáng)公有制的主體作用。 u 目前城鄉(xiāng)大量出現(xiàn)的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制經(jīng)濟(jì),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導(dǎo),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使之逐步完善。 u 勞動者的勞動聯(lián)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lián)合為主的集體經(jīng)濟(jì),尤其要提倡和鼓勵。 |
|
2002年,十六大報告 |
l 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diào)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chǎn)力發(fā)展具有重要作用。 l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jìn)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發(fā)展,統(tǒng)一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進(jìn)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jīng)濟(jì)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相互促進(jìn),共同發(fā)展。 l 要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除極少數(shù)必須由國家獨資經(jīng)營的企業(yè)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jīng)濟(jì)。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重要的企業(yè)由國家控股。 |
|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公報 |
l 要大力發(fā)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jīng)濟(jì),實現(xiàn)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xiàn)形式。 l 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yè),應(yīng)區(qū)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 l 要大力發(fā)展和積極引導(dǎo)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允許非公有資本進(jìn)入法律法規(guī)未禁入的基礎(chǔ)設(shè)施、公用事業(yè)及其他行業(yè)和領(lǐng)域。 |
|
2007年,十七大報告 |
l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jīng)濟(jì),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dǎo)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發(fā)展,堅持平等保護(hù)物權(quán),形成各種所有制經(jīng)濟(jì)平等競爭、相互促進(jìn)新格局。 l 深化國有企業(yè)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優(yōu)化國有經(jīng)濟(jì)布局和結(jié)構(gòu),增強(qiáng)國有經(jīng)濟(jì)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
十五大后,對現(xiàn)存公有制企業(yè)改制成為所有制改革的重點。抓大放小、鼓勵兼并、規(guī)范破產(chǎn)、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成為流行的口號。到2005年,國有中小企業(yè)改制面已達(dá)到85%以上,集體企業(yè)改制面更大,其中大批企業(yè)破產(chǎn)消亡了,更多的變成了私營企業(yè);[87] 在凈資產(chǎn)占全國國有企業(yè)三分之二的252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型骨干企業(yè)中,也有1331家改制為多元股東的股份制企業(yè),改制面為52.7%。[88] 與此同時,原來集體性質(zhì)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也紛紛易幟,到2006年,全國168萬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中,95%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其中20萬家轉(zhuǎn)成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yè),139萬家轉(zhuǎn)成了個體私營企業(yè)。[89] 經(jīng)過幾年的改制,2004年末,國家和集體投入占全國企業(yè)法人單位實收資本總額的比重降為56%;[90] 2005年,公有經(jīng)濟(jì)占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的比重降為39%(表1);2007年,國有、國有控股以及集體工業(yè)企業(yè)占全部工業(yè)總產(chǎn)值的比重降為32%;同年,國有和集體單位從業(yè)人員占全部城鎮(zhèn)從業(yè)人員的比重降為24.3%。[91]
與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相比,中國的所有制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公有經(jīng)濟(jì)成分大幅減少,公有經(jīng)濟(jì)的形式也多種多樣。顯然,這與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模式已經(jīng)相去甚遠(yuǎn)。盡管如此,中國公有經(jīng)濟(jì)的成分仍然遠(yuǎn)遠(yuǎn)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除此之外,中國憲法規(guī)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以及城市的土地都屬于國家所有;農(nóng)村和城市郊區(qū)的土地,除由法律規(guī)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都屬于集體所有。這使得中國仍然比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更加“社會主義”。正因為如此,國內(nèi)外總有一批人或明火執(zhí)仗地鼓噪“私有化”,或半遮半掩地?fù)u晃“反壟斷”旗幟,必欲將剩余的公有經(jīng)濟(jì)成分完全消滅而后快,從而在中國砍掉社會主義這面大旗。[92]中共十七大重申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jīng)濟(jì)”,“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dǎo)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一定讓他們相當(dāng)失望。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共和國后30年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讓世人矚目的成就。
第一,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加快。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9%,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以前被人贊譽(yù)有加的東亞“四小龍”都是些小經(jīng)濟(jì)體,其中最大的韓國也不過四千來萬人,相當(dāng)于中國一個中等規(guī)模的省。日本在其高速增長期,人口也只有一億上下,與中國最大的省差不多。作為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超大、超復(fù)雜經(jīng)濟(jì)體,中國連續(xù)30年高速增長,這在人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名副其實的“奇跡”。
第二,經(jīng)濟(jì)增長更加平穩(wěn)。這從圖2看到很清楚,后30年經(jīng)濟(jì)波動明顯不像前30年那么頻繁,波幅也沒有以前那么大。尤其是1992年以后,經(jīng)濟(jì)增長曲線更趨平滑,標(biāo)志著中國政府的宏觀經(jīng)濟(jì)管理水平大有進(jìn)步。
第三,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如圖5所示,在過去30年,中國政府已將貧困標(biāo)準(zhǔn)從100元提高到1196元。 即便如此,農(nóng)村貧困發(fā)生率也從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8年的4.2%。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貧困標(biāo)準(zhǔn)計算,中國的扶貧成就則更為顯著。從1981 年到2004 年,貧困人口的絕對數(shù)量從6.52 億降至1.35 億,5 億多人擺脫了貧困。而在同一時期,全球發(fā)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的絕對數(shù)量只減少了4 億。換言之,如果排除中國,發(fā)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數(shù)量不僅沒有減少,反倒增加了。難怪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贊嘆道: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對于全人類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93]
當(dāng)然,后30年的探索也不可避免的走過彎路。尤其是在20世紀(jì)90年代,各級領(lǐng)導(dǎo)人似乎有意無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鼓吹的 “下溢理論”:只要經(jīng)濟(jì)持續(xù)增長,所有人最終都會受益,其他一切問題都遲早會迎刃而解。在“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指導(dǎo)思想下,[94]為了追求盡可能高的經(jīng)濟(jì)增長速度,他們寧愿犧牲公平、就業(yè)、職工權(quán)益、公共衛(wèi)生、醫(yī)療保障、生態(tài)環(huán)境、國防建設(shè)等,結(jié)果帶來了一系列嚴(yán)重的問題。到90年代末,有些問題已變得觸目驚心,盡管經(jīng)濟(jì)持續(xù)增長,但工農(nóng)大眾享有的福利保障卻越來越少。大規(guī)模下崗失業(yè)、上學(xué)貴、就醫(yī)貴讓千千萬萬人痛感缺乏經(jīng)濟(jì)與社會安全。在這個背景下,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損或受益不多的階層對新推出的市場導(dǎo)向改革不再毫無保留地支持;相反,他們對凡是帶有“市場”、“改革”標(biāo)簽的舉措都疑慮重重,生怕再次受到傷害。
當(dāng)人們普遍感覺到中國改革已經(jīng)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時候,中央決策者也開始認(rèn)真反思鄧小平早已發(fā)出的警告:“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qū)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相應(yīng)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95] 2002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六大試圖重新解釋“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含意,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優(yōu)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96] 但貧富懸殊的殘酷現(xiàn)實告訴人們,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例如老板、經(jīng)理、干部與普通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樣需要重視,單靠財稅等再分配杠桿來調(diào)節(jié)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97]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雖然仍然沿用“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但其分量已被“以人為本”的“科學(xué)發(fā)展觀”大大沖淡。 2004年9月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干脆放棄了“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提法。[98] 2005年底,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guān)于制定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一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又進(jìn)了一步,提出未來中國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99] 到了中共十七大,標(biāo)準(zhǔn)提法已變?yōu)椤俺醮畏峙浜驮俜峙涠家幚砗眯屎凸降年P(guān)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00]
從2002年起,中國政府還開始致力于建立健全覆蓋城鄉(xiāng)全體居民的社會服務(wù)和保障體系(包括免費九年義務(wù)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養(yǎng)老、基本醫(yī)療、失業(yè)、工傷、生育保險制度等),其進(jìn)展速度超過以往任何時期,大大充實了鄧小平有關(guān)“共同富裕”的理念。如果說從1978年到1990年代后期中國只有經(jīng)濟(jì)政策、沒有社會政策的話,那么在世紀(jì)之交,我們看到社會政策已經(jīng)廣泛出現(xiàn)在神州大地上了。沒有一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政府,沒有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在短短幾年內(nèi)出現(xiàn)這樣歷史性的“大轉(zhuǎn)型”是難以想象的;這種“大轉(zhuǎn)型”本身也構(gòu)成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步驟。[101]
結(jié)語
到2009年,人民共和國渡過了它的第一個甲子。勿庸諱言,60年過后,對如何建設(shè)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依然沒有一套完美無缺的方案;我們有的只是一個大致的方向,那就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zhì)財富,消滅剝削和壓迫,消除兩極分化,實現(xiàn)社會公平和正義,逐步建立起一個沒有階級對立的“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102] 歷史經(jīng)驗告訴我們,建設(shè)社會主義最重要的不是有沒有詳盡的藍(lán)圖?而是有沒有認(rèn)清社會主義方向的視野?有沒有不相信歷史已經(jīng)終結(jié)的睿智?有沒有不折不饒地邁向社會主義未來的勇氣?有沒有不斷探索實現(xiàn)社會主義理想新途徑的膽略?
過去60年,中國一直在堅守了社會主義方向的同時,不懈地探索著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當(dāng)然,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中國都曾走過彎路。只要是探索,哪能一點彎路都不走呢?關(guān)鍵在于,從毛澤東到胡錦濤,中國領(lǐng)導(dǎo)人從不接受“歷史已經(jīng)終結(jié)”之類的謬論,從不相信存在什么“放諸四海而皆準(zhǔn)”的“普世”模式。相反,他們更側(cè)重于從實踐和實驗中進(jìn)行學(xué)習(xí),獲取必要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可則因,否則革”,不斷調(diào)整政策目標(biāo)和政策工具,以回應(yīng)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103] 雖然左一腳、右一腳,深一腳、淺一腳,過去60年,中國就是這么一步步走過來的。
正因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中國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書寫了一篇比韓愈精彩千萬倍的《送窮文》。從經(jīng)濟(jì)社會綜合發(fā)展水平看,在1950年,中國的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屬于“極低”之列,還不到前蘇聯(lián)的三分之一;而到2005年,中國的指數(shù)已跨入“上中”的行列,離當(dāng)年的“老大哥”不過一步之遙。在60年里,中國的人類發(fā)展指數(shù)快速攀升了0.6,遠(yuǎn)高于其它國家,證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正確的選擇(圖3)。盡管今天的中國還存在著大量嚴(yán)重的問題,面臨著多重嚴(yán)峻的挑戰(zhàn),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未來的道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廣。
2009年7月4日星期六
[1] 卡爾·波蘭尼 (馮鋼、劉陽譯), 《大轉(zhuǎn)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jīng)濟(jì)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頁。
[2] 林行止,“企業(yè)多顯人性 共造和諧社會”, 《信報》,2007年10月16日。
[3] 林行止,“糧食危機(jī)中對富人和中國的期待”,《信報》,2008年4月28日。
[4]
[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jì)念中國共產(chǎn)黨二十八周年》, 1949年6月30日。
[6] 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
[7] 毛澤東,《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8] 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chǎn)力》,1956年1月25日。
[9]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10] 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lián)負(fù)責(zé)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
[11] 毛澤東,《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12] 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1955年10月29日。
[13] 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chǎn)力》,1956年1月25日。
[14] 毛澤東,《讀蘇聯(lián)<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教科書>》的談話(節(jié)選)》,1959年12月—1960年2月。
[15] 毛澤東,《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1956年12月8日。1979年,在與外賓談話時,鄧小平也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lián)不完全一樣,一開始就有區(qū)別,中國建國以來就有自己的特點”。《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5頁。
[16] 同上。
[17] 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問題>談話》,1958年11月9-10日。
[18] 張建勤,《中蘇傳統(tǒng)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比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131-133頁。
[19] 劉國光、董志凱,“新中國50 年所有制結(jié)構(gòu)的變遷”,《當(dāng)代中國史研究》, 1999 年第5-6期,第27-28頁。
[20] 王鳳林,“我國社隊企業(yè)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中國農(nóng)村觀察》,1983年第4期。
[21] 毛澤東,《在擴(kuò)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22] 袁寶華,《赴蘇聯(lián)談判的日日夜夜》,《當(dāng)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26頁。
[23] 陳云,《關(guān)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1954年6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3035/83317/83596/5738291.html。
[24] 柳隨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國民經(jīng)濟(j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9頁。
[25]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注和談話(簡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xué)會,2000年,第73頁。
[26] 同上,第71頁。
[27] 叢進(jìn),《曲折發(fā)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5-456頁。
[28]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61頁。
[29] 史云、李丹慧,《難以繼續(xù)的“繼續(xù)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243-247頁。
[30]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jǐn)U大會議上的講話》, 1953年7月29日。
[31] 毛澤東,《論十大關(guān)系》,1956年4月25日。
[3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796-797頁。
[33]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jīng)濟(jì)史論》,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頁。
[34] 趙德韾《中華人民共和國經(jīng)濟(jì)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頁。
[35] 史云、李丹慧,《難以繼續(xù)的“繼續(xù)革命”:從批林到批鄧》,第225-232頁。
[36]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jīng)濟(jì)史論》,第512-515頁;Thomas P. Lyon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lanning in Mao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3-218。
[37] 趙德韾,《中華人民共和國經(jīng)濟(jì)史:1967-1984》,第60-62頁。
[38] 胡喬木,《毛主席在追求一種社會主義》,1980年6月9日。見《胡喬木傳》編寫組,《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72頁。
[39] 毛澤東,《對<這是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一文的批語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
[40]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注和談話(簡本)》,第40-41頁。
[41] 毛澤東,《對總后勤部關(guān)于進(jìn)一步搞好部隊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
[42] 毛澤東,《關(guān)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4年1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413頁。
[43]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四號文件),1976年3月3日。該文件根據(jù)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談話整理,并經(jīng)毛澤東審閱批準(zhǔn)。
[44] 對共和國前30年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這段歷史,鄧小平指出,“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jìn)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wù)虛會上的講話》,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7頁。對長時段世界經(jīng)濟(jì)增長頗有研究的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與鄧小平的看法一致:盡管中國在1952-1978年間遭到西方國家的阻隔,還與美、蘇對峙,與韓國、印度發(fā)生了戰(zhàn)爭,與過去100年相比,新中國經(jīng)濟(jì)仍取得了巨大的進(jìn)步。麥迪森對中國GDP增長速度的估計遠(yuǎn)低于官方數(shù)據(jù),但即使按他的數(shù)據(jù),在此期間,中國GDP也翻了三倍,人均GDP增加了82%,勞動生產(chǎn)率提高了58%。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也實現(xiàn)了歷史性的轉(zhuǎn)型:1952年,GDP中的工業(yè)比重是農(nóng)業(yè)比重的1/4,而到1978年,工業(yè)比重已超過農(nóng)業(yè)比重。見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OECD, 2007, p. 59.
[45]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jīng)濟(jì)史論》,第524-530頁。
[46] World Bank ,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 DC : World Bank , 1997 , p. 8.
[47]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Washington , DC : World Bank , 1991; A. Alesina and D. Rodrik, “Distributio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Cukierman, Z. Hercowitz and L . Leiderman, eds. Political
Economy,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pp. 23-50; T. Persson and G. Tabellini,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pp. 600-621; Roberto Pertotti , “Growth ,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Vol. 1 (June 1996) , pp. 149-18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Challenge, Vol. 41, No. 2 (March/ April 1998), pp. 61-80.
[48] 曼庫爾.奧爾森(呂應(yīng)中等譯),《國家興衰探源》,商務(wù)印書館,1999年。
[49] 曼庫爾.奧爾森(蘇長和、嵇飛譯),《權(quán)力與繁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頁。
[50] Susan Rose-Ackerman, “Was Mancur a Maoist? An Essay on Kleptocr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 15 (2003), pp. 135-162. 蘇珊•蘿絲-艾克曼不知道的是,90年代初,中國學(xué)者張宇燕曾與奧爾森有幾次對話。奧爾森對于毛澤東關(guān)于“黨內(nèi)的走資派”、“炮打司令部”、“摻沙子、挖墻角”、“從大亂達(dá)到大治”等論斷表現(xiàn)出極大興趣。當(dāng)他聽說,毛澤東認(rèn)為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時,更是激動地從沙發(fā)上站了起來。張宇燕,《跟奧爾森教授學(xué)習(xí)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與常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5頁。
[51]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yè)還成什么社會主義”。他批評蘇聯(lián)《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教科書》,“這本書在談到物質(zhì)利益的時候,不少地方只講個人的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業(yè)。這是一種片面性”。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注和談話(簡本)》,第282-284頁。
[52] 例如世界銀行的《1993 年世界發(fā)展報告: 投資與健康》稱中國當(dāng)年在醫(yī)療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國家是“獨一無二”的(a unique achievement for a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111. 也見Kenneth W. Newell, Health By The Peopl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1975);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United Nation Children's Fund, Meeting Basic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ntyies: Altemative Approach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Matthias Stiefel and W.F. Wertheim, Prodction, Equaty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London: Zed Pres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3).
[53]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Primary Health Car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 (Geneva: WHO, 1978.); Dean T. Jamison, et al., China, the Health Secto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4); BMJ Editorial Board, “Primary Health Care led NHS: Learn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BMJ, October 7, 1995,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1/7010/891 (2009年4月19日訪問); Therese Hesketh and Wei 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Reform,” BMJ, May 24, 1997,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4/7093/1543 (2009年4月19日訪問);
[54] 賴立、張竺鵬、謝國東,《我國成人文盲十年減少近1億 女性文盲率降幅大》,《中國教育報》,2007年8月1日,http://www.edunews.net.cn/jzzx/OldNews/20078190600.html。
[55] 國家統(tǒng)計局國民經(jīng)濟(jì)綜合統(tǒng)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資料匯編》,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1999年,第81-82頁。
[56] 參見羅默(Paul Rom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
[57] 阿瑪?shù)賮?#8226;森、讓·德雷茲,《印度: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社會機(jī)會》,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6年,第71頁。
[58] 同上,第80頁。
[59] 同上,第70頁。
[60]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61] 《蘇轍集》,欒城集卷十九,新論中,http://www.guoxue.com/sushiyjiu/szwj/szwj_019.htm。
[62]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9, p. 99.
[63] 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摘要,2009》,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09年,第109、111頁)。
[64] 《鄧小平文選》第3 卷第225 頁。
[65]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tuán)結(jié)一致向前看》(1979年12月13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0-153頁。
[66] 鄧小平,《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1979年9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26-128頁。
[67] 鄧小平,《社會主義首先要發(fā)展生產(chǎn)力》(1980年4月—5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2頁。
[68]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6-140頁。
[69] 鄧小平,《吸取歷史經(jīng)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7頁。
[70] 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jīng)濟(jì)》(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1頁。
[71] 鄧小平,《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72] 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1頁。
[73]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wù)》(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58頁。
[74] 鄧小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jīng)濟(jì)》,第236頁。
[75] 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4年,第1347頁。
[76] 鄧小平,《實行開放政策,學(xué)習(xí)世界先進(jìn)科學(xué)技術(shù)》(1978年10月10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33頁。
[77]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353頁。
[78]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jì)律才能團(tuán)結(jié)起來》(1985年3月7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0頁。
[79]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8頁。
[80]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372頁。
[81] 鄧小平,《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82] 鄧小平,《搞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年5、6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3頁。
[83] 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jì)律才能團(tuán)結(jié)起來》,第110-111頁。
[84] 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1350頁。
[85] 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2004年,第1364頁。
[86] 同上。
[87]李榮融,《進(jìn)一步推進(jìn)國有資產(chǎn)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yè)改革 實現(xiàn)國有企業(yè)的體制創(chuàng)新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在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的演講》,2005年7月12日,http://www.sasac.gov.cn/n1180/n3123702/n3123987/n3125287/3188291.html。
[88]張卓元,《30年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回顧與展望》,2008年02月03日,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80203/11264487740.shtml
[89]趙悅,《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前世今生”》,CCTV中國財經(jīng)報導(dǎo),2007年04月23日,http://www.cctv.com/program/cbn/20070424/102108.shtml。
[90] 國務(wù)院第一次全國經(jīng)濟(jì)普查領(lǐng)導(dǎo)小組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tǒng)計局,《第一次全國經(jīng)濟(jì)普查主要數(shù)據(jù)公報(第一號)》,2005年12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06/content_3883969.htm。
[91] 國家統(tǒng)計局,《改革開放30年報告之三: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在不斷優(yōu)化升級中實現(xiàn)了重大調(diào)整》,2008年10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029_402512864.htm。
[92] 美國保守組織“傳統(tǒng)基金會”一位亞洲經(jīng)濟(jì)研究員最近撰文批評,“自當(dāng)前的中國領(lǐng)導(dǎo)人掌權(quán)以來,以市場為導(dǎo)向的自由化已經(jīng)漸趨淡化。并且,當(dāng)以市場為導(dǎo)向的自由化逐漸銷聲匿跡時,國家干預(yù)開始卷土重來:控制價格,逆轉(zhuǎn)私有化”。見Derek Scissors, “Deng Undone,” April 29, 2009 and “Liberalization in Reverse,” May 4, 2009, http://www.heritage.org/about/staff/derekscissorspapers.cfm. 又見“So much for capitalism: The opening up of China’s economy goes into reverse,” The Economist, March 5, 2009, http://www.economist.com/business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3235115.
[93] 世界銀行東亞及太平洋地區(qū)扶貧與經(jīng)濟(jì)管理局,《從貧困地區(qū)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jìn)—中國貧困和不平等問題評估》,2009 年3 月,第iii頁。
[94] “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最初是由周為民、盧中原牽頭的“社會公平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課題組提出來的,其主報告以“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通向繁榮的權(quán)衡”為題發(fā)表于《經(jīng)濟(jì)研究》1986年第2期。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正式使用了“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十五大堅持了這個提法。
[95] 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8年第453頁。
[96] 江澤民,“全面建設(shè)小康社會,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
[97] 劉國光,“把‘效率優(yōu)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 《經(jīng)濟(jì)參考報》,2005年10月15日。
[98] “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 2004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19/content_1995366.htm。
[99] 新華網(wǎng)2005年10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8/content_3640318.htm。
[100]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
[101] 王紹光,《大轉(zhuǎn)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yùn)動》,《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8年第1期,第129-148頁。
[10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chǎn)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第1卷,第294頁。
[103] 王紹光,《學(xué)習(xí)機(jī)制與適應(yīng)能力:中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體制變遷的啟示》, 《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8年第6期,第111-133頁。
附文:
吳敬璉:中國經(jīng)濟(jì)六十年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87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來,從計劃到市場,在經(jīng)濟(jì)建設(shè)上走過一條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間經(jīng)歷過無數(shù)艱辛、動蕩、搖擺與反復(fù),既有山重水復(fù)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轉(zhuǎn)機(jī)。這是一段中華民族走向復(fù)興之路的歷史;一段打破思想桎梏、尋找經(jīng)濟(jì)規(guī)律的歷史;一段摒棄少數(shù)權(quán)威、尊重大眾個體權(quán)利與貢獻(xiàn)的歷史;一段重新劃定政府與市場界限的歷史。這個過程是人類探索未來發(fā)展方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人類社會貢獻(xiàn)了從計劃經(jīng)濟(jì)向市場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寶貴經(jīng)驗和教訓(xùn)。
60年前,中國開始了一個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礎(chǔ)上的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來實現(xiàn)民族振興的宏大嘗試。這個嘗試以失敗告終,有其內(nèi)在的必然性。當(dāng)整個社會取消了微觀個體對外探索的權(quán)利與自由,只由少數(shù)精英通過制定計劃的方式來引導(dǎo)全國人民向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進(jìn)行探索時,偶爾可能會走對了方向,但更多的可能是誤入歧途;甚至其糾錯機(jī)制都是非常僵化而低效的:認(rèn)識錯誤時要高度依賴少數(shù)精英,改正錯誤時是整個社會一致行動——但這種行動,往往也未必是正確的,整個社會來回往復(fù)地試錯,為此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難以度量。
30年前,中華民族窮則思變,摒棄了在原有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內(nèi)的修修補(bǔ)補(bǔ),開始了由計劃經(jīng)濟(jì)向市場經(jīng)濟(jì)轟轟烈烈的轉(zhuǎn)型。這個過程,在當(dāng)時叫做“摸著石頭過河”;到今天,則可以斷言,市場經(jīng)濟(jì)是引領(lǐng)中國經(jīng)濟(jì)再鑄輝煌的必由之路。
與此前的改良不同之處在于,從中國決定在公有經(jīng)濟(jì)之外開始市場化改革之日起,普通民眾作為個體,在開始獲得掌握自己命運(yùn)的權(quán)利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擔(dān)了探索社會發(fā)展方向的使命。理想的市場經(jīng)濟(jì)的優(yōu)越性在于,社會上每個微觀主體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由于稟賦不同,際遇不同,不同的人找到正確方向的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確的方向,社會其他人可以跟進(jìn),并分享這個好處。在這個過程中,價格體系發(fā)揮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引導(dǎo)和優(yōu)化資源配置,更對人們行為的優(yōu)劣起客觀的評判作用。找到正確方向的人,還可以通過價格機(jī)制得到合理的回報。
私有產(chǎn)權(quán)、市場、企業(yè),市場經(jīng)濟(jì)體系中這三位一體的基本元素,在計劃經(jīng)濟(jì)中一度完全缺失。基于產(chǎn)權(quán)基礎(chǔ)上的人力資本或者物質(zhì)資本,到底是通過價格機(jī)制在市場上配置或者組合,還是在企業(yè)中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利用,取決于兩種方式何者更有效。對于同樣一種經(jīng)濟(jì)活動,由各種人力資本和物質(zhì)資本通過締結(jié)契約而成的企業(yè),如果其管理成本高于市場價格機(jī)制配置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則說明該企業(yè)從事此經(jīng)濟(jì)活動是低效的,應(yīng)該將之歸于市場。這種市場經(jīng)濟(jì)中屢見不鮮的企業(yè)重組,在計劃經(jīng)濟(jì)中是無從得見的,因為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就是一個大企業(yè),但其運(yùn)作的好壞,由于沒有一個外在的市場和價格體系來衡量而無從知曉,最終流于低效、破敗。
中國經(jīng)濟(jì)60年的發(fā)展歷程,迄今為止絕大部分時間就是在對這套體系進(jìn)行改革的歷程。從原來徒勞無功的體制內(nèi)改良,到發(fā)展公有經(jīng)濟(jì)和計劃體制外的非公經(jīng)濟(jì)和市場體制,再到公有經(jīng)濟(jì)和計劃體制的全面變革,方向早已明確,目標(biāo)漸次清晰。產(chǎn)權(quán)改革,市場(價格)改革,(國有)企業(yè)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多管齊下,極大地釋放出國民經(jīng)濟(jì)的活力,支撐了中國經(jīng)濟(jì)30年來平均近10%的增長,使之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三大經(jīng)濟(jì)體。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經(jīng)濟(jì)的改革過程遠(yuǎn)未成功:產(chǎn)權(quán)改革依然任重道遠(yuǎn);許多要素價格如能源、利率、匯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國企改革到能源、電信、金融等國有壟斷行業(yè)便難以推進(jìn);政府和國有部門仍然控制著國民經(jīng)濟(jì)中大部分的資源。這些由于改革不徹底而造成的問題互相交織,是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失衡、環(huán)境惡化等問題的根源。
盡管中國經(jīng)濟(jì)60年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國民經(jīng)濟(jì)這些舉足輕重的領(lǐng)域上的改革不徹底,矛盾不斷積累,改革開放的偉業(yè)將難免功虧一簣,中國經(jīng)濟(jì)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將失去可靠的基礎(chǔ)。
改革已到深水區(qū)。如果說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則現(xiàn)在的進(jìn)一步改革將不可避免地?fù)p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國政府不但要克服強(qiáng)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tuán)的阻撓,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氣,前路挑戰(zhàn)重重。但既然“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有理由期許,更為切實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斷推進(jìn)。
中國經(jīng)濟(jì),不走回頭路。
——編者
在過去的60年,我們的國家始終是在應(yīng)對挑戰(zhàn)的努力中度過的。正是因為有市場化改革對于嚴(yán)峻挑戰(zhàn)的成功應(yīng)對,才迎來了今日的輝煌。然而,改革正未有窮期。只有認(rèn)真總結(jié)60年來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才能從容應(yīng)對我們面前的新挑戰(zhàn),再上一層樓,實現(xiàn)騰飛于世界的中國夢。
回想60年前,天安門的禮炮聲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在1949年-1953年的國民經(jīng)濟(jì)恢復(fù)時期中,曾經(jīng)災(zāi)禍縱橫的中國醫(yī)治好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國民經(jīng)濟(jì)的面貌為之一新。這使億萬民眾從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國》的歌聲:“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qiáng)。”
然而,勝利也有它的陰暗方面。恢復(fù)國民經(jīng)濟(jì)的偉大勝利,使人們滋長了虛夸冒進(jìn)的思想和高估自己的能力。在匆忙進(jìn)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chǔ)上建立的蘇聯(lián)式的集中計劃體制,非但沒有進(jìn)一步激發(fā)人民大眾的創(chuàng)造熱情,相反形成了毛澤東故主席所說“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缺乏生機(jī)與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從20世紀(jì)50年代開始,中國也同蘇聯(lián)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為改變集中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的低效率狀態(tài),試圖對經(jīng)濟(jì)體制作出一些調(diào)整。1956年提出的“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在公有制和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大框架不變條件下,進(jìn)行某些政策調(diào)整,以便給經(jīng)濟(jì)注入活力。此后20多年,才在不斷摸索中,逐漸明確了市場化改革的正確方向。然而,對于要建立什么樣的市場經(jīng)濟(jì),以及如何建立等問題,仍然存在觀點分歧。
在半個多世紀(jì)的改革過程中,中國先后采取了多種措施,變革集中計劃的經(jīng)濟(jì)體制,以及建立新的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這些措施以不同的經(jīng)濟(jì)理論和改革思路為背景,往往方向各異,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為了簡化頭緒、深入討論,本文以主要的改革措施為標(biāo)志,將中國經(jīng)濟(jì)改革的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對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進(jìn)行檢討,進(jìn)而解析中國經(jīng)濟(jì)的改革與發(fā)展之路。
第一階段是1958年至1978年,分權(quán)型命令經(jīng)濟(jì)。改革的重點,是中央政府向下屬各級政府放權(quán)讓利。
第二階段是1979年至1993年,為增量改革階段,改革主要在國有部門以外的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中推進(jìn),并以民營經(jīng)濟(jì)的成長壯大來支撐和帶動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
第三階段是從1994年至今,為整體推進(jìn)階段,以建立市場經(jīng)濟(jì)體系為目標(biāo)進(jìn)行全面改革。
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各個階段的多種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階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蘊(yùn)含后一階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階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階段改革的某些遺產(chǎn)。
上篇:分權(quán)型命令經(jīng)濟(jì)改革(1958年至1978年)
完成生產(chǎn)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之后,中央計劃經(jīng)濟(jì)得以全面推動,并在初期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其弊端也很快就顯現(xiàn)出來。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就像是一個“大企業(yè)”,中央政府是企業(yè)領(lǐng)導(dǎo),各級地方政府是企業(yè)的各級部門,本該作為獨立經(jīng)營主體的企業(yè),類似于這個“大企業(yè)”中大大小小的車間。
在這個“大企業(yè)”中,中央政府制定目標(biāo),通過計劃指令層層下達(dá)至各級“部門”,然后由各級“部門”下達(dá)給各生產(chǎn)“車間”。這是一個無比龐雜、自上而下集體行動的體系,集生產(chǎn)和消費于一體,其計劃異常復(fù)雜而難以精準(zhǔn),且缺乏調(diào)整的彈性。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看似有序,卻難免陷入低效甚至僵化的境地。
當(dāng)中央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開始拖經(jīng)濟(jì)的后腿時,中國政府試圖加以調(diào)整。不過,囿于當(dāng)時的意識形態(tài)和認(rèn)識水平,這個階段的種種調(diào)整不過是在計劃經(jīng)濟(jì)框架下的修修補(bǔ)補(bǔ)。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許多措施又往往容易變形走樣,甚至走向更為錯誤的方向。
此后的實踐證明,建立在中央計劃體制下的改良,無法根除其弊端。相反,由于嚴(yán)禁分權(quán)決策下微觀主體的必要嘗試,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每一次政策的調(diào)整,都意味著少數(shù)精英帶領(lǐng)整個社會都經(jīng)歷一次震蕩,其間缺乏應(yīng)有的緩沖和彈性。
“體制下放”
這一階段,調(diào)整的主要內(nèi)容是中央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quán)讓利。這是對計劃體制的第一次修補(bǔ),類似于“大企業(yè)”領(lǐng)導(dǎo)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級“部門”下放了自主經(jīng)營權(quán),也增加了“部門”之間的競爭,但其本質(zhì)不變,仍然是把整個國家看成一個企業(yè),主要靠行政命令進(jìn)行運(yùn)作,而不是依靠價格信號來對稀缺資源進(jìn)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極端依賴事前計劃的周密度和精準(zhǔn)度——而缺失價格信號作為客觀標(biāo)準(zhǔn),主觀計劃的優(yōu)劣無從作出合理評判。計劃本身的問題,執(zhí)行能力的問題,執(zhí)行者的動機(jī)問題,都可能造成各種無法度量的低效、浪費和損失。
1957年,中國政府根據(jù)1956年8月中共八大一次會議決定,制定了以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quán)讓利為主要內(nèi)容的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改革方案,并從1958年初開始了“體制下放”運(yùn)動,形成一種分權(quán)型的命令經(jīng)濟(jì)體制。與此同時,還發(fā)動了人民公社化運(yùn)動,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合并改組為工農(nóng)商學(xué)兵“五位一體”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了政府對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和社會的全面控制。由“體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經(jīng)濟(jì)體制,成為毛澤東在1958年發(fā)動的“大躍進(jìn)”運(yùn)動的制度基礎(chǔ)。
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quán)讓利的方針,與毛澤東在《論十大關(guān)系》講話中提出的向地方、生產(chǎn)單位和勞動群眾放權(quán)讓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后面兩種放權(quán)讓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年-1958年國內(nèi)政治事態(tài)發(fā)生變化,從而使向國有企業(yè)和職工放權(quán)讓利變成“政治上不正確”了。
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不少經(jīng)濟(jì)主管部門官員和國有企業(yè)領(lǐng)導(dǎo)曾經(jīng)懷著很大興趣研究南斯拉夫的“企業(yè)自治”試驗,希望中國能夠有所借鑒。在中共八大上,企業(yè)自治曾是一個熱門話題。然而,在1957年,隨著中共對南斯拉夫共產(chǎn)主義聯(lián)盟“自治社會主義”的批判逐步升級,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問題自然就從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改革綱領(lǐng)中刪除。
而毛澤東《論十大關(guān)系》中關(guān)于要向職工個人放權(quán)讓利,以便“調(diào)動”他們“積極性”的思想,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非斯大林化”過程中加強(qiáng)對國有企業(yè)職工物質(zhì)刺激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的。1957年,中共和蘇共在對待斯大林主義問題上的分歧已經(jīng)露出端倪,同時,“反右派”運(yùn)動后期,更把“個人主義”定為“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要求人們“斬斷名韁利索”。此時,通過對勞動者個人的“物質(zhì)刺激”來“調(diào)動積極性”,就明顯地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沖突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huán)境下,放權(quán)讓利就只能以各級地方政府為對象。這樣,向各級地方政府下放權(quán)力和與此相聯(lián)系的利益,就成為1958年改革的基本內(nèi)容,而“體制改革”也就被定義為“體制下放”。這種改革思路,對中國以后的經(jīng)濟(jì)體制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是發(fā)動“大躍進(jìn)”運(yùn)動的一次會議,同時也是開始“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改革”來“為躍進(jìn)運(yùn)動準(zhǔn)備體制基礎(chǔ)”的一次會議。會議原則通過了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五人小組組長陳云起草的《關(guān)于改進(jìn)工業(yè)管理體制的規(guī)定》《關(guān)于改進(jìn)商業(yè)管理體制的規(guī)定》和《關(guān)于劃分中央與地方對財政管理權(quán)限的規(guī)定》,并將這三個規(guī)定草案提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wù)委員會。總的精神,就是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quán)讓利,把權(quán)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機(jī)關(guān),以便進(jìn)一步發(fā)揮地方和企業(yè)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地制宜完成國家統(tǒng)一計劃。11月1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zhǔn)它們自1958年起施行。
1958年的“體制下放”,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下放計劃管理權(quán)。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發(fā)布《關(guān)于改進(jìn)計劃管理體制的規(guī)定》,要求將原來由國家計委統(tǒng)一平衡、逐級下達(dá)的計劃管理制度改變?yōu)椤耙缘貐^(qū)綜合平衡為基礎(chǔ)的、專業(yè)部門和地區(qū)相結(jié)合的計劃管理制度”,實行以地區(qū)為主、自下而上逐級編制和進(jìn)行平衡,使地方經(jīng)濟(jì)能夠“自成體系”。這份文件規(guī)定,地方政府可以對本地區(qū)的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指標(biāo)進(jìn)行調(diào)整;可以對本地區(qū)內(nèi)的建設(shè)規(guī)模、建設(shè)項目、投資使用等進(jìn)行統(tǒng)籌安排;可以對本地區(qū)內(nèi)的物資進(jìn)行調(diào)劑使用;可以對重要產(chǎn)品的超產(chǎn)部分,按照一定分成比例自行支配使用。
——下放企業(yè)管轄權(quán)。195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工業(yè)企業(yè)下放的幾項規(guī)定》,提出國務(wù)院各主管部門所管理的企業(yè),除極少數(shù)重要的、特殊的和試驗性的企業(yè)仍歸中央繼續(xù)管理外,一律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這樣,原來由中央各部委所屬的企業(yè)和事業(yè)單位,有88%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有的還下放到街道和公社;中央直屬企業(yè)的工業(yè)產(chǎn)值占整個工業(yè)產(chǎn)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為1958年的13.8%。
——下放物資分配權(quán)。一是減少由國家計委統(tǒng)一分配的物資(“統(tǒng)配物資”或稱“一類物資”)和由國務(wù)院各部管理的物資(“部管物資”或稱“二類物資”)的品種和數(shù)量。二是對保留下來的統(tǒng)配、部管物資,也由過去中央“統(tǒng)配”,改為各省、市、自治區(qū)“地區(qū)平衡,差額調(diào)撥”。三是在供應(yīng)方面,除少數(shù)部門外,都由地方政府的計劃機(jī)關(guān)負(fù)責(zé)分配和調(diào)撥。
——下放基本建設(shè)項目的審批權(quán)、投資管理權(quán)和信貸管理權(quán)。對于地方興辦的限額以上項目,只需將簡要計劃任務(wù)書報請國家計委批準(zhǔn),其余由地方審批;限額以下的項目,完全由地方自行決定。允許地方政府在中央下?lián)苜Y金和地方自籌資金總額的范圍內(nèi)興辦各種事業(yè),包括限額以上的大型項目。地方銀行可以根據(jù)各地“生產(chǎn)大上”的要求,“需要多少就貸多少,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貸”。
——下放財政權(quán)和稅收權(quán)。為了增加地方的財力,擴(kuò)大地方政府的財權(quán),決定實行“包稅制”。
——下放勞動管理權(quán)。改變勞動用工計劃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統(tǒng)一制定、層層下達(dá)的做法,各地招工計劃經(jīng)省、自治區(qū)和中央直轄市確定以后即可執(zhí)行。
1958年的改革,雖然把向企業(yè)放權(quán)讓利從它的公開綱領(lǐng)中刪除,但實際上除了向地方政府放權(quán)讓利,也采取了一些向企業(yè)放權(quán)讓利的措施,包括:(1)減少指令性計劃指標(biāo),將國家計委層層下達(dá)給工業(yè)企業(yè)的指令性指標(biāo)由12項減為主要產(chǎn)品產(chǎn)量、職工總數(shù)、工資總額、利潤等4項;(2)將原來分不同行業(yè)按一定比例從利潤中提取少量“企業(yè)獎勵金”(廠長基金)的制度,改為一戶一率的“全額利潤留成”制度;(3)擴(kuò)大了企業(yè)的人事安排權(quán),除企業(yè)主管人員和主要技術(shù)人員外,其他一切職工均由企業(yè)負(fù)責(zé)管理,企業(yè)還有權(quán)在不增加職工總數(shù)的條件下自行調(diào)整機(jī)構(gòu)和人員;(4)部分資金可以由企業(yè)調(diào)劑使用,企業(yè)有權(quán)增減和報廢固定資產(chǎn)。
“放-亂-收-死”
調(diào)整之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資源和自主權(quán),各級企業(yè)的自主權(quán)利也有了相應(yīng)的增加,但仍似總體計劃下地方政府指揮的“車間”。掌控著企業(yè)和多種資源的地方政府之間有競爭,卻既無價格機(jī)制作為信號引導(dǎo)和評判標(biāo)準(zhǔn),又無優(yōu)勝劣汰的有效約束,于是沒有朝著創(chuàng)造財富的方向發(fā)展,卻形成了“大躍進(jìn)”的制度和組織基礎(chǔ)。另一方面,由少數(shù)精英主導(dǎo)的計劃經(jīng)濟(jì),本身又極易受限于精英們的意識形態(tài)、認(rèn)識水平、政治立場甚至情緒波動,容易大起大落。這一階段,中國經(jīng)濟(jì)的進(jìn)程更是被深深打上了政治活動的烙印。
在保持計劃經(jīng)濟(jì)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總框架不變的條件下,向地方政府層層分權(quán)所形成的分權(quán)型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和農(nóng)村人民公社一起,構(gòu)成了“大躍進(jìn)”的制度基礎(chǔ)。在這種體制支持下,各級政府響應(yīng)毛澤東“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號召,充分運(yùn)用調(diào)動資源的權(quán)力,大上基本建設(shè)項目,大量招收職工,無償調(diào)撥農(nóng)民的資源,來完成“鋼鐵生產(chǎn)一年翻一番”之類絕無可能實現(xiàn)的高計劃指標(biāo)。結(jié)果很快爆發(fā)了各地區(qū)、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zhàn),“一平(平均主義)、二調(diào)(無償調(diào)撥)、三收款”的“共產(chǎn)風(fēng)”盛行,經(jīng)濟(jì)秩序一片混亂。
由于經(jīng)濟(jì)混亂,經(jīng)濟(jì)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費大量資源所換得的,只是一大堆為了邀功請賞而制造的虛夸數(shù)字。后來的事實證明,當(dāng)時號稱已經(jīng)完成的鋼鐵、糧食等生產(chǎn)指標(biāo),完全是虛假的。
然而,一些領(lǐng)導(dǎo)人仍然陶醉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在食品供需出現(xiàn)短缺,全國性饑荒即將爆發(fā)的時刻,毛澤東卻在思考“糧食多了怎么辦”的問題,提出采取“休耕制”“敞開肚皮吃飯”一類解決辦法。在人民公社中,紛紛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辦法。
1958年末,這種一意孤行做法的消極后果終于顯現(xiàn),生產(chǎn)下降,大批工商企業(yè)出現(xiàn)虧損,生活必需品供應(yīng)不足,經(jīng)濟(jì)陷入嚴(yán)重困難。
面對這種嚴(yán)峻局面,中共中央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擴(kuò)大會議和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要求“壓縮空氣”、糾正“左”的偏向。
1959年7月到8月間,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jǐn)U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提出這次會議要進(jìn)一步總結(jié)“大躍進(jìn)”以來的經(jīng)驗,而且承認(rèn)“大躍進(jìn)”存在“沒有搞平衡,打亂了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的比例關(guān)系”“人權(quán)、財權(quán)、商權(quán)、工權(quán)等四大權(quán)力下放過多”等缺點。可是,后來因為政治局委員彭德懷致信毛澤東,要求認(rèn)真總結(jié)“大躍進(jìn)”和人民公社化運(yùn)動的經(jīng)驗教訓(xùn),毛澤東臨時決定延長會期,對彭德懷的“右傾機(jī)會主義反黨活動”進(jìn)行嚴(yán)厲批判,由此掀起了全國范圍的“反右傾運(yùn)動”。整個政治氣氛從“糾‘左’”轉(zhuǎn)向“反‘右’”。
“反右傾”運(yùn)動導(dǎo)致的第二次“共產(chǎn)風(fēng)”,使經(jīng)濟(jì)和社會狀況進(jìn)一步惡化。1959年全國共生產(chǎn)糧食1700億公斤,比1958年的實際產(chǎn)量2000億公斤減少了300億公斤;1960年糧食產(chǎn)量降到1435億公斤,比1951年的1437億公斤還低,全國普遍發(fā)生饑荒。
由于封鎖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鎮(zhèn)地區(qū)廣泛出現(xiàn)因營養(yǎng)不良導(dǎo)致的浮腫病,農(nóng)村地區(qū)則造成2000萬至4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秋季,黨中央終于確定對國民經(jīng)濟(jì)實行“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恢復(fù)了由陳云任組長的中共中央財經(jīng)領(lǐng)導(dǎo)小組,采取堅決措施來克服“大躍進(jìn)”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嚴(yán)重經(jīng)濟(jì)困難。
“八字方針”的實施,主要采取了以下手段:
——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市、地、縣五級干部參加的“擴(kuò)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表示承擔(dān)錯誤責(zé)任以平息干部的怨氣,同時要求加強(qiáng)團(tuán)結(jié),加強(qiáng)紀(jì)律,加強(qiáng)集中統(tǒng)一,做好工作,戰(zhàn)勝困難。與此同時,恢復(fù)了以陳云為首的中共中央財經(jīng)領(lǐng)導(dǎo)小組,統(tǒng)管“調(diào)整國民經(jīng)濟(jì)”工作。
——根據(jù)國務(wù)院和中央財經(jīng)領(lǐng)導(dǎo)小組建立比1950年統(tǒng)一財經(jīng)時“更嚴(yán)更緊”體制的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門在財政、信貸和企業(yè)管轄權(quán)等方面收回在1958年改革中下放的權(quán)力。例如,發(fā)布了加強(qiáng)計劃紀(jì)律的“十項規(guī)定”和一系列收回原來下放權(quán)力的決定,對金融、財政和統(tǒng)計實行中央的垂直領(lǐng)導(dǎo)。1958年下放給地方管理的企業(yè),也大多回到中央由各行業(yè)部管理。
——憑借這一套高度集中化的體制實行稀缺資源的再配置,主要的措施是:大煉鋼鐵中興建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冶煉設(shè)施全部“下馬”;將“大躍進(jìn)”中“招之即來”、進(jìn)入城鎮(zhèn)就業(yè)的約3000萬農(nóng)民工“揮之即去”,全部退回農(nóng)村;對城市工業(yè)企業(yè)進(jìn)行“關(guān)、停、并、轉(zhuǎn)”調(diào)整。
經(jīng)過幾個月的調(diào)整,經(jīng)濟(jì)逐漸穩(wěn)定下來,并在1964年大體上得到恢復(fù)。
不過,在人們慶幸經(jīng)濟(jì)秩序恢復(fù)的同時,卻發(fā)現(xiàn)集中計劃經(jīng)濟(jì)的所有弊病又都卷土重來。于是又醞釀再次進(jìn)行改革。
但是,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jié)束,由于存在社會主義只能采取行政命令配置資源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障礙,市場取向改革很難在政治上被接受。于是,進(jìn)行向地方政府下放計劃權(quán)力,幾乎成了惟一可能的改革選擇。因此,此后仍然多次進(jìn)行過類似于1958年的行政性分權(quán)改革,例如,1970年以“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命”為口號的大規(guī)模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改革,就是1958年“體制下放”的重演。
總之,1958年至1976年期間的多次“體制下放”,無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亂和隨后重新集中告終。在“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循環(huán)下,形成了“放-亂-收-死”的怪圈。
制度反思
“放-亂-收-死”的魔咒揮之不去,促使人們深刻反思,這種情況可能是由以公有制為基礎(chǔ)的集中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所固有的缺陷所決定的,甚至進(jìn)一步摒棄固有的思維模式。在這種思考的基礎(chǔ)上,人們的思想認(rèn)識逐漸深入和提高,并為以后的改革實踐提供了思想基礎(chǔ)。
中國理論界第一個對“體制下放”思路提出批評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是孫冶方。他在1961年給中國經(jīng)濟(jì)工作領(lǐng)導(dǎo)人的上書中指出,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的中心問題,不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quán)力應(yīng)當(dāng)如何劃分,而是“作為獨立核算單位的企業(yè)的權(quán)力、責(zé)任和它們同國家的關(guān)系問題,也即是企業(yè)的經(jīng)營管理權(quán)問題”。在孫冶方看來,只有讓企業(yè)獲得權(quán)力,“才能調(diào)動其積極因素,全面地把國家交給它的擔(dān)子挑起來。”
不過,孫冶方的這種批評,并不是從稀缺資源有效配置和使用的角度,而是在“放權(quán)讓利”和“調(diào)動積極性”的理論框架下進(jìn)行的。因此,他并沒有從理論上講清楚為什么向地方政府放權(quán)讓利不能解決問題,而向企業(yè)放權(quán)讓利,“擴(kuò)大企業(yè)的管理權(quán)”就能提高國民經(jīng)濟(jì)的效率。而且當(dāng)時在極“左”路線統(tǒng)治下,即使孫冶方這種要求在計劃經(jīng)濟(jì)框架下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的主張,也不可能被當(dāng)局所接受。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觀點后不久,就被說成是“比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的“修正主義分子”而受到批判和迫害。在1976年極“左”路線統(tǒng)治傾覆后,孫冶方的意見才被許多人所接受。
直到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人們才開始運(yùn)用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去分析“體制下放”的利弊得失。在這一爭論中,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認(rèn)識:
一種觀點認(rèn)為,“體制下放”對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特別是非國有經(jīng)濟(jì)成分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例如,上世紀(jì)80年代初實行財政“分灶吃飯”,向地方政府下放財權(quán),導(dǎo)致了地區(qū)間的競爭,進(jìn)而又引發(fā)了民營企業(yè)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在地方政府擁有某種財政獨立性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本地利益,運(yùn)用手中的權(quán)力使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得到融資、生產(chǎn)、銷售等方面的某些保護(hù)或便利,是中國非國有企業(yè)迅速發(fā)展的重要原因。張五常教授在他總結(jié)中國市場化改革30年的論文中,給予向地方政府放權(quán)讓利(層層承包)以極高的評價,認(rèn)為正是由此造成的“縣際競爭”促成了中國經(jīng)濟(jì)的迅速發(fā)展。
持另一種觀點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對那種把“體制下放”作為改革主線的想法和做法持批評態(tài)度。他們認(rèn)為,不應(yīng)當(dāng)籠統(tǒng)地把改革的目標(biāo)規(guī)定為“分權(quán)”,而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兩種分權(quán),即市場經(jīng)濟(jì)下的分權(quán)狀態(tài)(“經(jīng)濟(jì)性分權(quán)”)和計劃經(jīng)濟(jì)下的分權(quán)狀態(tài)(“行政性分權(quán)”)。能夠從根本上改善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狀況和提高整體效率的分權(quán),只能是經(jīng)濟(jì)性分權(quán),而不能是行政性分權(quán)。他們的論證如下:
——從計劃經(jīng)濟(jì)的角度看,要使這種經(jīng)濟(jì)體制多少行得通,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在集中進(jìn)行經(jīng)濟(jì)計算的基礎(chǔ)上編制和下達(dá)計劃,并且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政出多門,按照地方的利益和長官意志配置資源,結(jié)果只會使整個經(jīng)濟(jì)陷于混亂。總之,計劃經(jīng)濟(jì)的資源配置方式在本質(zhì)上要求集權(quán)。分權(quán)的計劃經(jīng)濟(jì),是較之集權(quán)的計劃經(jīng)濟(jì)還要糟的計劃經(jīng)濟(jì)。要擺脫“集權(quán)的計劃經(jīng)濟(jì)就是死,分權(quán)的計劃經(jīng)濟(jì)就是亂”這一兩難境地,惟一的出路是進(jìn)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市場制度,使得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chǔ)性的作用。
——從建立市場制度的觀點看,市場經(jīng)濟(jì)是一種分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在那里,個人和企業(yè)等獨立的市場主體根據(jù)市場價格信號和自身的利益,自主地作出生產(chǎn)什么、生產(chǎn)多少、為誰生產(chǎn)等決策。行政性分權(quán)在短時期中的確有激勵地方政府積極支持民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作用。但是,由此形成了企業(yè)與當(dāng)?shù)卣P(guān)系過于緊密的體制,既會促成地方保護(hù)主義的蔓延,也容易滋生腐敗。
從后一種觀點看來,中國在1958年、1970年和1980年實行的行政性分權(quán)的財政體制,的確為市場關(guān)系在地區(qū)之間競爭的縫隙中成長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又使地方保護(hù)主義和市場割據(jù)的傾向得以滋長。到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地區(qū)間相互封鎖、分割市場以及對本地企業(yè)實行行政保護(hù)等行為,已經(jīng)成為形成國內(nèi)統(tǒng)一市場(integratedmarket,即一體化的市場)的重大障礙。甚至有人把中國經(jīng)濟(jì)稱為“諸侯經(jīng)濟(jì)”。
因此,對于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的中國來說,當(dāng)市場力量增強(qiáng)到一定程度,打破地區(qū)封鎖和形成統(tǒng)一市場就成為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wù)。
中篇:增量改革(1979年至1993年)
在計劃體制內(nèi)多次徒勞無功的改良嘗試和震蕩,迫使中國政府進(jìn)行深刻的反思,并考慮其他方向的變革。允許微觀主體在公有體制之外進(jìn)行嘗試,成為這一階段改革極為重要的積極因素,在這個基礎(chǔ)上,才有了非國有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空間,以及更為系統(tǒng)的增量改革戰(zhàn)略。
從小崗村的農(nóng)地改革試驗開始,允許人們在公有體制之外進(jìn)行嘗試,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抉擇。在分散的微觀主體成功嘗試的基礎(chǔ)上加以系統(tǒng)性的理論總結(jié),并逐漸以制度化的形式將這些成果固定并加以推廣,是一個偉大的經(jīng)驗。這種看似沒有理論指導(dǎo)的“摸著石頭過河”策略,蘊(yùn)藏著一個內(nèi)在合理性,即允許分散的微觀主體分頭探索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并且一旦這些探索取得成功,整個社會可以分享其成果。
“增量”的強(qiáng)大生命力一旦釋放,便迅速為社會所認(rèn)可,并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資源積聚,不但逐漸成為國民經(jīng)濟(jì)的一個重要支撐點,更在與“存量”的競爭中占了上風(fēng)。至關(guān)重要的一點是,能夠反映稀缺資源程度,并引導(dǎo)資源配置的市場價格體系在“增量”中逐漸形成,最終在大多數(shù)領(lǐng)域內(nèi)將原有的公有經(jīng)濟(jì)徹底融入了新的價格體制。改革開放的大門一旦打開,新舊兩種體制的優(yōu)劣立判;在經(jīng)濟(jì)力量的牽引和推動下,就無法再回頭了。
1976年10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結(jié)束,使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jī),此后的經(jīng)濟(jì)社會體制改革,是從擴(kuò)大國有企業(yè)自主權(quán)開始的。在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試驗不成功、國有經(jīng)濟(jì)改革停頓不前的情況下,中國領(lǐng)導(dǎo)把取得進(jìn)展的希望放到了非國有經(jīng)濟(jì)方面,力圖通過一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使民營經(jīng)濟(jì)得以破土而出并逐漸發(fā)展壯大,成為中國新的經(jīng)濟(jì)增長點。我們把這種改革戰(zhàn)略叫做增量改革戰(zhàn)略。往后中國經(jīng)濟(jì)改革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一新的改革戰(zhàn)略有關(guān)。不過,由這種改革戰(zhàn)略長期延續(xù)所帶來的“雙軌體制”,也造成了一系列很難解決的問題。
“體制內(nèi)改革”受挫
傳統(tǒng)的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固然已經(jīng)難以為繼,但無論是意識形態(tài)、人們的認(rèn)識水平,還是原有體制的慣性,都決定了新的經(jīng)濟(jì)體制不可能從天而降。當(dāng)改革已成大勢所趨,改革的方向卻存在爭議。究竟是繼續(xù)在原有體制下進(jìn)一步改良,把重點從“給地方政府放權(quán)讓利”改為“給企業(yè)更多的自主權(quán)”,還是在計劃指導(dǎo)下充分發(fā)揮市場調(diào)節(jié)的作用,甚至全面建立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
改良的主張在辯論和實踐上一度占據(jù)上風(fēng),但其固有的缺陷也很快再次顯現(xiàn)。與此同時,包括產(chǎn)權(quán)改革萌芽的市場化改革實踐,則開始在民間小心而積極地嘗試,并顯現(xiàn)出勃勃生機(jī)。
十年“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由于把整個社會變成牢籠和使上億人遭到迫害,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對“全面專政”制度徹底絕望,全社會一致認(rèn)為舊路線和舊體制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須通過改革開放變革救亡圖存的共識。這正像鄧小平所說:“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過去二十多年的封閉狀況必須改變。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zāi)難的教訓(xùn)太深刻了。”
啟動改革的第一項行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發(fā)動解除極“左”思想束縛的“思想解放運(yùn)動”。當(dāng)時主持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支持《光明日報》在1978年5月11日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的評論員文章,以此為開端,全國掀起了一場以“解放思想”為基本內(nèi)容的啟蒙運(yùn)動。“思想解放”意味著原來認(rèn)為天經(jīng)地義的“階級斗爭為綱”“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之類的理論是可以被懷疑的,原來認(rèn)為神圣不可侵犯的計劃經(jīng)濟(jì)制度和“對黨內(nèi)外資產(chǎn)階級(包括所謂‘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全面專政”的政治制度是可以改變的。這次運(yùn)動打破了數(shù)十年僵化思想的束縛,激發(fā)了工人、農(nóng)民、知識分子和機(jī)關(guān)干部開動腦筋去尋找挽救危亡、求得發(fā)展的出路。他們認(rèn)真總結(jié)自己的教訓(xùn),學(xué)習(xí)他國的經(jīng)驗,提出了各種各樣變革的設(shè)想。中國政府也派出了許多代表團(tuán),分別到美國、西歐、東歐和東亞國家去考察取經(jīng),力圖汲取它們促進(jìn)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方面的經(jīng)驗。
在這種氛圍下,決策層提出了改革問題。1978年7月-9月召開的“國務(wù)院務(wù)虛會”印發(fā)了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國進(jìn)行企業(yè)改革和引進(jìn)外資促進(jìn)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的材料。國務(wù)院副總理李先念在務(wù)虛會上作總結(jié)報告時指出,當(dāng)務(wù)之急,是既要大幅度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chǎn)力,也要多方面改變生產(chǎn)關(guān)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nóng)業(yè)企業(yè)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nóng)業(yè)企業(yè)的管理方式,改變?nèi)藗兊幕顒臃绞胶退枷敕绞健?/p>
至于如何進(jìn)行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大致上有兩種不同的想法:
第一種是以擴(kuò)大國有企業(yè)自主權(quán)為主要內(nèi)容。
在“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經(jīng)濟(jì)政策的“撥亂反正”中,絕大多數(shù)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和黨政領(lǐng)導(dǎo)人認(rèn)同孫冶方的經(jīng)濟(jì)思想,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把擴(kuò)大企業(yè)經(jīng)營自主權(quán)和提高企業(yè)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李先念在“國務(wù)院務(wù)虛會”的總結(jié)中指出:“過去20多年的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缺點,是把注意力放在行政權(quán)力的分割和轉(zhuǎn)移上,由此形成了‘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環(huán)’。在今后的改革中,一定要給予各企業(yè)以必要的獨立地位,使它們能夠自動地而不是被動地執(zhí)行經(jīng)濟(jì)核算制度,提高綜合經(jīng)濟(jì)效益。”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也指出:舊經(jīng)濟(jì)體制的“嚴(yán)重缺點是權(quán)力過于集中”,“應(yīng)當(dāng)有領(lǐng)導(dǎo)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nóng)業(yè)企業(yè)在國家統(tǒng)一計劃的指導(dǎo)下有更多的經(jīng)營管理自主權(quán)”,以便“充分發(fā)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yè)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使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的各個部門、各個環(huán)節(jié)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fā)展起來”。
多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例如,時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工業(yè)經(jīng)濟(jì)研究所所長的馬洪在1979年9月的一篇論文中提出,“改革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要從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入手”,擴(kuò)大企業(yè)在人、財、物和計劃等方面的決策權(quán)力。同一研究所的副所長蔣一葦針對中央集權(quán)的“國家本位論”和行政性分權(quán)的“地方本位論”,提出了“企業(yè)本位論”。他認(rèn)為,改革的方向應(yīng)當(dāng)是“以企業(yè)(包括工業(yè)企業(yè)、商業(yè)企業(yè)、農(nóng)業(yè)企業(yè)等等)作為基本的經(jīng)濟(jì)單位。企業(yè)在國家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和監(jiān)督下,實行獨立經(jīng)營、獨立核算,一方面享受應(yīng)有的權(quán)利,一方面確保完成對國家應(yīng)盡的義務(wù)”。他主張:“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是企業(yè)全體職工的聯(lián)合體,……企業(yè)的權(quán)利是掌握在全體職工的手里”實行獨立經(jīng)營、獨立核算。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經(jīng)濟(jì)研究所副所長董輔則把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歸結(jié)為改變“全民所有制的國家所有制形式”,認(rèn)為全民所有制經(jīng)濟(jì)單位“應(yīng)該具有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下的獨立性,實行全面的獨立的嚴(yán)格的經(jīng)濟(jì)核算”;“各經(jīng)濟(jì)組織中的勞動者有權(quán)在維護(hù)和增進(jìn)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在統(tǒng)一計劃的指導(dǎo)下,結(jié)合本單位和自身的利益的考慮直接參加經(jīng)營。”
另一種意見的思考范圍更加寬廣,認(rèn)為改革的目標(biāo)應(yīng)當(dāng)是建立一種完全不同于蘇聯(lián)模式的新經(jīng)濟(jì)體制:社會主義的商品經(jīng)濟(jì)。例如,中國經(jīng)濟(jì)學(xué)界宿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長期擔(dān)任中央政府經(jīng)濟(jì)領(lǐng)導(dǎo)工作的薛暮橋在1979年出版的、對當(dāng)時的改革思想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問題研究》中指出,中國經(jīng)濟(jì)改革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企業(yè)(包括集體經(jīng)濟(jì)單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業(yè)成為有活力的基層經(jīng)營管理單位;另一個是國民經(jīng)濟(jì)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適合于社會化大生產(chǎn)的要求。”他在1980年初夏為國務(wù)院體制改革辦公室起草的《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提出:“我國現(xiàn)階段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是生產(chǎn)資料公有制占優(yōu)勢,多種經(jīng)濟(jì)成分并存的商品經(jīng)濟(jì)。我國經(jīng)濟(jì)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yīng)當(dāng)是,在堅持生產(chǎn)資料公有制占優(yōu)勢的條件下,按照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jì)的要求,自覺運(yùn)用價值規(guī)律,把單一的計劃調(diào)節(jié)改為在計劃指導(dǎo)下,充分發(fā)揮市場調(diào)節(jié)的作用。”薛暮橋在1980年9月召開的各省市區(qū)第一書記會議上就這個《意見》作說明時說:“所謂經(jīng)濟(jì)體制的改革,是要解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yīng)當(dāng)建立什么形式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根本方向。將來起草的經(jīng)濟(jì)管理體制改革規(guī)劃,是一部‘經(jīng)濟(jì)憲法’。”薛暮橋起草的《意見》,得到了胡耀邦等領(lǐng)導(dǎo)人的支持,但是這種想法并沒有最終形成政府的決定。[$Page_Split$]
另一位對于中國經(jīng)濟(jì)改革理論和政策有著重要影響的是杜潤生,他長期從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研究,曾經(jīng)輔佐過被毛澤東批評為1952年到1962年“十年一貫制”地“右傾”的中國農(nóng)村工作領(lǐng)導(dǎo)人鄧子恢。杜潤生早在上世紀(jì)80年代初期從推行農(nóng)村承包制開始,重新發(fā)揮他在制定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政策方面的影響。他廣泛吸收了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成果,主張全面建立市場經(jīng)濟(jì)體系。
長期在宣傳部門工作的于光遠(yuǎn)從恢復(fù)馬克思主義“原義”的角度批評斯大林、毛澤東的經(jīng)濟(jì)理論和經(jīng)濟(jì)體制。他和他的追隨者更多地傾向于南斯拉夫共產(chǎn)主義聯(lián)盟提出的“企業(yè)自治”和“社會所有制”的經(jīng)濟(jì)體制。
在上述兩種思想中,第一種思想更加受到實際工作者和國有企業(yè)領(lǐng)導(dǎo)人的支持。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四川省率先開始了“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的改革。1978年10月,四川省選擇了六家國有工廠進(jìn)行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試點,取得了明顯成績。隨后,四川省的試驗擴(kuò)大到100家國有企業(yè)。1979年7月,國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擴(kuò)大國營工業(yè)企業(yè)經(jīng)營自主權(quán)的若干規(guī)定》等文件,要求各地方、各部門選擇一些企業(yè)按照這些規(guī)定進(jìn)行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的試驗。到1979年底,全國試點工業(yè)企業(yè)達(dá)到4200個。到1980年,又?jǐn)U大到6600個,它們的產(chǎn)值占全國預(yù)算內(nèi)工業(yè)產(chǎn)值的60%、利潤占全國工業(yè)企業(yè)利潤的70%。
“擴(kuò)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改革的內(nèi)容與1965年蘇聯(lián)總理柯西金領(lǐng)導(dǎo)的“完全經(jīng)濟(jì)核算制”改革大體類似,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簡化計劃指標(biāo),放松計劃控制;二是擴(kuò)大資金數(shù)額,強(qiáng)化對企業(yè)和職工的物質(zhì)刺激。
在開始的幾個月內(nèi),“擴(kuò)權(quán)”顯著提高了試點企業(yè)職工增產(chǎn)增收的積極性。但是,這種和1965年蘇聯(lián)的“柯西金改革”相類似的做法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現(xiàn)出來。在新體制下?lián)碛心承┳灾鳈?quán)的企業(yè)并未受市場公平競爭的約束,也不處在價格信息的引導(dǎo)之下,因此,企業(yè)“積極性”的發(fā)揮往往不一定有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加之當(dāng)時對發(fā)展工業(yè)要求過高過急,增加投資的壓力很大,造成了總需求失控,財政赤字劇增,經(jīng)濟(jì)秩序陷于混亂。
“體制外先行”戰(zhàn)略
旱路不通走水路。當(dāng)體制內(nèi)改革的嘗試遭遇瓶頸時,決定整個改革方向的中央領(lǐng)導(dǎo)表現(xiàn)出足夠的包容度和靈活性。以微觀主體的自發(fā)探索為第一推動力,中央政府從默許到制度化承認(rèn),逐步在公有制之外推行市場化取向的變革。以家庭承包制度為基礎(chǔ)的農(nóng)村土地改革,率先推動了產(chǎn)權(quán)制度層面的變革,并迅速在國有部門之外形成燎原之勢。此后,對外開放與對內(nèi)改革齊頭并進(jìn),私有產(chǎn)權(quán)和計劃之外的價格體系得到事實上的認(rèn)可,并不斷發(fā)展壯大。非公部門和市場價格對公有部門和命令價格體系形成有力的沖擊,成為公有制改革的強(qiáng)大外在壓力,但前兩者與后兩者長時間仍然并行運(yùn)行,分別形成經(jīng)濟(jì)體制與價格體系的“雙軌”。
當(dāng)國有企業(yè)的擴(kuò)大自主權(quán)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已經(jīng)掌握領(lǐng)導(dǎo)權(quán)力的鄧小平改變了改革的重點,從城市的國有經(jīng)濟(jì)轉(zhuǎn)向農(nóng)村的非國有經(jīng)濟(jì),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轉(zhuǎn)變,是對農(nóng)村包產(chǎn)到戶由禁止到允許的轉(zhuǎn)變。
1980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允許農(nóng)民根據(jù)自愿實行家庭承包制度。此后僅僅兩年時間,家庭承包制,即家庭農(nóng)場制就在全國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chǔ)”的制度。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從此氣象一新。在此基礎(chǔ)上,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也蓬勃發(fā)展起來。從這時起,中國開始采取了一種有別于蘇東國家以改革現(xiàn)有國有企業(yè)為主的新戰(zhàn)略,這就是不在國有經(jīng)濟(jì)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驟,而把改革重點放到非國有部門去,在那里創(chuàng)建市場導(dǎo)向的企業(yè),并依托它們實現(xiàn)經(jīng)濟(jì)增長。這種戰(zhàn)略被稱為“增量改革”戰(zhàn)略或“體制外先行”戰(zhàn)略。
當(dāng)增量改革戰(zhàn)略在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國黨政領(lǐng)導(dǎo)將這種經(jīng)驗推廣到其他部門,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國有經(jīng)濟(jì)主體地位的條件下,逐步放開對私人創(chuàng)業(yè)活動的限制,加上在這之前已經(jīng)開始的對外資開放國內(nèi)市場,為民營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開拓出一定的空間,使非國有經(jīng)濟(jì)(民營經(jīng)濟(jì))得以自下而上地發(fā)展起來。
發(fā)展非國有經(jīng)濟(jì)的戰(zhàn)略,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允許非國有企業(yè)成長。
是否允許非公有經(jīng)濟(jì)存在和發(fā)展,在中國一直是一個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問題。即使在1976年以后幾年的“撥亂反正”時期,“愈大愈公愈好”“割資本主義尾巴”“要讓資本主義絕種”等毛澤東時代的教條仍然統(tǒng)治著人們的觀念。因此,在改革開始時期,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發(fā)展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包產(chǎn)到戶”取得成功以后,這種思想禁錮才被進(jìn)一步突破。1983年在事實上取消了對私人企業(yè)雇工人數(shù)的限制。也就是說,私有企業(yè)取得了合法地位。在那以后,私有部門得到了愈來愈快的發(fā)展。
第二,營造“經(jīng)濟(jì)特區(qū)”的“小氣候”,實現(xiàn)部分地區(qū)與國際市場對接。
在各國以往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史中,國內(nèi)市場的發(fā)展往往是曠日持久的,需要很長時期才能形成。本來舊中國的商業(yè)文化傳統(tǒng)就十分薄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經(jīng)歷了30年的計劃經(jīng)濟(jì)實踐,市場力量幾乎被消滅殆盡,國內(nèi)市場的形成就更加困難。面對這種情況,要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短時期內(nèi)形成國內(nèi)市場并全面與國際市場對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國家建立出口加工區(qū)和自由港的經(jīng)驗,利用沿海地區(qū)毗鄰港澳臺和海外華僑、華人眾多的優(yōu)勢,通過營造地區(qū)性的“小氣候”作為對外開放的基地。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布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積極發(fā)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jīng)濟(jì)合作。1979年,中國政府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以便發(fā)揮它們毗鄰香港、澳門的區(qū)位優(yōu)勢;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四個經(jīng)濟(jì)特區(qū);1985年又決定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對外開放以來,逐漸在沿海、沿江、沿邊地區(qū)形成了有一定縱深的開放地帶。
對外開放促進(jìn)了國內(nèi)經(jīng)濟(jì)改革。參與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使中國的經(jīng)營管理人員對國際市場有了更好的了解,同時也使他們對提高產(chǎn)品質(zhì)量和降低生產(chǎn)成本,產(chǎn)生了緊迫感。為了在競爭中生存,取得更大的自主權(quán)和改進(jìn)經(jīng)營管理成為十分必要的事情。參與進(jìn)出口貿(mào)易競爭,也促使中國國內(nèi)價格結(jié)構(gòu)向國際市場看齊,加快了國內(nèi)價格改革的進(jìn)程。
第三,建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綜合試驗區(qū),實行改革開放的“地區(qū)推進(jìn)”。
在市場取向的改革不能在全國同時鋪開,改革又需要有系統(tǒng)性的條件下,選擇沿海某些市場一向比較發(fā)達(dá)、又具有較好的對外開放條件的地區(qū)建立改革試驗區(qū),在改革和開放這兩個方面結(jié)合運(yùn)用前面講到的兩種做法,使市場經(jīng)濟(jì)體系能夠多少完整地建立起來,然后通過它們的示范和輻射,帶動內(nèi)地的改革和開放。自從1985年廣東省的廣州、佛山、江門、湛江等四個市被國務(wù)院確定為“全國經(jīng)濟(jì)體制綜合改革城市”,經(jīng)過十來年的發(fā)展,到上世紀(jì)90年代中期,中國從遼東半島到廣西沿海一線涌現(xiàn)了已經(jīng)初步形成成片市場、經(jīng)濟(jì)具有很強(qiáng)活力的地區(qū)。在內(nèi)地,也出現(xiàn)了某些初步“搞活”的地區(qū)。市場力量的作用,正在從這些地區(qū)向四面八方輻射,它們已經(jīng)成為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強(qiáng)大基地。
實施增量改革戰(zhàn)略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民營經(jīng)濟(jì)得以從下而上地成長起來,并且日益發(fā)展壯大。上世紀(jì)80年代,中國民營工業(yè)的增長率約為國有工業(yè)的2倍。到80年代中期,非國有經(jīng)濟(jì)成分無論在工業(yè)生產(chǎn)中還是在整個國民經(jīng)濟(jì)中,都占據(jù)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工業(yè)中,其產(chǎn)出份額已經(jīng)達(dá)到三分之一以上;在零售商業(yè)中,非國有成分的份額增長得更快。
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給中國經(jīng)濟(jì)帶來了高速增長。在1978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年均增長14.6%,城鎮(zhèn)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3.1%。
“雙軌制”的形成
非公經(jīng)濟(jì)與市場價格的持續(xù)發(fā)展,不可避免地與公有經(jīng)濟(jì)和命令價格產(chǎn)生直接的沖突。“雙軌”不可持久。一者因為公有經(jīng)濟(jì)部門長期處于命令價格的保護(hù)之內(nèi),既缺乏自我改革的動力,又使非公經(jīng)濟(jì)部門在競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二者因為兩套價格長期并行,以命令價格取得資源者可以利用價差牟取暴利,致使尋租、腐敗盛行,極大地擾亂經(jīng)濟(jì)秩序。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產(chǎn)物,“雙軌制”曾經(jīng)作出過重要的貢獻(xiàn),然而隨著時代的進(jìn)步,已經(jīng)越來越不適應(yī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要求,甚至妨礙改革的進(jìn)一步深化。
實行增量改革戰(zhàn)略,在大體維持國有經(jīng)濟(jì)現(xiàn)有體制的條件下,容許私有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引入部分市場機(jī)制,使中國經(jīng)濟(jì)出現(xiàn)了命令經(jīng)濟(jì)和市場經(jīng)濟(jì)雙軌并存的狀態(tài)。這種經(jīng)濟(jì)體制“雙軌制”最集中的表現(xiàn),是生產(chǎn)資料分配和價格的“雙軌制”。
在計劃經(jīng)濟(jì)條件下,生產(chǎn)資料由國家在國有經(jīng)濟(jì)單位之間統(tǒng)一調(diào)撥,價格只是這些單位之間進(jìn)行核算的工具;消費品由國營商業(yè)系統(tǒng)統(tǒng)一經(jīng)營,各級物價管理部門統(tǒng)一定價。
在改革開放之初,國有企業(yè)獲得了銷售產(chǎn)品的自主權(quán)。1979年國務(wù)院轉(zhuǎn)發(fā)的《關(guān)于擴(kuò)大國營工業(yè)企業(yè)經(jīng)營自主權(quán)的若干規(guī)定》允許企業(yè)自銷超計劃產(chǎn)品,在計劃軌之外開辟了物資流通的“第二軌道”——市場軌。
與此同時,沒有物資調(diào)撥指標(biāo)的非國有企業(yè)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也提出了從市場獲得原料等物資的必要性。到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非國有企業(yè)工業(yè)總產(chǎn)值已經(jīng)占到全國工業(yè)總產(chǎn)值的31%,通過市場流轉(zhuǎn)的生產(chǎn)資料份額也不斷擴(kuò)大。在這種情況下,1985年1月國家物價局和國家物資局下發(fā)《關(guān)于放開工業(yè)生產(chǎn)資料超產(chǎn)自銷產(chǎn)品價格的通知》,允許企業(yè)按市場價出售和購買“計劃外”產(chǎn)品,從此開始正式實行生產(chǎn)資料供應(yīng)和定價的“雙軌制”。具體的辦法是,對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權(quán)取得計劃內(nèi)調(diào)撥物資的國有企業(yè),仍然根據(jù)1983年調(diào)撥數(shù)(即“83年基數(shù)”),按調(diào)撥價供應(yīng)所需生產(chǎn)資料;超過“83年基數(shù)”的部分,則按照市場價格從市場上購買。
在實行增量改革戰(zhàn)略情況下,由于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雙軌并存,除生產(chǎn)資料分配和價格形成的“雙軌制”外,還在其他領(lǐng)域形成了多種“雙軌制”,例如國家銀行貸款利率和市場利率的“雙軌制”、外匯牌價和調(diào)劑市場價格的匯率“雙軌制”,等等。
對于“雙軌制”的利弊得失,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看法也非常不同。
劉遵義、錢穎一、G.羅蘭(GérardRoland)和張軍對價格“雙軌制”在穩(wěn)定國有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和實現(xiàn)帕累托改進(jìn)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作出了肯定評價。他們根據(jù)一般均衡分析,論證了雙軌價格自由化的帕累托改進(jìn)的特性。
國家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委員會體制改革研究所1986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從經(jīng)濟(jì)和政治兩方面論證了價格“雙軌制”的積極作用。報告認(rèn)為,從經(jīng)濟(jì)上看,在“雙軌制”條件下,“企業(yè)無論是增加或減少生產(chǎn)品或投入品,其增減變化部分的價格實際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市場價事實上已對企業(yè)的邊際產(chǎn)出和投入產(chǎn)生了決定性作用,通過這種邊際作用,形成了調(diào)整短期供求的信號和影響力量。”從政治上看,“在雙軌經(jīng)濟(jì)中有一種能夠用行政權(quán)力分配資源的機(jī)制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這種憑證的貨幣化會向權(quán)力的貨幣化轉(zhuǎn)化,即分配憑證的權(quán)力,實際上是分配貨幣的權(quán)力,也就是說權(quán)力本身能夠用貨幣度量了。它完全可以把權(quán)力變成一種貨幣。這種腐化行為在經(jīng)濟(jì)上是非常合理的。只要憑證貨幣化的機(jī)制發(fā)揮作用,在計劃所派生的行政權(quán)力又有所保留時,把對各種資源的分配權(quán)力當(dāng)做一種資本來運(yùn)用,就完全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情況。”
美國經(jīng)濟(jì)學(xué)家K.墨菲(KevinMorphy)、A.施萊弗(AndreiShleifer)和R.維什尼(RobertVishny)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rèn)為,如果所有的價格不是一齊放開,就會產(chǎn)生資源配置的扭曲。而且,它會在能夠獲得變相補(bǔ)貼的國有企業(yè)與只能以市場價格獲得原料、設(shè)備和貸款的民營企業(yè)之間造成不平等的經(jīng)營條件,因此愈到后來就愈益成為阻礙民營經(jīng)濟(jì)進(jìn)一步壯大的因素。
另外一些中國學(xué)者例如本文作者對“雙軌制”持續(xù)帶來的社會政治后果給予高度關(guān)注。
他們認(rèn)為,“雙軌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經(jīng)濟(jì)和社會后果是雙重的。一方面,正像前面一些學(xué)者所說,它給民間創(chuàng)業(yè)活動一定的空間,使各種類型的民營企業(yè)得以成長;另一方面,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這種“權(quán)力貨幣化”或“權(quán)力資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續(xù)下去甚至得到加強(qiáng),就會造成廣泛的尋租(rent-seeking)環(huán)境,埋下腐敗蔓延的禍根。而如果不能及時通過進(jìn)一步的市場化改革鏟除這一禍根,就有可能助長權(quán)貴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釀成嚴(yán)重的經(jīng)濟(jì)、社會及政治后果。
下篇:“整體推進(jìn)”全面改革(1994年至今)
“雙軌”的存在,意味著國民經(jīng)濟(jì)中仍然存在著大量低效的公有經(jīng)濟(jì)成分以及非市場化價格體系。公有經(jīng)濟(jì)和計劃體制痼疾未除,與新生的非公經(jīng)濟(jì)和市場體制之間的矛盾卻在日益尖銳。中國經(jīng)濟(jì)的改革戰(zhàn)略從“增量改革”向“全面改革”進(jìn)行轉(zhuǎn)變,遂成這個時期的必由之路。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價格“雙軌制”的“并軌”,以及國有企業(yè)大刀闊斧的改革。許多改革措施卓有成效,為中國經(jīng)濟(jì)持續(xù)高速發(fā)展作出關(guān)鍵性貢獻(xiàn),但由于種種原因,許多重要的改革未能適時推進(jìn),導(dǎo)致進(jìn)一步的改革更為艱難。
在國民經(jīng)濟(jì)許多重要領(lǐng)域,如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國有壟斷行業(yè),改革難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價格,如能源、利率、匯率,也尚未放開,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更為嚴(yán)重的問題在于,政府和國有經(jīng)濟(jì)部門依然掌控著國民經(jīng)濟(jì)的大部分資源,與市場經(jīng)濟(jì)的生產(chǎn)方式不相適應(yīng),而且“國進(jìn)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時有發(fā)生。
多年來的經(jīng)驗證明,改革如果不徹底,則其在推進(jìn)至某個特定的階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時,往往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tuán),成為妨礙改革進(jìn)一步推進(jìn)的重要阻力。而由于改革不徹底而產(chǎn)生的種種弊端,包括腐敗、尋租、社會不公等,又必須通過繼續(xù)進(jìn)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經(jīng)進(jìn)入深水區(qū),其進(jìn)程更加不容耽誤,中國經(jīng)濟(j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
采取增量改革戰(zhàn)略,目的是為了減少改革阻力,積蓄改革力量,縮短改革進(jìn)程,最終目的還是建立統(tǒng)一的市場經(jīng)濟(jì)體系。因此,改革終歸要推進(jìn)到國有部門。在“體制外”改革已經(jīng)為全面建立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準(zhǔn)備了必要條件的基礎(chǔ)上,就應(yīng)當(dāng)抓住時機(jī),在占用了國民經(jīng)濟(jì)中大部分重要資源的國有部門進(jìn)行整體配套改革,實現(xiàn)由計劃經(jīng)濟(jì)到市場經(jīng)濟(jì)的全面轉(zhuǎn)軌。
由于沒有能夠及時實現(xiàn)改革戰(zhàn)略的轉(zhuǎn)變,國民經(jīng)濟(jì)中已經(jīng)搞活的“體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體制束縛的“體制內(nèi)”部分之間出現(xiàn)了劇烈的摩擦,經(jīng)濟(jì)體系中存在著許多漏洞,國民經(jīng)濟(jì)的穩(wěn)定發(fā)展就經(jīng)常受到威脅。正如青木昌彥(MasahikoAoki)在《比較制度分析》一書中所指出的,一個體系中的各種制度具有戰(zhàn)略互補(bǔ)性,某一項或幾項制度發(fā)生變革,其他的制度要么進(jìn)行相應(yīng)的變化,要么就會與新制度不相配合,對新制度的實施產(chǎn)生阻礙。因此,制度變革本質(zhì)上就應(yīng)該是整體推進(jìn)的,雖然在實施上可以分步進(jìn)行,否則,就會存在巨大的制度運(yùn)行成本。所以,“雙軌制”拖得愈久,其消極后果也體現(xiàn)得愈嚴(yán)重。
隨著社會經(jīng)濟(jì)矛盾的加劇,由局部市場化轉(zhuǎn)向全面改革的呼聲也在上世紀(jì)80年代中期變得愈來愈強(qiáng)烈。1986年,在改革領(lǐng)導(dǎo)人的推動下,終于開始轉(zhuǎn)向進(jìn)行全面改革的嘗試。
試水全面改革
這是中國改革以來又一個全新的階段,改革開始從非公部門推向公有部門,從農(nóng)村推向城市,從價格體制推向以價格體制、稅收體制和財政體制為重點的配套改革,從經(jīng)濟(jì)改革推向政治改革,進(jìn)行了全面的嘗試。這些改革措施在許多領(lǐng)域,尤其是宏觀經(jīng)濟(jì)體系建立和所有制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兩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jìn)展,但由于突發(fā)性事件以及既得利益集團(tuán)的阻撓,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出現(xiàn)重大反復(fù),并未能取得預(yù)期的成就,這也使得后來的改革難度進(jìn)一步加大。
鄧小平是“增量改革”的倡導(dǎo)者,但他并不滿足于改革前期在非國有部門取得的成就。當(dāng)非國有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能夠為整個改革提供支撐點的時候,他提出了轉(zhuǎn)移改革戰(zhàn)略重點、把改革推向國有部門的要求。他在1984年6月指出,在農(nóng)村改革見效以后,“改革要從農(nóng)村轉(zhuǎn)到城市。城市改革不僅包括工業(yè)、商業(yè),還有科技、教育等,各行業(yè)”。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實施這一戰(zhàn)略轉(zhuǎn)變。
為了落實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和1985年《中共中央關(guān)于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1986年-1990年)的建議》提出的通過企業(yè)、市場體系和宏觀調(diào)控體系等三方面互相聯(lián)系的改革,“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內(nèi),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jī)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體制的基礎(chǔ)”的要求,中國政府從1986年起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1986年初,時任國務(wù)院總理趙紫陽提出了以價格體制、稅收體制和財政體制為重點進(jìn)行配套改革的設(shè)想。他宣布1986年國務(wù)院的工作方針是:在繼續(xù)加強(qiáng)和改善宏觀控制的條件下改善宏觀管理,在抑制需求的條件下改善供應(yīng),同時做好準(zhǔn)備,使改革能在1987年邁出決定性的步伐。接著,趙紫陽就改革形勢和“七五”(1986年-1990年)前期改革的要求多次發(fā)表講話。他在這些講話中指出,這種新舊體制膠著對峙,相互摩擦,沖突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長。因此1987年和1988年需要采取比較重大的步驟,促使新的經(jīng)濟(jì)體制能夠起主導(dǎo)作用。這就需要在市場體系和實現(xiàn)間接調(diào)控這兩個問題上步子邁大一點,為企業(yè)能夠真正自負(fù)盈虧,并在大體平等的條件下展開競爭創(chuàng)造外部條件。“具體說來,明年的改革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設(shè)計、去研究:第一是價格,第二是稅收,第三是財政。這三個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聯(lián)系的。”“關(guān)鍵是價格體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圍繞價格改革來進(jìn)行。”
為了進(jìn)行擬議中的配套改革,國務(wù)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經(jīng)濟(jì)改革方案設(shè)計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在國務(wù)院和中共中央財經(jīng)領(lǐng)導(dǎo)小組的直接領(lǐng)導(dǎo)下,擬定了“七五”前期以價格、稅收、財政、金融和貿(mào)易為重點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的價格改革,準(zhǔn)備采取類似于捷克斯洛伐克在1967年-1968年改革的做法,用“先調(diào)后放”的辦法實施價格市場化:先根據(jù)計算全面調(diào)整價格,然后用一到兩年時間將價格全面放開,實現(xiàn)并軌。在財稅體制方面的主要舉措,則是將當(dāng)時實行的“分灶吃飯”體制(Revenue-SharingSystem),改革為“分稅制”(Tax-SharingSystem)以及引進(jìn)增值稅(VAT)等,上述配套改革方案在1986年8月獲得國務(wù)院常務(wù)會議通過,決定從1987年1月1日起施行。鄧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聽取中央財經(jīng)領(lǐng)導(dǎo)小組關(guān)于改革方案的匯報時,對這個配套改革方案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要求照此執(zhí)行。[$Page_Split$]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1986年再次要求啟動以“黨政分開”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使中國的政治體制適應(yīng)于市場經(jīng)濟(jì)的需要。20世紀(jì)80年代雙軌并存引致的諸多矛盾表明,問題的癥結(jié)在于:在雙軌體制下,“國家辛迪加”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經(jīng)濟(jì)資源的遺產(chǎn)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要消除這些遺產(chǎn),就不能不徹底進(jìn)行國家體制的改革。正是由于認(rèn)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鄧小平在1986年重提進(jìn)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繼續(xù)前進(jìn),就會阻礙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阻礙四個現(xiàn)代化的實現(xiàn)。”遺憾的是,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沒能進(jìn)行下去。
在經(jīng)濟(jì)改革方面,在政府內(nèi)部和學(xué)術(shù)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國務(wù)院領(lǐng)導(dǎo)原來是堅持“價、稅、財配套”改革的,但是到1986年10月,國務(wù)院領(lǐng)導(dǎo)改變了原來的想法,轉(zhuǎn)向以國有企業(yè)改革為改革主線,并在1987年和1988年實行了“企業(yè)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干”“外貿(mào)大包干”和“信貸切塊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回到了維持市場經(jīng)濟(jì)與命令經(jīng)濟(jì)雙軌并存體制的老做法。由于喪失大步推進(jìn)改革的時機(jī),行政腐敗、通貨膨脹等問題愈演愈烈,最后以1988年的搶購風(fēng)波和1989年的政治風(fēng)波告終。
1988年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和1989年的政治風(fēng)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把這次經(jīng)濟(jì)和政治動蕩歸罪于市場取向的改革,指責(zé)“取消計劃經(jīng)濟(jì),實現(xiàn)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于是,發(fā)生了改革開放以后的又一次回潮。直到1992年初鄧小平作了推動進(jìn)一步改革開放的南巡講話以后,才迎來新的改革開放熱潮。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改革目標(biāo)。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作出了《關(guān)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以下的問題上獲得重要突破:
第一,明確提出“整體推進(jìn)、重點突破”的新的改革戰(zhàn)略。也就是說,不只在邊緣地帶進(jìn)攻,而且要在國有部門打攻堅戰(zhàn),要求在20世紀(jì)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
第二,為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外匯管理體制、企業(yè)體制和社會保障體系等重點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目標(biāo),擬定了方案。
根據(jù)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從1994年初開始,中國政府在財稅、金融、外匯管理、企業(yè)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和國有企業(yè)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來推進(jìn)改革。同時,國務(wù)院要求按照《公司法》進(jìn)行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試點,以便在取得經(jīng)驗后全面推廣。在以上諸方面的改革中,外匯改革進(jìn)展最為順利,提前實現(xiàn)了全會《決定》所規(guī)定的在經(jīng)常賬戶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目標(biāo),財稅體制也進(jìn)入了預(yù)定的軌道。其他方面,特別是國有經(jīng)濟(jì)改革雖有一定進(jìn)展,但仍未達(dá)到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jì)的要求。
到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在宏觀經(jīng)濟(jì)體系建立和所有制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兩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jìn)展。基本標(biāo)志是原來國有經(jīng)濟(jì)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發(fā)生了改變,國有經(jīng)濟(jì)在國民經(jīng)濟(jì)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較大下降。不過從全面建立市場經(jīng)濟(jì)所有制基礎(chǔ)的角度看,改革的大關(guān)并沒有過。直到1993年,雖然國有經(jīng)濟(jì)在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國有企業(yè)仍然是稀缺經(jīng)濟(jì)資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資金為例,國有部門占用了70%以上的信貸資源。此外,由于政府和國有企業(yè)在國民經(jīng)濟(jì)中的領(lǐng)導(dǎo)地位,使適合市場經(jīng)濟(jì)的金融、財稅等體系難以健全。發(fā)生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舊有的國有經(jīng)濟(jì)體制,亦即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的“國家辛迪加”(TheStateSyndicate),或者用現(xiàn)代語言說,黨政經(jīng)一體化的大公司(TheParty-StateInc.),乃是整個舊體制的核心或基礎(chǔ)。以此為依據(jù)的利益關(guān)系盤根錯節(jié)。如果在舊體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個社會的利益為重,就會以種種口實(包括政治借口)阻礙國有部門改革和改組的進(jìn)行。于是,改革和改組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世紀(jì)之交的改革與矛盾
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與反改革的力量交鋒日益激烈。從某種意義上講,此后的改革比改革初期更為艱難。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來自意識形態(tài),而此時則主要來自既得利益;改革初期的措施有帕累托改進(jìn)的特性,而此時國有壟斷企業(yè)和政府部門已經(jīng)享受改革的成果,但進(jìn)一步改革會損害它們的利益。推動國有壟斷企業(yè)和政治體制改革,意味著政府要對自身進(jìn)行改革,改革由此進(jìn)入更為艱難的攻堅戰(zhàn),進(jìn)度明顯放慢。
中國經(jīng)濟(jì)改革面臨的舊所有制結(jié)構(gòu)的障礙,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取得了某些重要的突破。
從經(jīng)濟(jì)方面說,中共十五大否定把國有經(jīng)濟(jì)比重大小同社會主義性質(zhì)的強(qiáng)弱直接聯(lián)系起來,明確肯定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在世紀(jì)之交,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chǔ)的市場經(jīng)濟(jì)的輪廓開始顯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據(jù)此,代表大會要求根據(jù)“三個有利于”的原則,調(diào)整和完善國民經(jīng)濟(jì)的所有制結(jié)構(gòu),建立今后長時期的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調(diào)整包括三項主要內(nèi)容:(1)縮小國有經(jīng)濟(jì)的范圍,國有資本要從不關(guān)系國民經(jīng)濟(jì)命脈的領(lǐng)域退出;(2)尋找能夠促進(jìn)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多種公有制實現(xiàn)形式,發(fā)展多種形式的公有制;(3)明確宣布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個體私營等非公有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
1998年,中共十五大的上述決定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jīng)濟(jì)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在法律規(guī)定范圍內(nèi)的個體經(jīng)濟(jì)、私營經(jīng)濟(jì)等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hù)個體經(jīng)濟(jì)、私營經(jīng)濟(jì)的合法的權(quán)利和利益。”
在此后幾年中,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改革取得了不小進(jìn)展。
第一,國民經(jīng)濟(jì)的所有制結(jié)構(gòu)明顯優(yōu)化,從國有經(jīng)濟(jì)一家獨大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yōu)槎喾N所有制企業(yè)共同發(fā)展。除少數(shù)壟斷行業(yè)外,民營經(jīng)濟(jì)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業(yè)方面,民營企業(yè)成為吸納就業(yè)的主體,2006年民營企業(yè)就業(yè)人數(shù)達(dá)到全國城鎮(zhèn)就業(yè)人數(shù)的72%。
第二,國有企業(yè)改革取得重大進(jìn)展。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國有企業(yè)已從國有獨資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yōu)橐怨煞荻嘣墓局破髽I(yè)為主。目前在非金融類企業(yè)方面,絕大多數(shù)國有二級企業(yè)已經(jīng)改組為國家相對或絕對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金融類企業(yè)中,21世紀(jì)初實現(xiàn)四家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海外整體上市,為中國金融市場提供了必要的微觀基礎(chǔ)。二是這些公司在股權(quán)多元化的基礎(chǔ)上搭起了公司治理結(jié)構(gòu)的基本框架。
中國雖然在20世紀(jì)末建立起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場經(jīng)濟(jì)的若干重要架構(gòu),例如規(guī)范的金融市場,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jì)所必需的法治體制,并沒有建立起來。所以說,距離原來確定的經(jīng)濟(jì)改革目標(biāo)還有不小的差距。有鑒于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guān)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若干問題的決定》。不過,這一決定的執(zhí)行不是沒有阻力和障礙的。由于改革有所放緩,社會矛盾的態(tài)勢也發(fā)生了新的變化。
首先,按照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國有經(jīng)濟(jì)的布局調(diào)整和國有企業(yè)的股份化改制都有了重要的進(jìn)展。到了21世紀(jì)初期,全國中小型國有企業(yè),包括基層政府所屬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已經(jīng)全面改制,其中絕大部分成為個人獨資或公司制企業(yè),但是,當(dāng)國有經(jīng)濟(jì)改革改到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yè)的國有壟斷企業(yè)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慢了下來。
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yè)中國有企業(yè)究竟應(yīng)當(dāng)“進(jìn)”,還是應(yīng)當(dāng)“退”的爭論又起。有些論者提出,在這些行業(yè)中,國有經(jīng)濟(jì)的比重不但不應(yīng)當(dāng)降低,還應(yīng)當(dāng)提高。2003年,國資委有的官員宣傳一種“國有經(jīng)濟(jì)是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觀點,引起相當(dāng)程度的思想混亂。直到2004年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議上黨政領(lǐng)導(dǎo)對此做出了澄清,但類似的論調(diào)在一部分人中間仍然很有市場。2004年爆發(fā)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確的爭論以后,社會上又出現(xiàn)了被媒體稱為“再國有化”或“新國有化”現(xiàn)象。這種“回潮”的趨勢主要有兩種表現(xiàn)形式:一是有些領(lǐng)域在已對民營企業(yè)進(jìn)入發(fā)放“許可證”的情況下,又往后退縮,不讓民營企業(yè)繼續(xù)經(jīng)營;二是一些國有獨資和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對民營中小企業(yè)展開了收購兼并,使這類企業(yè)的壟斷地位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
第二,政府對企業(yè)微觀經(jīng)濟(jì)活動的行政干預(yù),在“宏觀調(diào)控”的名義下有所加強(qiáng)。
從2003年四季度開始,中國經(jīng)濟(jì)出現(xiàn)了“過熱”的現(xiàn)象。為了保持經(jīng)濟(jì)的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中國政府決定采取措施促使經(jīng)濟(jì)降溫。宏觀經(jīng)濟(jì)是一個總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發(fā)生了宏觀經(jīng)濟(jì)過熱,即總量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的情況下,就理應(yīng)按照市場經(jīng)濟(jì)的常規(guī),以匯率、存款、準(zhǔn)備金率等間接手段為主,進(jìn)行總量調(diào)控。當(dāng)然,在中國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還有必要運(yùn)用某些行政手段,例如對銀行信貸的“窗口指導(dǎo)”作為補(bǔ)充。但是,必須明確,它們只能是輔助性的手段,而且應(yīng)當(dāng)在運(yùn)用這種手段時,對它們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充分的估計。但是,當(dāng)時,在對宏觀經(jīng)濟(jì)形勢進(jìn)行判斷時,主流意見卻把問題的性質(zhì)確定為“局部過熱”,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聯(lián)合發(fā)文,采用審批等行政手段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過熱行業(yè)”的投資、生產(chǎn)活動進(jìn)行嚴(yán)格控制。從那時起,“宏觀調(diào)控要以行政調(diào)控為主”就成為正式的指導(dǎo)方針。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dǎo)下,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diào)控”的名義加強(qiáng)了對微觀經(jīng)濟(jì)的干預(yù)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大為強(qiáng)化,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chǔ)性作用則遭到削弱。英國的阿克頓勛爵(LordActon)說:“權(quán)力易于導(dǎo)致腐敗,絕對的權(quán)力會絕對地腐敗”。行政權(quán)力的擴(kuò)張,導(dǎo)致尋租活動制度基礎(chǔ)擴(kuò)大,使腐敗日益盛行。
第三,政治改革滯后。鄧小平在1980年發(fā)動全國農(nóng)村承包制改革同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講話,啟動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jīng)濟(jì)改革也難于貫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過,這兩次改革都沒有能夠進(jìn)行下去。鄧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領(lǐng)導(dǎo)人在追悼會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問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一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shè)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十年來進(jìn)展十分緩慢。例如《物權(quán)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jīng)濟(jì)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出臺。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jì)來說,沒有合乎公認(rèn)基本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zhí)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jīng)濟(jì)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chǎn)的安全,就只有去“結(jié)交官府”。于是,就出現(xiàn)了尋租的“新動力”。
由于尋租規(guī)模的擴(kuò)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根據(jù)1988年以來若干學(xué)者的獨立研究,中國租金總數(shù)占GDP的比率高達(dá)20%-30%,年絕對額高達(dá)4萬億至5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量,自然會對中國社會中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系數(shù)的居高不下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
第三次改革大辯論
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jìn)一步改革。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jīng)濟(jì)問題相關(guān)的不公事實,根源在于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這一點在中央決策層已經(jīng)明確,并指出“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但要將改革深化推進(jìn),還需要有更切實、有力的措施。
由于實行“雙軌制”的社會存在法治的市場經(jīng)濟(jì)和權(quán)貴資本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發(fā)展前途,于是,近年來就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當(dāng)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jìn),例如,當(dāng)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放開,商品市場尋租的可能性大幅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當(dāng)世紀(jì)之交包括大量“蘇南模式”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內(nèi)的中小企業(yè)實現(xiàn)“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區(qū)經(jīng)濟(jì)的大發(fā)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時,雖然出現(xiàn)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為,滿意的聲音仍然占有優(yōu)勢。反之,當(dāng)進(jìn)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礙,比如說國有壟斷企業(yè)的改革停頓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說推行了所謂“斯托雷平式”的權(quán)貴私有化時,就會造成腐敗活動猖獗,貧富差別進(jìn)一步擴(kuò)大的態(tài)勢。
面對這種形勢,提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
支持市場化的經(jīng)濟(jì)改革和與之相適應(yīng)的政治改革的人們認(rèn)為,既然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是由市場化經(jīng)濟(jì)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嚴(yán)重滯后,權(quán)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qiáng)化對市場自由交換活動干預(yù)壓制等尋租活動基礎(chǔ)所造成的,根本解決之道就只能是堅持經(jīng)濟(jì)改革和政治改革,鏟除權(quán)貴資本主義存在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并使公共權(quán)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jiān)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決方法,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極“左”路線支配下的舊體制去。一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諉過于市場化改革,將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極現(xiàn)象的正當(dāng)不滿,南轅北轍地引向反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輪改革大辨論。
改革開放30年來,類似的爭論已經(jīng)有過多次。例如,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進(jìn)行過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又進(jìn)行過一次,2004年-2006年已經(jīng)是第三次。這次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究竟是一條應(yīng)當(dāng)堅持的正確路線,還是一條應(yīng)當(dāng)否定的錯誤路線?
在這場爭論中,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發(fā)表講演,印發(fā)書刊,組織“學(xué)習(xí)”,重彈他們在1989年-1991年大爭論中唱過的“取消計劃經(jīng)濟(jì),實現(xiàn)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舊調(diào),指責(zé)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他們把中國改革說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dǎo)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責(zé)改革的領(lǐng)導(dǎo)人是“背叛了列寧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走資派”和“資改派”:“一是經(jīng)濟(jì)上繼續(xù)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繼續(xù)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沒有階級性和革命性的口號和主張,例如什么‘以人為本’‘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等”;“三是在外交上繼續(xù)實行投降妥協(xié)的路線”,“根本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了”,“反而跟著帝國主義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運(yùn)動是什么‘恐怖主義組織’‘破壞穩(wěn)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開放在制度上肯定下來,培養(yǎng)了一些親美的新資產(chǎn)階級分子。”他們還攻擊說,當(dāng)前醫(yī)療、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國有資產(chǎn)流失、貧富兩極分化乃至礦難頻發(fā)等問題,都是由這種市場化的“資改路線”造成的。
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wèi)者極力鼓吹,目前我們遇到的種種社會經(jīng)濟(jì)問題,從腐敗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貴、上學(xué)難,甚至國有資產(chǎn)流失、礦難頻發(fā)等都是由市場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動扭轉(zhuǎn)改革開放的大方向,重舉“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旗幟,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來一次,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jìn)行到底”,實現(xiàn)“對黨內(nèi)外資產(chǎn)階級的全面專政”。
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對中國現(xiàn)狀所作的這些主張,不論就他們的“診斷”,還是就他們的“處方”來說,都是不正確的。
以貧富分化為例。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wèi)者宣傳說,贊成市場取向改革的人們主張擴(kuò)大貧富差距,而市場化改革也正是中國貧富差距擴(kuò)大的罪魁禍?zhǔn)住_@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中國收入差距過大,正是一批主張改革的社會學(xué)家和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在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漸引起社會注意的。
問題的焦點在于,中國社會中的貧富分化加劇的原因何在,解決這一問題的著力點又應(yīng)當(dāng)在哪里。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wèi)者斷言,這是由市場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們主張把矛頭對準(zhǔn)在市場經(jīng)濟(jì)中由于勤于勞動、善于經(jīng)營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們,以便拉平他們和低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主張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的人們則認(rèn)為,目前中國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機(jī)會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級黨政機(jī)關(guān)有過大的支配資源的權(quán)力,能夠接近這種權(quán)力的人就可以憑借這種權(quán)力靠尋租活動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業(yè)的行業(yè)壟斷所造成。根據(jù)這種分析,縮小貧富差距的著力點應(yīng)當(dāng)是通過推進(jìn)市場化改革,挖掉尋租活動的基礎(chǔ),打破對競爭性領(lǐng)域的行業(yè)壟斷,堅決打擊“權(quán)力攪買賣”的腐敗行為。
當(dāng)然,在市場經(jīng)濟(jì)機(jī)會平等的情況下,由于人們的能力有大小,也會產(chǎn)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別是中國目前傳統(tǒng)低效農(nóng)業(yè)和現(xiàn)代先進(jìn)工商業(yè)二元經(jīng)濟(jì)并存,這種差距就會比一元經(jīng)濟(jì)中更大。對于這種結(jié)果不平等,也應(yīng)當(dāng)采取切實措施加以補(bǔ)救。但最重要的補(bǔ)救辦法,應(yīng)當(dāng)是由政府負(fù)起責(zé)任來,建立起能夠保證低收入階層基本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
中國原來實行的只覆蓋國有部門的社會保障體系本來就很不完善。像公費醫(yī)療費體系,只覆蓋國營企業(yè)和黨政機(jī)關(guān),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別是黨政領(lǐng)導(dǎo)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別是農(nóng)民卻缺醫(yī)少藥。改革開放以后,這一套體系完全無法運(yùn)轉(zhuǎn)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對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設(shè)計。從現(xiàn)在的情況來看,這一設(shè)計也是基本正確和大體可行的。如果能在實施過程中進(jìn)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為中國居民編織一個能夠有效運(yùn)轉(zhuǎn)的安全網(wǎng)。
可是14年過去了,由于某些部門出于部門利益的考慮,采取消極甚至抵制的態(tài)度,使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方案由于國有企業(yè)老職工“空賬戶”補(bǔ)償問題未獲解決而不能實現(xiàn)。
如果說他們對中國社會問題所作的“診斷”屬于“誤診”,他們開出的“處方”,即回到“全面專政”時代,就更是有害無益了。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quán)貴資本主義現(xiàn)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約束的權(quán)力對于經(jīng)濟(jì)活動的干預(yù)和對于經(jīng)濟(jì)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強(qiáng)國有企業(yè)的壟斷地位,加強(qiáng)政府及其官員不受約束的“專政”權(quán)力,不正是強(qiáng)化腐敗的制度基礎(chǔ),和他們所宣稱的目標(biāo)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這樣,雖然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和他們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某種優(yōu)勢,在對醫(yī)療、教育、住房以及國企改革等具體問題的討論中,通過蒙蔽蠱惑大眾,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一當(dāng)他們亮明底牌,即扭轉(zhuǎn)歷史車輪,回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災(zāi)難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的時候,那些雖然對于改革開放的某些具體做法和中國社會的現(xiàn)狀懷有意見,但能夠理性思考問題、并不反對經(jīng)濟(jì)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們,也就離他們而去了。
對于這種開倒車的主張,中國的黨政領(lǐng)導(dǎo)也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3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海代表團(tuán)的講話中指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chǔ)性作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尖銳地提出“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對那種走回頭路的主張進(jìn)行了正面的批判。這份報告指出:“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yīng)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中國是否能夠在未來的30年續(xù)寫輝煌,將取決于我們能否正確應(yīng)對新一輪的挑戰(zhàn)。(作者為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新中國60年經(jīng)濟(jì)體改大事記
1952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guān)于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及干部配備方案的決定》。各級人民政府相繼成立地方計委,全國性計劃管理機(jī)構(gòu)初步建立。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cè)蝿?wù),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些時間內(nèi),基本完成國家工業(yè)化以及對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合作社問題》的報告,由此掀起全國農(nóng)業(yè)合作化高潮。
195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轉(zhuǎn)發(fā)毛澤東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重申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nèi)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
1958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在農(nóng)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全國范圍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yùn)動的高潮。
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關(guān)于調(diào)整管理體制的若干暫行規(guī)定》,強(qiáng)調(diào)集中統(tǒng)一,經(jīng)濟(jì)管理大權(quán)應(yīng)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qū)),以克服經(jīng)濟(jì)困難。
1964年9月21日,全國計劃會議召開,決定根據(jù)“大權(quán)獨攬、小權(quán)分散”,“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分級管理”的原則改進(jìn)計劃管理體制。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反對經(jīng)濟(jì)主義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立即停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鬧經(jīng)濟(jì)主義的傾向。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進(jìn)一步打擊反革命經(jīng)濟(jì)主義和投機(jī)倒把活動的通知》,堅決取締無證商販、個體手工業(yè)戶等。
1976年3月3日,財政部決定從1976年起實行“定收定支,收支掛鉤,總額分成,一年一變”的財政管理體制。
1978年11月25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nóng)民在當(dāng)時的生產(chǎn)隊長的帶領(lǐng)下,商定“私下”實行大包干,并當(dāng)場立下字據(jù),按上手印。這標(biāo)志著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開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工作重點轉(zhuǎn)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標(biāo)志著中國進(jìn)入了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新時期。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針對國民經(jīng)濟(jì)比例嚴(yán)重失調(diào)的情況,決定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jīng)濟(jì)實行“調(diào)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要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確貫徹計劃經(jīng)濟(jì)為主、市場經(jīng)濟(jì)為輔的原則,是經(jīng)濟(jì)體改中一個根本性問題。
1983年6月6日,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全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要改革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發(fā)展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市場,改革財政體制、工資制度和勞動體制。
1983年7月8日,深圳寶安縣聯(lián)合投資公司成立,在深圳公開發(fā)行股份證,是全國第一家股份制集資企業(yè)。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1984年農(nóng)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長土地承包期,一般應(yīng)在15年以上。
1984年10月4日,國務(wù)院批轉(zhuǎn)國家計委《關(guān)于改進(jìn)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guī)定》,強(qiáng)調(diào)要根據(jù)“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的精神,適當(dāng)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是以公有制為基礎(chǔ)的有計劃的商品經(jīng)濟(jì)。
1984年11月8日,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成立,并向社會發(fā)行股票。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家比較規(guī)范的股份公司。
1986年3月3日,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廈門國際銀行正式成立。
1986年8月3日,沈陽市防爆器材廠宣告破產(chǎn)。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正式宣布破產(chǎn)的第一家國有企業(yè)。
1986年12月5日,國務(wù)院作出《關(guān)于深化企業(yè)改革增強(qiáng)企業(yè)活力的若干規(guī)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yè)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jīng)營;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yè)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jīng)營責(zé)任制;各地可以選擇少數(shù)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yè)進(jìn)行股份制試點。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jì)中葉分三步走、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戰(zhàn)略。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允許私營經(jīng)濟(jì)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nèi)存在和發(fā)展,私營經(jīng)濟(jì)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jīng)濟(jì)的補(bǔ)充。國家保護(hù)私營經(jīng)濟(jì)的合法的權(quán)利和利益,對私營經(jīng)濟(jì)實行引導(dǎo)、監(jiān)督和管理”等規(guī)定載入《憲法》。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進(jìn)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強(qiáng)調(diào)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當(dāng)前要著重落實企業(yè)承包經(jīng)營責(zé)任制、財政包干制、金融體制、外貿(mào)承包體制等方面的改革。
1991年9月23日至27日,中央工作會議強(qiáng)調(diào),把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yè)作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大事擺到突出位置。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工作的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為主的責(zé)任制、統(tǒng)分結(jié)合的雙層經(jīng)營體制,作為中國鄉(xiā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wěn)定下來。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fā)表重要談話,強(qiáng)調(diào)基本路線要堅持100年不動搖,指出計劃經(jīng)濟(jì)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jīng)濟(jì)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jīng)濟(jì)手段。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確定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目標(biāo)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憲法,肯定了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肯定了農(nóng)村中的以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為主的責(zé)任制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jīng)濟(jì);肯定了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diào)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chǔ)性作用。
1993年12月25日,國務(wù)院作出關(guān)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獨立執(zhí)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的宏觀調(diào)控體系。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制定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發(fā)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yuǎn)景目標(biāo)的建議》,提出經(jīng)濟(jì)體制從傳統(tǒng)的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轉(zhuǎn)變,經(jīng)濟(jì)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zhuǎn)變。
1996年1月12日,中國首家主要由民營企業(yè)投資的全國股份制商業(yè)銀行——中國民生銀行成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實現(xiàn)形式可以而且應(yīng)當(dāng)多樣化。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shù)等生產(chǎn)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1998年3月19日,時任國務(wù)院總理朱镕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三個到位”:一是確定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shù)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yè)擺脫困境,進(jìn)而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二是確定在三年內(nèi)徹底改革金融系統(tǒng),中央銀行強(qiáng)化監(jiān)管、商業(yè)銀行自主經(jīng)營的目標(biāo)要在本世紀(jì)末實現(xiàn);三是政府機(jī)構(gòu)改革的任務(wù)要在三年內(nèi)完成。
1999年9月19日至22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國有企業(yè)改革和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認(rèn)為推進(jìn)國有企業(yè)改革和發(fā)展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wù),首先要盡最大努力實現(xiàn)國有企業(yè)改革和脫困的三年目標(biāo)。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mào)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首都多哈以全體協(xié)商一致的方式,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mào)組織的決定。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guān)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2003年12月16日,中央?yún)R金公司成立,并于當(dāng)月30日向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shè)銀行注資共450億美元,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拉開帷幕。
2004年8月26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國有獨資商業(yè)銀行整體改制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yè)銀行。隨后三年,中國建設(shè)銀行、交通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相繼轉(zhuǎn)變?yōu)楣煞葜粕绦小?006年底,上述四家銀行全部完成股改上市。中國農(nóng)業(yè)銀行股份制改革正在進(jìn)行中。
2005年2月24日,國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鼓勵支持和引導(dǎo)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若干意見》。針對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突出問題,提出了放寬市場準(zhǔn)入、加大財稅支持七方面的政策措施。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fā)布公告稱,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chǔ)、參考一籃子貨幣進(jìn)行調(diào)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jī)制。
2006年11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發(fā)布。根據(jù)加入世貿(mào)組織承諾,中國將在2006年12月11日前向外資銀行開放對中國境內(nèi)公民的人民幣業(yè)務(wù),并取消開展業(yè)務(wù)的地域限制以及其他非審慎性限制,在承諾基礎(chǔ)上對外資銀行實行國民待遇。
2007年7月23日,國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開展城鎮(zhèn)居民基本醫(y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dǎo)意見》,決定這一年在79個城市試點,擴(kuò)大城鎮(zhèn)居民基本醫(yī)療保險的覆蓋面,爭取2010年覆蓋全國。
《財經(jīng)》雜志2009年第20期 2009-10-1
相關(guān)文章
- 王樹增《解放戰(zhàn)爭》節(jié)錄,用事實反駁《大江大海》的謠言
- 推薦北京人藝新排《龍須溝》和《窩頭會館》
- 科學(xué)解讀和評估兩個三十年的經(jīng)濟(jì)增長與發(fā)展(一)
- 獻(xiàn)給1973-1982年出生的超齡兒童們
- 淺說建國60年和我們的未來走向
- 孫學(xué)文:駁資改派建國頭29年“經(jīng)濟(jì)崩潰”論
- 新華網(wǎng):美國為何少祝福中國30年
- 國慶大閱兵,精英之家電視臺解說詞!
- 丑牛:又逢己丑--“我們決不做李自成!”
- 《刷盤子還是讀書》姊妹版:用一般科學(xué)原理認(rèn)識毛時代
- 梅新育:對建國初30年的重新估值
- 滄桑巨變:共和國60年的社會變遷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