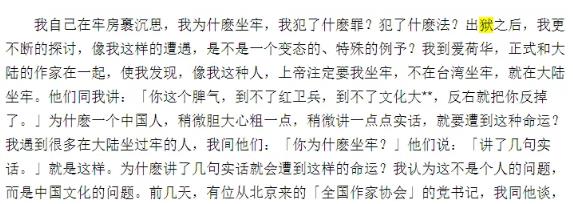昨晚看到一則消息:
張香華女士此舉還算深明大義,但這絲毫不能減少筆者對柏楊的鄙視與厭惡。
筆者對柏楊的評價(jià)如文題所言,他雖是被蔣氏父子關(guān)了近十年,但觀其終身的言行,也不過是蔣氏父子的忠實(shí)走狗而已。
拿方志敏與柏楊相提并論,當(dāng)然是侮辱了方志敏;而為了說清楚柏楊的問題究竟在哪里,筆者又不得不作這樣的對比。
方志敏同志不僅是一名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同時(shí)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知識分子,有著極高的文學(xué)造詣。
方志敏22歲就已經(jīng)是《新江西》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其后更是有豐富的辦報(bào)和宣傳工作經(jīng)歷;24歲創(chuàng)作的白話小說《謀事》與魯迅、郁達(dá)夫、葉圣陶等著名作家作品一起入選上海小說研究所編印的小說《年鑒》;1930年1月,他創(chuàng)作了革命新劇《年關(guān)斗爭》,并在貴溪親自登臺演出;1935年不幸被捕,他又在獄中創(chuàng)作了《清貧》、《可愛的中國》、《獄中紀(jì)實(shí)》等文學(xué)作品。
在《可愛的中國》里,方志敏同志飽含深情地寫道:
朋友!中國是生育我們的母親。你們覺得這位母親可愛嗎?我想你們是和我一樣的見解,都覺得這位母親是蠻可愛蠻可愛的。以言氣候,中國處于溫帶,不十分熱,也不十分冷,好像我們母親的體溫,不高不低,最適宜于孩兒們的偎依……咳!母親!美麗的母親,可愛的母親,只因你受著人家的壓榨和剝削,弄成貧窮已極;不但不能買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裝飾起來;甚至不能買塊香皂將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現(xiàn)出怪難看的一種憔悴襤褸和污穢不潔的形容來!
中國真是無力自救嗎?我絕不是那樣想的,我認(rèn)為中國是有自救的力量的。中國民族,不是表示過它的斗爭力量之不可侮嗎?彌漫全國的“五卅”運(yùn)動,是著實(shí)的教訓(xùn)了帝國主義,中國人也是人,不是豬和狗,不是可以隨便屠殺的。
朋友,雖然在我們之中,有漢奸,有傀儡,有賣國賊,他們認(rèn)仇作父,為虎作倀;但他們那班可恥的人,終竟是少數(shù),他們已經(jīng)受到國人的抨擊和唾棄,而漸趨于可鄙的結(jié)局。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有良心有民族熱情的中國人,仍然是熱心愛護(hù)自己的國家的。現(xiàn)在不是有成千成萬的人在那里決死戰(zhàn)斗嗎?他們決不讓中國被帝國主義所滅亡,決不讓自己和子孫們做亡國奴。
同樣是進(jìn)了國民黨的監(jiān)獄,方志敏同志最終犧牲在了獄中,并寫下了文辭優(yōu)美、對祖國和人民飽含深情的《可愛的中國》;柏楊在獄中完成了從囚犯到獄卒的身份轉(zhuǎn)換并最終被放了出來,出獄后卻以上帝和判官的視角寫出了言語猙獰、對全體中國人充滿鄙夷和貶低、對殖民者的文明頂禮膜拜的《丑陋的中國人》。
柏楊在80年代的爆紅,全是因?yàn)椤冻舐闹袊恕罚欢⌒〉暮u的千萬人,還不足以讓柏楊“爆紅”;《丑陋的中國人》80年代在大陸的走俏以及被知識精英的競相吹捧,才最終促成了柏楊的被“封神”。
這不僅僅是柏楊個(gè)人的問題,而是80年代非毛化和告別革命的大時(shí)代的悲哀。
柏楊1984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xué)的演講錄音后來被他整理成了《丑陋的中國人》一書,在演講中他說道:
由這樣的內(nèi)容,我們其實(shí)不難想象,寫出《丑陋的中國人》的柏楊,不僅為仇視社會主義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派所需要,也為80年代大陸那些仇恨毛主席的叛徒和知識精英所需要——這是他們要聯(lián)合起來給柏楊封神的真正原因。
筆者在中學(xué)時(shí)代也曾為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撫掌擊節(jié)、大為贊嘆;后來上了大學(xué)才有了初步的哲學(xué)思辨能力,又曾到工廠與農(nóng)村做些社會調(diào)查,進(jìn)而再整理從兒時(shí)起的社會記憶,就愈發(fā)覺得柏楊之片面與極端。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經(jīng)回顧過家鄉(xiāng)的農(nóng)民在80年代還殘存的協(xié)作與集體主義精神以及這樣的精神在90年代后的徹底消亡,回顧過社會風(fēng)氣從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后來的一步步變化,絕非全部時(shí)間以及全體中國人都如柏楊所謂的“窩里斗”狀態(tài)。
“窩里斗”固然已經(jīng)是普遍現(xiàn)象,但是看不到這樣的歷史變化過程,自然也就搞不清楚“窩里斗”產(chǎn)生的真正根源。正因如此,柏楊擺出了一副“世人皆濁我獨(dú)清,眾人皆醉我獨(dú)醒”的架勢,實(shí)際上卻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一位知乎網(wǎng)友對柏楊的“編排”還是很犀利的:
“自私”、“冷漠”并非有著幾千年歷史的中國“特產(chǎn)”,實(shí)在是一切私有制社會的共同特征。
然而,柏楊卻說:
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diǎn):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也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
在這里,柏楊扯了一個(gè)彌天大謊,將近代帝國主義列強(qiáng)侵略、壓迫、欺凌、侮辱中國人的滔天罪惡一筆勾銷;用三個(gè)“凡是”,把中國人深重的災(zāi)難的原因一歸結(jié)為中國人自己欺負(fù)自己。不許“說西方的財(cái)富是搶來的”,還說這樣講是“嫉妒”。
而李敖對《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的批判更是指出了關(guān)鍵,“所謂丑陋的中國人只是一種刻板印象而已,柏楊將一部分中國人的丑陋加諸于所有中國人之上,是懦夫的行為”。
柏楊講過一個(gè)浙江的青年,因?yàn)榭谷栈顒訝奚耍耐l(xiāng)中的一個(gè)“正人君子”(柏楊賜予的封號)說這個(gè)青年“這個(gè)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場。”,然后柏楊就開始嘲諷:
這正是一種冷漠,一種殘忍。在醬缸文化中,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獵取富貴功名的行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間靈性,消失罄盡,是非標(biāo)準(zhǔn),顛之倒之,人與獸的區(qū)別,微乎其微。惟一只貫天日的,只剩下勢利眼。
在柏楊的口中,“正人君子”搖身一變成了全體“中國人”了,可是這個(gè)抗日青年難道不是中國人嗎?柏楊自己呢?
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看起來是“振聾發(fā)聵、正義凜然”,實(shí)則是“傲慢與諂媚”并存,對比自己地位低的廣大中國人民高高在上地指手畫腳、當(dāng)教父;對欺負(fù)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qiáng)極盡諂媚之能。
李敖將柏楊稱作國民黨的“文學(xué)侍從之臣”,這個(gè)評價(jià)大抵是準(zhǔn)確的。
柏楊在回憶錄中說,西安事變發(fā)生時(shí),得知蔣中正被扣押,自己感到心痛如絞,覺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國就要亡了。
“我的內(nèi)心一直是11歲的我,我整天為國家擔(dān)心,為領(lǐng)袖擔(dān)心,我們把國家愛入骨髓,我們不辜負(fù)國家,我們把領(lǐng)袖愛入骨髓,我們愿意為他死。”
1941年,日寇飛機(jī)襲擊重慶,已經(jīng)是中央訓(xùn)練團(tuán)學(xué)員的柏楊在較場口的防空洞中第一次見到了蔣介石,柏楊將此視作自己的榮耀的經(jīng)歷,他回憶,“我仔細(xì)地觀察領(lǐng)袖,發(fā)現(xiàn)他鎮(zhèn)定如恒……”
可以說,蔣介石在柏楊心目中那可是“如君如父”的地位,甚至“愿意為他死”。
跟隨蔣介石到了臺灣之后,柏楊就投奔到蔣經(jīng)國麾下的中國青年反G救國團(tuán)。柏楊離開國民黨蔣氏父子的原因,一般的說法是柏楊一次與同事聊天,談起對岸軍隊(duì)紀(jì)律嚴(yán)明、不拿人民一針一線,就被發(fā)現(xiàn)“偷聽敵臺”進(jìn)而被抓了起來,卻并未判刑,放出來后,柏楊開始在雜志專欄中撰寫小說和雜文;然而,李敖考證的結(jié)果卻是“他離開國民黨核心,不再得寵,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事實(shí)如何,不是本文要討論的,至于柏楊也的確主動或被動地?fù)Q了幾個(gè)妻子,其中還有“婚內(nèi)出軌”的。
柏楊此時(shí)的雜文雖然已經(jīng)在抨擊蔣氏父子治下的臺灣社會的時(shí)弊,但大致也屬于“幫忙”或者“幫閑”的角色,“幫忙”者就是露骨地幫蔣氏父子謾罵大陸,至于“幫閑”,用姚立民《評介向傳統(tǒng)挑戰(zhàn)的柏楊》中的評價(jià)就是,“柏楊批評臺灣政治,批評傳統(tǒng)文化是實(shí),但對‘元首’父子則毫無指責(zé)侮辱之處”。
柏楊1968年的入獄,屬實(shí)“冤枉”。那時(shí)候柏楊是《自立晚報(bào)》的特刊作者,稿酬其實(shí)已經(jīng)很高,但還在兼職負(fù)責(zé)《大力水手》漫畫的編譯出版。《大力水手》漫畫中有一章,畫的是波比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gè)小島上,父子競選總統(tǒng),發(fā)表演說,在開場稱呼時(shí),波比稱“Fellows”,本應(yīng)譯作“伙伴們”,偏偏英文不大好的柏楊習(xí)慣性地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這是蔣介石的發(fā)言中常對民眾的稱呼,柏楊說他心中并沒有絲毫惡意,這是信手拈來而已,柏楊很快被冠上“打擊國-家-領(lǐng)-導(dǎo)中心”的罪名而入獄。
諷刺的是,柏楊被捕之日,還在《自立晚報(bào)》發(fā)表了響應(yīng)“蔣夫人的號召”的馬屁之作;入獄前還惦記著利用自己與蔣經(jīng)國的私人關(guān)系幫助當(dāng)時(shí)的妻子倪明華出國,他在給妻子的密件中講“可找李煥先生或逕找蔣主任,哀訴,必可獲助”,“蔣主任是熱情忠厚之人,李煥先生一向?qū)ξ谊P(guān)愛”,“蔣經(jīng)國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國,英雄必?zé)崆椋?dāng)無問題……”;直到被判決前,柏楊依然心存希望,信仰基督的他祈禱有共同信仰的蔣氏父子能釋放他……
對蔣氏父子忠心耿耿的柏楊當(dāng)然覺得自己冤枉了,于是便不停地申訴、自辯。李敖曾因柏楊針砭時(shí)弊而引為知己,于是為營救柏楊而奔走呼號。
柏楊在判刑后的答辯書中,有這樣一段:
《中華日報(bào)》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畫,畫是美國原稿,我只擔(dān)任翻譯對話說明……被調(diào)查局認(rèn)為有影射總統(tǒng)及蔣部長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偵訊,肯定的認(rèn)為我是出于惡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學(xué)生集中訓(xùn)練及從事三民主義青年團(tuán)工作,對總統(tǒng)有一種嬰兒對親長的依戀之情,至于對蔣部長,只舉一件事來做說明,臺灣中部橫貫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當(dāng)中,有一個(gè)蔣部長所住過的“不知名的地方”(后來被命名“日新岡”),我特地定名為“甘棠植愛”,這份欽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對蔣氏父子的諂媚溢于言表。
失去自由九年半,按理說柏楊該對蔣氏父子心存怨懟。可他出來之后又捧起了小蔣,他在《柏楊詩抄》的“后記”中寫道“只緣家國邁向新境,另開氣象,昔日種種,已不復(fù)再”。這是他后來與李敖交惡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對蔣氏父子的態(tài)度和立場完全不同。
當(dāng)然,要說柏楊對入獄的經(jīng)歷沒有怨言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他沒有選擇去“報(bào)復(fù)”蔣氏父子,而是選擇“報(bào)復(fù)”社會,“報(bào)復(fù)”全體中國人,于是便有了《丑陋的中國人》一書,他在愛荷華大學(xué)的演講也將自己的被冤枉入獄歸咎于“丑陋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還連帶上大陸一起罵。
這樣的腦路不可謂不清奇,李敖評價(jià)柏楊寫《丑陋的中國人》是“懦夫的行為”,還真是極其恰當(dāng)——欺軟怕硬,可不就是“懦夫”?
而說到李敖和柏楊,筆者又想到了臺灣另一個(gè)進(jìn)過國民黨監(jiān)獄的知識分子陳映真。李敖和柏楊大抵還屬于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陳映真的眼睛卻早已是向下的,他所時(shí)刻關(guān)心的是臺灣底層勞動人民的命運(yùn)。他的作品中濃厚的本土意識和致力于揭示“跨國資本對第三世界經(jīng)濟(jì)文化和心靈的侵略”,他始終不渝地崇拜和學(xué)習(xí)魯迅“關(guān)懷被遺忘的弱勢者”的精神。
反觀柏楊,他又何曾真正關(guān)心過真正的最底層的勞動人民和“弱勢者”,他又何曾真正以平等的人格對待過底層的勞動人民和“弱勢者”。
這不僅是柏楊與陳映真的本質(zhì)區(qū)別,也是柏楊與方志敏烈士的本質(zhì)區(qū)別。因?yàn)檫@樣的區(qū)別,方志敏眼中看到的是“可愛的中國”,他不僅看到了占少數(shù)的“漢奸、傀儡、賣國賊”,更看到了堅(jiān)韌不屈、奮勇反抗四萬萬可愛的勞動人民;而柏楊眼中,只有“丑陋的中國人”……
“憤世嫉俗”的柏楊,所“憤”的只是自己個(gè)人遭遇的被冤枉。
柏楊是“愛國者”嗎?或許是吧。據(jù)說他晚年曾經(jīng)為了抗議陳水扁而一度絕食。但他所愛的只是蔣氏父子這樣的統(tǒng)治者將柏楊這樣的知識分子階層引為上層階級的“國”,絕非一個(gè)勞動人民當(dāng)家作主的“國”,在這一點(diǎn)上,80年代的反毛知識精英與柏楊有著共同的趣味。
今天仍舊不遺余力地吹捧、“造神”柏楊的知識精英,絕大多數(shù)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勞動人民已經(jīng)漸漸醒來,便已不如當(dāng)初那么容易上當(dāng)受騙,繼續(xù)跟著你們膜拜柏楊了。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