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探訪了一座位于中國西北部地區的村莊:

凌晨3點,原隆村的村民就在茫茫夜色中排隊,等待接駁的車輛,然后坐一小時的車,前往私人資本承包的葡萄園勞動。干到中午12點,一天八個小時勞動,掙100元;每拉一個“勞動力”,勞務中介可以得到20元……



光明日報的博文寫道:“在這條奔向鄉村振興的路上,每一個人都在努力尋找著適合自己的位置,用實實在在的勞動開拓著自己的幸福生活。”
記者看到的是滿滿的“幸福”,筆者看到的卻是生存的不易。
“凌晨三點起床”、就近當“農業工人”,這比起二十年前的貧困村的確強多了。但筆者在想一個問題,如果這些在當地農民自己土地上流轉出去建立的葡萄園是農民自己辦的,他們的收益恐怕就不僅僅是“干一天100元”了吧?而熟悉農業勞動的人都知道,這樣的“干一天100元”的工作并不穩定,農業資本在支付了這部分低廉報酬之外,并不支付農民的社保,乃至“負擔”各種社會福利。此外,如果每個村村民都有自己合辦的葡萄園或者蔬菜基地、糧食基地,也許就不用成為流動的臨時勞動力跑這么遠的路了吧?

看到車上滿載的農民務工者,光明日報的微博下面,也有網友表示了擔憂:

這樣的擔憂并不是“杞人憂天”。
今年9月4日凌晨4點,黑龍江省勃利縣境內一重型半掛車與拖拉機相撞,致15死1傷;
僅僅過了一天,慘劇再一次發生,9月5日,安徽省太湖縣境內一皮卡車墜入山溝,致12人遇難。

兩起交通事故的背后有著共同的背景:發生事故的車輛都有超載等違規行為;遇難者都為農業務工人員……
而此類的交通事故,其實是折射出了一種已經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隨著土地流轉的加速以及資本下鄉的規模不斷加大,越來越多的個體農民已經徹底轉換了身份,成為“職業”的農業雇傭勞動工人。
當然,因為現階段的土地流轉暫時限于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農民名義上還具有對土地承包的支配權,這樣的農業雇傭勞動者還不能算著嚴格意義的農業無產者。不過,隨著各地為了“增強流轉的穩定性”,不斷延長流轉周期和規模,個體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實際上是在不斷虛化。
因為農業生產本身的時節性以及農產品周期性的市場震蕩,這樣的“職業”并不穩定,往往呈現的是短期、臨時性用工,工種比較紛雜但對技能要求普遍不高,例如剪枝、除草、施肥、打藥、采摘、搬運及包裝等。因此也就造成勞動關系很難被法律固定,勞動強度大、待遇卻普遍較低,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從業者一般為當地的中老年農民。
筆者曾經在成都周邊的幾個地級市下面的農村地區做過調研,類似的葡萄基地、柚子基地、獼猴桃基地或者蔬菜基地大量地存在著,實際的工資水平甚至還比不上光明日報記者采訪中給出的數字,一般每天的工資在60~80元,碰到農忙時節工資能到100,但每日工作時間也要在10小時以上。
而現在的葡萄都是采用大棚種植,到了噴灑農藥的季節,被雇傭的農民往往只是戴上一個簡單的口罩就要進到大棚作業。筆者站在大棚外面都因為農藥散發的味道感覺暈眩,農民在大棚作業要忍受怎樣的傷害是可想而知的。
在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出現之前,個體農戶種植蔬菜或者經濟作物的也不少,但是水果蔬菜收貨之后的儲存周期一般都比較短,農民要想盡快出售掉,就只能賣給僅存收購的經銷商人,個體農民基本不具備議價權;而市場的追漲殺跌也使農民不斷面臨著“多收三五斗”的困境,經常虧得血本無歸。
農業資本下鄉以后的規模化經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問題。不可否認,資本下鄉比起原有的小農經濟模式,的確帶來了局部的經濟繁榮,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資本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早已提供過另外一種道路。
更為重要的是,光明日報的記者將西海固地區的農業雇傭勞動者描述為“用實實在在的勞動開拓著自己的幸福生活”,將這樣的模式描述成鄉村振興和農民脫貧的典型,但是,這樣的描述遮蔽了資本下鄉和雇傭勞動所帶來的社會分化,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問題。

2019年第3期《開放時代》雜志刊登了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陳航英教授針對西海固地區的黃高縣資本下鄉狀況的深度調查報告《干涸的機井:資本下鄉與水資源攫取——以寧夏南部黃高縣蔬菜產業為例》。
這篇調查文章指出,黃高縣的蔬菜種植可追溯到1996年。2002年,“中國蔬菜之鄉”山東省壽光市援建黃高縣三百棟節能日光溫室,當地政府希望借助發展蔬菜產業促進當地產業和經濟的發展、完成當地脫貧攻堅。市場滯銷時,農戶虧損嚴重;市場緊俏時,個體農戶又出現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加之種子、化肥、農藥等成本不斷增加,農戶逐漸退出蔬菜種植。
2011年開始,當地政府大力支持各類資本進入項目區流轉土地展開規模經營。然而,在基層政府推動資本下鄉發展蔬菜規模經營過程中已經出現水資源攫取現象。黃高縣整體上屬于水資源缺乏的地區,當地主要依靠抽取地下水滿足農戶生活和生產的用水需求。伴隨蔬菜項目區的建設,“項目井”開始出現,取水量和取水速度大大超過之前的個體農戶取水,地下水超采嚴重,原住農戶的私人井就要斷水。而為了保護資本下鄉積極性,基層政府開始通過一些手段排斥本地農戶的用水權益。
與之同時,這也是一種涸澤而漁的發展模式,這種方式取得的發展成果又有多少能夠真正回饋給當地民眾?
淪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的當地農民,除了能夠獲得一點點低廉的勞動報酬,未來的生存前景卻是堪憂的。而資本本身是可流動的,下鄉資本并不需要顧及這些問題,他們大不了再去開墾下一塊“處女地”……
作為資本下鄉的替代模式,西海固地區同樣經歷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輝煌時期,只是這在后來被描述為“貧困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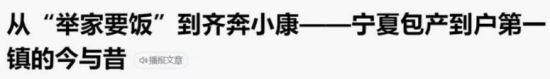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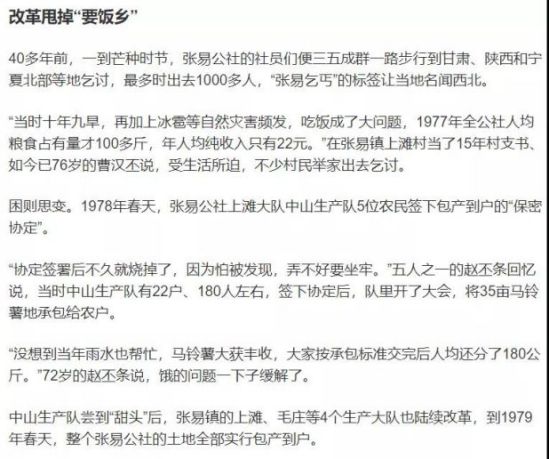
然而,同樣是在這個張易公社的上灘大隊,在1964年卻也曾被當作先進典型報道過:


歷史的真實場景是怎樣的,恐怕要留給后人書寫。但大寨的道路乃至目前還在堅持集體化道路的南街、華西,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農業集體化的道路恐怕才是農民真正脫貧致富的康莊大道。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