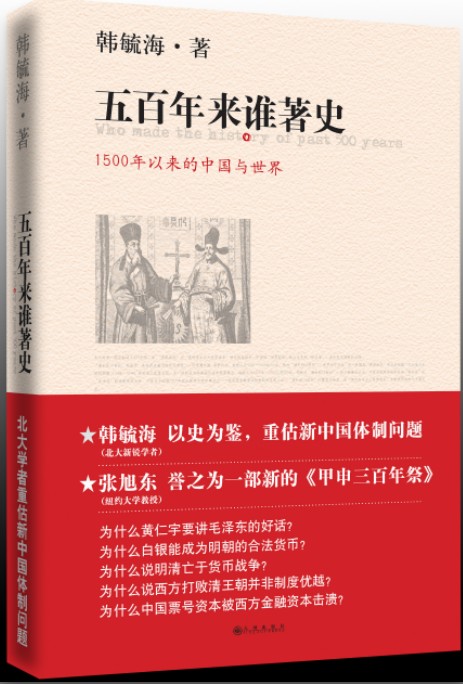烏有之鄉(xiāng)首發(fā):韓毓海新著《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睜眼看世界”書系·做清醒的中國人
選題策劃:胡楊文化
作者:韓毓海
書號:978-7-80195-993-5
出版:九州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定價(jià):32.00元
l 北大教授精心打造的《貨幣戰(zhàn)爭》升級版
l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制問題
l 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張旭東)
l 深受北大文科生追捧的思想講義
★這是一本從金融與歷史角度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著作,核心思想足以為當(dāng)下中國提供政策依據(jù)。
★作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講義,語言曉暢明快,問題意識敏銳,堪稱名家大手筆。
★作者韓毓海是北大新銳學(xué)者,國內(nèi)鮮見的大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其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和價(jià)值取向,每每引起關(guān)心國家命運(yùn)、關(guān)注底層生活的讀者的強(qiáng)烈共鳴。
★本書觀點(diǎn)尖銳深刻,直接針對時(shí)下熱點(diǎn)話題。作者把視野引向基層,引向世界,引向大歷史,從而讓大眾也能看清國際金融動(dòng)態(tài),以及中國的應(yīng)對和走向。
★本書關(guān)心國家能力和民族利益,強(qiáng)調(diào)國家金融安全,是《貨幣戰(zhàn)爭》的歷史升級版,諸多觀點(diǎn)與市面流行的《金融的邏輯》針鋒相對,面市之后,勢必引起巨大爭議。
為什么黃仁宇要講毛澤東的好話?
為什么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
為什么說明清亡于“貨幣戰(zhàn)爭”?
為什么說西方打敗清王朝并非制度優(yōu)越?
為什么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
究竟有沒有中國模式?
本書以“基層組織”、“財(cái)政金融”、“世界大勢”為三個(gè)支點(diǎn),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qiáng)弱。這一結(jié)論為當(dāng)下中國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韓毓海,北京大學(xué)教授。曾任紐約大學(xué)東亞系教授,東京大學(xué)教養(yǎng)學(xué)部特任教授。著有《摩登者說》《天下:江山走筆》等。多年來,韓毓海以其大氣磅礴的思想氣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風(fēng)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負(fù),成為“士”的精神傳統(tǒng)在當(dāng)代的有力接續(xù)。
目錄
緒 言: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制問題
上篇:“漫長的16世紀(jì)”
導(dǎo) 語
第一節(jié) “無發(fā)展的增長”與“科學(xué)發(fā)展”
第二節(jié) 歷史與迷信
第三節(jié) “當(dāng)中國稱霸海洋”
第四節(jié) 回首射雕時(shí),萬里暮云平
第五節(jié) “隆慶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轉(zhuǎn)折
第六節(jié) 重寫《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節(jié) 黃仁宇為什么要講毛澤東的好話
第八節(jié) 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歷史命運(yùn)
小 結(jié) “中國道路”與世界史問題
下篇:“漫長的19世紀(jì)”
導(dǎo) 語
第一節(jié) 重新思考19世紀(jì)
第二節(jié) 中國為什么被打敗?
第三節(jié) 國債與資本
第四節(jié) 從康德到列寧
第五節(jié) 作為“中國方法”的《大同書》
第六節(jié) “出乎意料”的現(xiàn)代性及其后果
1.專制與現(xiàn)代文明
500年來,中國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yàn)樯a(chǎn)不發(fā)展、市場不發(fā)達(dá),更不是由于什么“體制干預(yù)”過多,而恰恰由于體制的“無為”、體制的“無力”和低效率。
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于“專制制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quán)利”,這其實(shí)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于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脫離太遠(yuǎn)的空洞教條,就是由于它本身過于疏闊淺薄。
當(dāng)前,對于中國文明及其歷史命運(yùn),存在著大致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說中華文明從來輝煌燦爛,只是在1840年之后由于西方的入侵,才突然間衰落了、落后了。另一種看法則是說這個(gè)文明從根本上“一塌糊涂”,幾千來來都是“專制”和“獨(dú)裁”,因而注定是要被“現(xiàn)代文明”所蕩滌和拋棄的。本書的這一部分挑戰(zhàn)了這兩種一般性的看法,指出這些無非都是未經(jīng)過研究和思考,而得出的盲目結(jié)論。
2.國家能力
考察中國500年興衰的關(guān)鍵,其實(shí)又在于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gè)矛盾現(xiàn)象。
國家能力持續(xù)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從幾個(gè)去處尋找原因:一,中國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學(xué)蛻化為道學(xué),精英階層對于經(jīng)濟(jì)財(cái)政司法一無所知,無法承擔(dān)由宗法國家向近世財(cái)政國家,特別是向民族-人民國家的轉(zhuǎn)換;三,豪門巨富與新興外貿(mào)商人的勾結(jié),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場壟斷復(fù)又加劇,造成生產(chǎn)者和一般小農(nóng)流離失所,生產(chǎn)力大幅度下降;四,小農(nóng)喪失土地,民兵制無所依據(jù),國家喪失勞動(dòng)力,稅收長期無著,稅收無著,則無以養(yǎng)兵,故武備廢弛,不堪一擊。五,金融業(yè)委之于外國。
3.關(guān)于精英
500年來,中國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層和精英,而精英們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們總是要咒罵下層民眾“不成熟”——這實(shí)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精英”、讀書人對于什么是社會生產(chǎn)組織,特別是對于社會各階級斗爭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對金融組織、貨幣組織、稅收體制,則更是一竅不通、一塌糊涂;既將一切簡單地歸之為“體制”,而同時(shí)對于“體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膚淺,平日袖手談心性,事后著書罵“屁民”,無亂天下興亡,永遠(yuǎn)正確的反證只有他自己。這種“反體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評價(jià)估計(jì),其實(shí)也不能不是“道學(xué)家們”的“發(fā)脾氣”而已。
4.中國為什么會被打敗?
一,“文化帝國”的弊端:政治上依賴地方社會自治、經(jīng)濟(jì)上依賴社會互助、邊疆和藩屬治理主要依靠松散的文化認(rèn)同,于是國家不知何為,上下脫節(jié),內(nèi)外不通,國家能力自然持續(xù)下降。二,貨幣-財(cái)政體系混亂,貨幣金融既然依賴外國貨幣市場,而當(dāng)著1830-1850世界金融體系由“銀本位”而“金本位”轉(zhuǎn)化的歷史關(guān)鍵時(shí)刻,貨幣體系卻一朝崩潰,財(cái)政體系亦隨之而解。三,兵農(nóng)分離,從而顧此失彼,"重農(nóng)"反而導(dǎo)致了軍餉的缺乏,如此兵制必不能對抗英國的軍商合一。而國家與社會脫節(jié)、中央與地方特別是邊疆脫節(jié)、生產(chǎn)與軍事脫節(jié),如此“帝國”,自然也不能對抗西歐民族國家。
5. 歐洲的工業(yè)革命
對于歐洲的工業(yè)革命,如果不分析歐洲立足于應(yīng)對大規(guī)模戰(zhàn)爭融資制度,如果脫離歐洲軍商合一的體制,空談商人資本與工業(yè)資本的結(jié)合,這也只能是脫離具體歷史的書生之見。
為什么是在西歐、而且僅僅是在西歐,—才獨(dú)自發(fā)展出工業(yè)革命、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形式?在黑格爾和韋伯等思想家看來,除非須承認(rèn)歐洲在思想、文化、宗教和社會形態(tài)上具有根本的獨(dú)特性、具備天然的先進(jìn)性,否則就無法構(gòu)建"世界史"。這些觀點(diǎn)是馬克思所謂的”頭足倒置“的”形而上學(xué)“思考方式的結(jié)果。相反,可以用最簡單的話概括,那就是:歐洲的近代興起,并不是歐洲獨(dú)自發(fā)展的結(jié)果,更不是歐洲思想、宗教和社會獨(dú)特性、天然先進(jìn)性的結(jié)果,——因?yàn)檫@是1350年之后,在生產(chǎn)發(fā)展-市場擴(kuò)大的驅(qū)動(dòng)下,世界逐步建立其廣泛聯(lián)系的結(jié)果,”世界經(jīng)濟(jì)“是世界的聯(lián)系和彼此互動(dòng)的結(jié)果,也是世界范圍內(nèi)物質(zhì)和文化交流的結(jié)果,而不是”歐洲精神“和”頭腦“的產(chǎn)物。
6. 歐洲為什么要擴(kuò)張?
有這樣一種說法”歐洲的擴(kuò)張是要為‘世界精神尋找一個(gè)安置的場所,一個(gè)‘生存空間’“,對此,韓認(rèn)為這種說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非歷史的事后編纂,指出歐洲的對外擴(kuò)張實(shí)際上是緣于其灰暗而慘痛的“大陸意識”。這種意識與公元1000年以來歐洲大陸內(nèi)部曠日持久的互相殺伐關(guān)系密切,通過約500年的自相殘殺,從原來的約200個(gè)國家減少到至今約25個(gè)。我們今日看到的歐洲,是歷史上一批又一批部落為追兵所迫,在漫長艱辛的大陸上向西移民的過程—西班牙和葡萄牙之所以要走海到杭州這個(gè)”天堂“去,首先也是為了突破奧土曼突厥帝國從大陸方向上對其進(jìn)行的長期封鎖,葡萄牙、西班牙沖出地中海的航海活動(dòng),則兼有繞開穆斯林帝國和蒙古部落封鎖,以及到東方尋找光明的雙重目的;蒙古帝國崩潰后亞洲與歐洲之間陸上交通的中斷,作為陸地與海洋斷裂的意識,奠定了歐洲近代以來的空間觀念。
中國為什么積貧積弱?很多人以為:中國歷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視商人和商業(yè),反而是“重農(nóng)抑商”,結(jié)果商業(yè)不發(fā)達(dá),所以就不能發(fā)展出資本主義。對這種膚淺的觀點(diǎn),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經(jīng)徹底批駁過了。黃先生的基本觀點(diǎn)同樣也是說:中國歷史上的商人與生產(chǎn)活動(dòng)、生產(chǎn)者是完全脫離的,商人有了錢,無非是買地和放貸,而這些都破壞生產(chǎn)和國家稅收,正因?yàn)樯倘伺c生產(chǎn)相脫離,所以國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況近代以來,更有買辦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國資本放債盤剝中國市場和生產(chǎn)者,因此中國要完成工業(yè)革命,就非要國家資本、國有企業(yè)不可。故而對于這樣不事生產(chǎn)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則國家一定會繼續(xù)貧困下去。
盡管黃仁宇有國民黨的背景,但若單純地看黃仁宇教授關(guān)于明代稅收制度的觀點(diǎn),我們一定會發(fā)現(xiàn)他是很有些“左傾”的,其實(shí),對于壯大國家資本、國有企業(yè)這一點(diǎn),國共兩黨的政策區(qū)別本來就很小。因此他對中共建政之初,為新中國建設(shè)所選擇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還說:共產(chǎn)黨不僅僅是恢復(fù)了基層的小農(nóng)生產(chǎn),實(shí)現(xiàn)了耕者有其田的“孫文主義”,最為關(guān)鍵的是,共產(chǎn)黨更建立了牢固的社會組織結(jié)構(gòu),尤其是把一盤散沙的農(nóng)民組織起來,把農(nóng)業(yè)剩余從地主豪商手中奪取,用于國家工業(yè)化建設(shè),同時(shí)又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大量合格的現(xiàn)代勞動(dòng)者,工業(yè)發(fā)展反過來使得過剩農(nóng)業(yè)人口得以充分就業(yè)。這是中國國家復(fù)興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于注意上層結(jié)構(gòu),很少涉及底層”,[ ①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j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第454頁。] 而只有共產(chǎn)黨改造和建立了中國的基礎(chǔ)結(jié)構(gòu)。在那個(gè)冷戰(zhàn)的時(shí)代,黃仁宇能堅(jiān)持這樣的觀點(diǎn)是非常不容易的。
當(dāng)然,他的許多具體觀點(diǎn)是值得討論的,比如說,他的核心觀點(diǎn)之一是說:中國國家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重心,全在于國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資本與勞動(dòng)和生產(chǎn)結(jié)合起來,經(jīng)濟(jì)要發(fā)展,沒有勞動(dòng)者固然不行,沒有資本也不行,而沒有國家把二者結(jié)合起來,引導(dǎo)資本不斷投資于勞動(dòng),那就更是不行。故黃先生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其實(shí)不過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國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國家無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惡政,例如把糧稅交由地方豪強(qiáng),將鹽稅交由商人,勞役稅收折銀之后,稅率又交由地方官員,從來不能固定,表面上國家省事,但實(shí)際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內(nèi)卷化”——這些無不證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亂。[ ② 黃仁宇:《十六世紀(jì)明代中國之財(cái)政與稅收》,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420頁。] 但是,問題在于:國家究竟怎樣才能有為呢?具體說,國家怎樣才能夠改變資本的逐利本性,同時(shí)又不斷調(diào)動(dòng)勞動(dòng)者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更使得二者結(jié)合起來呢?對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的經(jīng)濟(jì)綱領(lǐng),而黃仁宇當(dāng)然沒有直接贊美“共同綱領(lǐng)”,而只是歸結(jié)為對明代歷史的種種敘述,但是對此綱領(lǐng),他顯然是十分贊成的。不過,要把資本家與勞動(dòng)者結(jié)合在一起,這需要一個(gè)強(qiáng)大的財(cái)政國家存在才行,即這樣的國家一方面要向資本家不斷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勞動(dòng)者不斷提供福利,方才能兩頭調(diào)動(dòng)積極性、兩面討好。但是,即使美國羅斯福“新政”長期實(shí)行造成的教訓(xùn),也已經(jīng)充分證明,這種政策的最終結(jié)果,實(shí)際上是兩不討好。因?yàn)檎f到底,將資本和勞動(dòng)結(jié)合,這無異于將狼與羊圈養(yǎng)在一起,本來就是很難實(shí)行的。
黃教授另外一個(gè)基本觀點(diǎn),就是認(rèn)為明代的稅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稅收得太少,國稅太低,國家面對千百萬無組織之小農(nóng)征稅,成本太高,結(jié)果國家沒有錢;因?yàn)閲覜]有錢,又不愿意通過加強(qiáng)或者增加稅收來解決財(cái)政問題,而是通過濫發(fā)貨幣,以通貨膨脹來掠奪老百姓的財(cái)富,結(jié)果長此以往,造成了經(jīng)濟(jì)崩潰,從而導(dǎo)致了明朝的瓦解。
盡管黃仁宇的論述可以遭到許多挑戰(zhàn)和質(zhì)疑,但是,如果我們從他所倡導(dǎo)的“五百年大歷史”的視野去反思,我們就不能不承認(rèn),黃仁宇教授有一點(diǎn)是非常深刻的。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終都沒有一個(gè)比較準(zhǔn)確細(xì)致的“國家預(yù)算”,因?yàn)闆]有準(zhǔn)確的國家預(yù)算,那么國家實(shí)際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錢,特別是需要從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賦貢收多少稅,這就是他指出的明朝“稅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更為關(guān)鍵的是,這樣一來,明朝也就不能在準(zhǔn)確的稅收基礎(chǔ)上,明白自己要發(fā)行多少紙鈔,——既不能少發(fā),但更不能濫發(fā),——因?yàn)橹挥羞@樣才能保證鈔法的穩(wěn)定,才能建立起獨(dú)立自主的貨幣制度、發(fā)鈔制度,從財(cái)政上說,這樣的國家才能說擁有自己的財(cái)政-稅收-貨幣體系,它才能成為一個(gè)真正意義上的財(cái)政國家。
貨幣金融問題,是近500年來中國最為關(guān)鍵之問題。中國貨幣的歷史發(fā)展過程高度復(fù)雜,由于長期實(shí)行多種幣制,更使得不同幣種之間的換算成為貨幣史上的難題。而從歷史看,中國在近代用銀為主幣之前,鑄幣主要用銅。漢代以降,銅禁頗嚴(yán),唐代以降,歷朝也多頒銅禁。宋以后,銀方才在市場上逐漸采用,自此銅禁漸馳。這期間魏晉至唐初,天下大亂,大體說來,民間貿(mào)易主幣為布帛,而政府收稅也采用布和谷。可見,最終導(dǎo)致白銀成為主幣,在歷史上是一個(gè)漫長而復(fù)雜的過程。
實(shí)際上,明朝初年,白銀也還并不是合法貨幣,政府甚至禁用金銀交易。從《大明會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鈔法”、“錢法”,卻并沒有“銀法”。但是,盡管政府有明確禁令,但白銀在民間市場上的使用卻并未停止,反而隨著市場貿(mào)易的活躍而漸成大潮。這首先就是由于主導(dǎo)市場的大商人手中掌握著大量白銀的緣故,白銀作為流通主幣,與他們的推波助瀾最有關(guān)系。而到嘉靖年間(1540年代),白銀的主幣化過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銀普遍通行于全社會,終于占據(jù)了貨幣流通領(lǐng)域的主導(dǎo)地位。
迄今為止,中外學(xué)術(shù)界對白銀在明代社會前后期地位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說法:正統(tǒng)初年明英宗“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認(rèn)為白銀貨幣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結(jié)果。但事實(shí)上,明代白銀貨幣化是民間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動(dòng)的結(jié)果,因此它才經(jīng)歷了一個(gè)“自下而上”的發(fā)展歷程,到嘉靖以后,經(jīng)過商人與政府的長期博弈,銀作為主幣才終于為官方所認(rèn)可,而這首先就與著名的“一條鞭法”的推行有關(guān)。
嘉靖間,浙江巡按龐尚鵬,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擁有進(jìn)口白銀的實(shí)際情況,首次奏請實(shí)行一條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頭多少征糧食租稅,并將土地稅收折合為銀;同時(shí)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銀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貢方面,土貢方物,亦皆折合為銀征收。租、役、貢都折合為銀征收,這就是一條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頭征租,這顯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擁有白銀,東南沿海,特別是浙江、福建民間進(jìn)口白銀最多,所以大商人和這些地區(qū)的城市工商業(yè)者卻是擁護(hù)一條鞭法稅收的主體,而由于各個(gè)地區(qū)土地收入不同,內(nèi)陸地區(qū)銀又很缺乏,加上這個(gè)政策默認(rèn)商人、特別是沿海地區(qū)商人的走私活動(dòng),所以反對它的聲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沒有在全國范圍內(nèi)真正實(shí)行。直到萬歷年間,張居正當(dāng)國,下制申飭全國通行這全民以交納白銀而免除賦役的一條鞭法,這種賦役折銀的做法,才最終確立下來。
這就使得白銀滲透到社會的每個(gè)角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張居正改革的這種前所未有的“重商主義政策”,一方面使得農(nóng)民的負(fù)擔(dān)空前加重,一方面卻使得商人、特別是沿海商人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也使得市場在白銀的驅(qū)動(dòng)下,前所未有地活躍起來,它促進(jìn)了這一時(shí)期商品經(jīng)濟(jì)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和市鎮(zhèn)的興起。至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朱載垕頒令: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只許用錢。而隆慶元年這條“銀錢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權(quán)形式肯定了白銀為合法貨幣,并且是用法權(quán)形式把白銀作為主幣的貨幣形態(tài)固定了下來,同時(shí)又以法的形式將城市工商的地位、權(quán)利固定下來。
當(dāng)明王朝籌劃其銀本位的貨幣體系之時(shí),一個(gè)問題自然也就隨之浮出水面:隨著白銀滲透到整個(gè)社會,社會各階層對白銀的需求就日益增長,如何解決這一嚴(yán)重的供求矛盾便成為當(dāng)務(wù)之急。對于明朝政府而言,除了從歷史上繼承下來的白銀儲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們手中,國庫擁有并不多),白銀的來源主要就是兩個(gè)方面:一是國內(nèi)自有的白銀礦藏資源,另一個(gè)自然是海外貿(mào)易交換而得的外來銀資。
白銀作為主幣地位之確立,決定了明代以降大規(guī)模引進(jìn)海外白銀的政策,正是這個(gè)貨幣政策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原有的聯(lián)系世界的貿(mào)易線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國認(rèn)識世界的方式。本來,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亞)是中國海外貿(mào)易的主要目標(biāo),而為了引進(jìn)白銀,中國的貿(mào)易線路開始經(jīng)過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陸。
明朝最終把白銀確立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原因固然復(fù)雜,但如果最簡要地歸結(jié)起來也無非兩方面:于內(nèi)因方面,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來,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貨幣發(fā)鈔體系、建立信用貨幣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從外因上說,則是由于美洲白銀的發(fā)現(xiàn),使得這種失敗變得更為迅速而徹底。
當(dāng)嘉靖皇帝繼位時(shí)的1522年,中國以其超前的科學(xué)技術(shù)水平、繁榮的市場經(jīng)濟(jì),遠(yuǎn)遠(yuǎn)領(lǐng)先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但是在“無為”的道學(xué)思想支配下,明朝卻沒有建立起一個(gè)像樣的國家財(cái)政體制和金融體制 ,皇權(quán)與士大夫的爭斗不能停止,由皇權(quán)直接面對千百萬小農(nóng)的“兩張皮”結(jié)構(gòu)也沒有改變,在長期表面的繁華掩蓋下,中國的國力卻日益衰落,上層為“道學(xué)”而戰(zhàn),基層又沒有組織,政府掌握經(jīng)濟(jì)、整合社會的能力于是不斷下降。特別是:由于當(dāng)國的官僚階級和士大夫階級不善財(cái)政、甚至恥于言利、恥于言財(cái)政,這種風(fēng)氣終明一代泛濫不治造成的結(jié)果,就是國家在與國內(nèi)的豪強(qiáng)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會失敗。而當(dāng)國家不得不將貨幣短缺的解決之道委之于商人,甚至進(jìn)一步委之于海外白銀進(jìn)口的時(shí)候,這就非但使得中國歷來不事生產(chǎn)的商人壟斷社會的局面一發(fā)不可收拾,而且,它也開了中國經(jīng)濟(jì)依賴國外金融業(yè)的先河。
中國國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說是由于封建制度對于國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其實(shí)并沒有被徹底掃除,恰恰相反,中國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來的清代獲得了新的、更為穩(wěn)固的形式,而其最為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影響中國歷史甚巨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這是因?yàn)橹袊运我詠恚肮佟迸c“吏”就是分離的,官以科舉出身,所長者無非經(jīng)史辭章,但對于財(cái)稅經(jīng)濟(jì)司法,均一無所長,于是只能將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體制,官常有升遷、有調(diào)防,而吏卻是永不升遷、無調(diào)防,這勢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為最大的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tuán)。這種官與吏分離的體制,所造成的直接結(jié)果,自然就是財(cái)稅經(jīng)濟(jì)司法,實(shí)際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說,所謂近代意義上的“國家命脈”,500年來其實(shí)都是由吏來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無升遷的吏,一向又只能是從財(cái)稅經(jīng)濟(jì)和司法中獲得、抽取利益,于是,當(dāng)著國家有任何改革,特別是面向國家財(cái)政的財(cái)政稅收改革(如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之際,其所首先觸及的就是“吏”這個(gè)集團(tuán)的根本利益,而這些改革之所以總是歸于失敗,并不是由于其出發(fā)點(diǎn)不好,或者目標(biāo)不明確,而是由于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則根本不能推行,而這種改革又往往總是與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這種“體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總是有能力、有辦法將改革轉(zhuǎn)變?yōu)閷τ诎傩盏母鼑?yán)酷的榨取,使得國家政令扭曲,最終使得意在壯大國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發(fā)社會矛盾、促使國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無他,大抵就在此“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體制。
明清兩個(gè)大帝國有一點(diǎn)是完全相同的,——就是這兩個(gè)大帝國都以白銀為國家稅收和國家儲備貨幣,也就是說,清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承襲了明制。而500年來,中國這種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供給的貨幣政策,對于世界經(jīng)濟(jì)的“變異”來說,既是決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對于明清兩朝來說,中國對外貿(mào)易的主要目的,其實(shí)主要就是為了進(jìn)口白銀——而另一方面,從長遠(yuǎn)看,由于銀根主要依賴國外,所以白銀的短缺和白銀的外流,又勢必造成周期性的、劇烈的通貨緊縮,威脅宏觀經(jīng)濟(jì),而這使得白銀問題反過來成為明清兩朝經(jīng)濟(jì)最為致命的軟肋,這甚至就是解釋明清兩個(gè)帝國突然間迅速瓦解的一個(gè)最為根本的原因。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金融體系的崩潰與軍事的失敗接踵而至,此后,中國再無財(cái)政之獨(dú)立,國家財(cái)政亦完全淪為虛名,它對內(nèi)被排斥在本國金融服務(wù)之外,對外是不能設(shè)防的——即中國無法將自己的剩余資本投資于國家的軍事自衛(wèi)的建設(shè)。從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約100年間,中國面向富強(qiáng)、現(xiàn)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謂層出不窮,但最終也沒有形成一個(gè)金融-軍事工業(yè)-工商業(yè)-農(nóng)業(yè)相統(tǒng)一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國家經(jīng)濟(jì)沒有財(cái)政的指導(dǎo),社會又無分工交換的組織能力,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國的內(nèi)戰(zhàn)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國人自相殘殺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個(gè)原因就是:中國人之間的內(nèi)戰(zhàn)持續(xù)的時(shí)間越長,對于西方的金融機(jī)構(gòu)放債、乃至賣軍火就越有好處。可見,貨幣主權(quán)蕩然無存,金融依賴海外的問題,乃是從明王朝到蔣介石政權(quán)以來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根本困局,這是中國國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回顧此番重大歷史轉(zhuǎn)變,對于今天的啟示意義起碼有二:一,中國要不要改革開放,這其實(shí)早已經(jīng)是不需要爭論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因?yàn)槲覀冏悦鞔_始就是改革開放的;500年來,最為徹底地依靠市場來組織一切的,總起來說就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我們真正需要爭論的問題僅僅是:中國為什么沒有形成獨(dú)立自主的財(cái)政和金融體制,為什么長期沒有建成一個(gè)國家財(cái)政,從而沒有完成向現(xiàn)代國家體制的轉(zhuǎn)化。而這里的核心就是:中國500年來都沒有解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問題,從而也就沒有完成徹底的反封建的使命,這就使得中國的財(cái)政、稅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團(tuán)的手中,士大夫階級徒慕虛文事務(wù),作為政治精英又是極不合格的。因此,要國家富強(qiáng),就要實(shí)行徹底的反封建,要徹底反封建,就只有發(fā)動(dòng)人民組織起來自治、起來革命,從組織基層入手推翻土豪劣紳和地方吏治,否則是沒有辦法的。這就是近代中國國家建設(shè)必從革命始的原因。
英國和西方列強(qiáng)絕非僅僅是“靠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實(shí)際上,英國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qiáng)們,更是靠它們長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債體系,逐步地控制了中國的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和生產(chǎn)活動(dòng),而鴉片戰(zhàn)爭不過是以暴力的方式,揭開了現(xiàn)代世界由資本投資主導(dǎo)的債務(wù)剝削體系的鐵幕而已。從這個(gè)意義上說,中國的近代失敗當(dāng)然也不僅僅是單純的軍事失敗,因?yàn)樗鳛?9世紀(jì)漫長歷史的結(jié)果,首先表現(xiàn)為世界貨幣-金融體制的轉(zhuǎn)換所導(dǎo)致的清國家內(nèi)部貨幣體系的紊亂,由于作為國庫存銀和“貨幣基準(zhǔn)”的“紋銀”的大規(guī)模流失,由于大量劣質(zhì)貨幣的流入造成的清代貨幣換算體系的崩潰,最終這一切,在軍事失敗之外,又勢必對晚清的國家貨幣稅收體系造成滅頂性的打擊。
由此看來,由世界貨幣體系的變遷、世界貨幣流動(dòng)逐步造成的中國內(nèi)部金融-貨幣體系的動(dòng)蕩,自然也并非是從1840年才開始的,而是在19世紀(jì)初的頭幾年就開始了、并且逐漸地加劇了。這種貨幣金融變遷,其實(shí)又早已經(jīng)潛在地、然而卻根本性地影響著中國的金融-貨幣體系,并必然會最終傳導(dǎo)到中國的國家財(cái)政-稅收體系,這就是清代國家財(cái)政日益陷入困難的根本原因。而這種國家財(cái)政的困難,當(dāng)然勢必會影響到清的國家能力——特別是國家軍事能力建設(shè)。
與金融壟斷相比,軍事暴力只不過是19世紀(jì)“歐洲文明”的一個(gè)方面,反過來說,軍事失敗同樣也只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華帝國失敗的一個(gè)方面,即軍事失敗只不過是中國國家財(cái)政失敗的最直接表現(xiàn),而中國國家財(cái)政的失敗,則是300年來中國將貨幣委之于外國的必然結(jié)果,它才是造成中國國家能力在近500年里持續(xù)下降的根本。在這個(gè)意義上,當(dāng)代中國人將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簡單地歸結(jié)為英國的“船堅(jiān)炮利”和科技文明先進(jìn)之類的說法,就幾乎是完全不著邊際的。
從更為長遠(yuǎn)的角度看,這個(gè)似乎注定的結(jié)局,首先是由于清英不同的社會結(jié)構(gòu)、特別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這種土地制度長期實(shí)施所導(dǎo)致的。如前所述,一方面,英國的土地制度是與農(nóng)奴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的,包括“圈地運(yùn)動(dòng)”在內(nèi)的對于土地進(jìn)行資本化經(jīng)營的英國土地改革,一方面將農(nóng)奴改造成一無所有的流浪漢,并為后來的城市工廠準(zhǔn)備了大量廉價(jià)勞動(dòng)力,但另一方面,在圈地運(yùn)動(dòng)中,原本一無所有的農(nóng)奴并沒有失去土地,他們失去的僅僅是服勞役的“義務(wù)”而已。因此,包括圈地運(yùn)動(dòng)在內(nèi)的土地資本化運(yùn)動(dòng),既與解決農(nóng)奴問題相聯(lián)系,在英國的條件下方才是可行的。同時(shí),又因?yàn)楣I(yè)革命的資源和市場都在“外部”,要控制外部市場和資源,就非依靠軍隊(duì)和軍事暴力不可,而英國要發(fā)展軍事力量,既要有大量流浪漢兵源,又非對國民加稅和借貸不可。而形成悖論的是,這種“英國道路的可行性”,恰恰在于英國農(nóng)奴制度相對于清王朝的自耕農(nóng)制度的落后性。
正因?yàn)榍逋醭耐恋刂贫仁墙⒃诖罅康男∽愿r(nóng)土地所有制基礎(chǔ)上的,在人口不斷膨脹的條件下,剝奪小農(nóng)的土地,不僅不利于生產(chǎn)的發(fā)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為的。因此,養(yǎng)活龐大人口,并促進(jìn)生產(chǎn)發(fā)展,就只能是通過減稅的方式、以擴(kuò)大分工剌激交換的方式來鼓勵(lì)農(nóng)民經(jīng)營和開發(fā)土地,增加糧食產(chǎn)量。換句話說:清康乾盛世以來,國家收入不斷減少,從而導(dǎo)致軍隊(duì)越來越弱,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寬仁政策所導(dǎo)致的一個(gè)“出乎意料之外的”結(jié)果,甚至是市場經(jīng)濟(jì)高水平發(fā)展所導(dǎo)致的資本積累困境所致——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而較早指出這個(gè)歷史關(guān)鍵點(diǎn)的,是日本東洋史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京都史學(xué)派的奠基人內(nèi)藤湖南。
內(nèi)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縣鹿角市,他在明治維新的時(shí)代特立獨(dú)行,積極反對明治政府推行的“脫亞入歐”的全盤歐化路線,而主張“東洋(東方)史就是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史”,日本不應(yīng)該“脫亞”而應(yīng)該“援亞”。他更進(jìn)而主張中國和同為“東洋”的日本,從根本上說代表著完全不同于英國和“西洋”的發(fā)展模式,中國雖然在軍事上被英國打敗了,這種軍事上的失敗既有其必然性,但從長遠(yuǎn)看,卻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輕言中國乃至“東洋”發(fā)展模式的失敗乃是一種“短見”。
因?yàn)閰^(qū)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場和貿(mào)易,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從事這樣的交換活動(dòng)的人,一般來說也不必是與生產(chǎn)活動(dòng)截然分離的、獨(dú)立的商人階級,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獨(dú)立的商業(yè)資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稱為近代意義上的商人階級,他們只是一邊生產(chǎn),一邊銷售的“商販”——即所謂“販夫走卒”而已。
近代中國的行商和晉商,正是這樣一個(gè)既與生產(chǎn)活動(dòng)相分離,又可以通過大規(guī)模的長途貿(mào)易把國內(nèi)生產(chǎn)組織起來的商人階級,從而它才支持了大規(guī)模的海洋貿(mào)易和大陸貿(mào)易。晉商資本,首先就是指從事跨國長途貿(mào)易的大商業(yè)資本。
但是,盡管中國的信用機(jī)構(gòu)誕生的并不比西方晚,盡管晉商擁有龐大的資本,并經(jīng)營著為跨國長途貿(mào)易提供信用服務(wù)的匯兌網(wǎng)絡(luò),——我們還是必須指出:票號資本卻并不是近代西方意義上的銀行資本和金融資本。
那么,山西票號與西方的私人銀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簡單地回答這個(gè)問題,我的結(jié)論就是——盡管山西票號大規(guī)模地投資生產(chǎn)和貿(mào)易,但是它卻并不投資于戰(zhàn)爭。正因?yàn)樗粸閲业膽?zhàn)爭行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國家賦予的以國家稅收為抵押的發(fā)鈔權(quán)。而在一個(gè)帝國主義的時(shí)代,票號只是從生產(chǎn)和貿(mào)易中獲利發(fā)財(cái),卻沒有從戰(zhàn)爭中獲利和發(fā)財(cái),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資于戰(zhàn)爭卻是西方主要私人銀行經(jīng)營的根本手段,在帝國主義時(shí)代,由于戰(zhàn)爭是最大的獲利工具,所以在這樣的時(shí)代,山西票號就完全不可能競爭過西方的私人銀行,——所謂中國資產(chǎn)階級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認(rèn)為也只有從這個(gè)角度才能得到解釋。
西方最早的私人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和英格蘭銀行)都是發(fā)戰(zhàn)爭財(cái)起家的,這就是它與山西票號的根本不同。在歐洲民族國家爭霸的條件下,西方私人銀行的基本功能,其實(shí)就是為國家提供戰(zhàn)爭借款,國家又反過來以稅收作為抵押,賦予私人銀行以發(fā)鈔權(quán)。作為國家的債主,私人銀行因而具有了“絕對的權(quán)力”,這就是為什么阿克頓勛爵說:“權(quán)力導(dǎo)致腐敗,絕對權(quán)力導(dǎo)致絕對的腐敗” [ ① 阿克頓(Lord Acton,1834-1902):《自由史論》,胡傳勝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249頁。] ——前者指國家,后者就指私人銀行。
而1840年之后,為其經(jīng)營宗旨所決定,西方金融機(jī)構(gòu)在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為,其實(shí)是通過經(jīng)營戰(zhàn)爭的方式來逐步擴(kuò)大和掌握世界市場:即它一方面為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的國家提供貸款,另一方面則又為戰(zhàn)敗國提供“賠款”的借貸“服務(wù)”,并同時(shí)要求以該國的稅收、特別是海關(guān)稅收作為抵押。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西方私人銀行逐步控制了各個(gè)國家的稅收和貿(mào)易權(quán)利,從而成為一個(gè)跨國的、壟斷的金融資產(chǎn)階級。
近代中國為什么不能富國強(qiáng)兵呢?說穿了,一方面是國家財(cái)政確實(shí)捉襟見肘,根本沒有錢投資在軍事和工業(yè)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強(qiáng)也不允許中國把金融業(yè)與軍事工業(yè)結(jié)合起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在徹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國家財(cái)政的同時(shí),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國內(nèi)融資振興軍事的能力歸于徹底的不可能。而對于山西票號而言,我們則可以說:在一個(gè)帝國主義的時(shí)代,票號資本作為喪失了“戰(zhàn)爭投資”這個(gè)最大客戶的金融機(jī)構(gòu),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說,票號資本先是不能投資于國家的軍事自衛(wèi),隨后又被排除在經(jīng)營戰(zhàn)爭借款和賠款之外,這樣它就幾乎喪失了帝國主義時(shí)代所有的“大宗業(yè)務(wù)”——在這個(gè)意義上,中國的票號資本顯然是被現(xiàn)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說是被西方的金融壟斷所擊潰的。
一
2008年9月,我在美國紐約大學(xué)教書,學(xué)校與華爾街之間徒步不過20分鐘,教學(xué)之余,正好就近觀察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金融大危機(jī)。那個(gè)時(shí)候?qū)懥恕斗疵娼滩牡膬r(jià)值》這篇文章,以英文發(fā)表之后,國內(nèi)的幾家學(xué)術(shù)刊物也想刊出漢語稿。記得高超群教授為了索要這個(gè)文章,曾深夜從北京把電話打到了紐約,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動(dòng)。最后,這個(gè)文章很迅速地在《綠葉》、《世界博覽》雜志刊出(這要感謝楊學(xué)軍先生和閻海東先生),隨之又被幾家報(bào)刊轉(zhuǎn)載,反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體會到當(dāng)今的中國是如此夜以繼日、密切地注意著國際風(fēng)云的變幻的,而自己深以為幸的更是:作為一個(gè)貨幣金融領(lǐng)域里的外行,一點(diǎn)有限的閱讀和觀察體會,遠(yuǎn)隔千山萬水,竟也能夠?qū)τ趪液屠习傩沼行┰S輕微的意義。
從中國的視野、或“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歷史的變遷,致力于探詢當(dāng)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我最近這些年來學(xué)術(shù)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說老實(shí)話,這也僅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讀書不多,尤其不是歷史系科班出身,所以這個(gè)探詢的過程,其實(shí)完全就是學(xué)習(xí)的過程。
最近500年來,我們身處的這個(gè)世界發(fā)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歐美霸權(quán)的形成并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由逐漸衰落而再次走向偉大復(fù)興。有人把這段歷史歸結(jié)為資本主義的勝利,對此我不敢茍同。因?yàn)槭紫龋烤故裁床攀恰百Y本主義”,學(xué)術(shù)界可以稱之為“正宗”的意見,起碼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紛紜眾說,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見中,一種將資本主義歸結(jié)為社會生產(chǎn)方式和社會關(guān)系的變革,特別是大機(jī)器生產(chǎn)和雇傭勞動(dòng)關(guān)系的奠定(卡爾 ·馬克思);一種著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發(fā)明,說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經(jīng),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馬科斯·韋伯);第三種則側(cè)重于自然經(jīng)濟(jì)向金融經(jīng)濟(jì)的蛻變和飛躍(費(fèi)爾南·布羅代爾)。用這三個(gè)流派來解釋什么是資本主義,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們來解釋西方之所以興起,中國之所以衰落,解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在我看來,則起碼是沒有抓住歷史要害,而且也不盡符合歷史的事實(shí)。
我認(rèn)為:最簡捷地解釋這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實(shí)際上就在于“國家能力”這一點(diǎn)上。在西方現(xiàn)代興衰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說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紀(jì)地中海地區(qū)的銀行家們投資于國家間的戰(zhàn)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fā)鈔權(quán),而讓世界上最強(qiáng)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gè)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xiǎn)埋單和作擔(dān)保(這隨著1913年美聯(lián)儲體制的形成而達(dá)到高峰),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jié)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關(guān)鍵,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眾說紛紜的“資本主義”,充其量只不過是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充當(dāng)了“幫手”的角色而已。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根本目標(biāo)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金融家的根本目標(biāo)則在于通過債務(wù)關(guān)系攫取最大利潤,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種“資本主義”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這兩個(gè)根本目標(biāo)之達(dá)成而定。
考察中國500年興衰的關(guān)鍵,其實(shí)又在于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gè)矛盾現(xiàn)象。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宋,反而打不過立足于軍事組織的遼、金、西夏部落,這里的關(guān)鍵并不在經(jīng)濟(jì),而在社會組織能力。由皇權(quán)直接來面對基層馬鈴薯一般無組織的小農(nóng),這樣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什么組織效率可言,而宋代以來的政策,反而是將組織社會的任務(wù)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yè)、運(yùn)輸乃至軍需供應(yīng)中全盤退出,國家取“無為”和“不干涉主義”,而這就是“開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層沒有組織,而且上層的貨幣財(cái)政也十分混亂,貨幣短缺、“多幣制”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明隆慶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于進(jìn)口美洲白銀,這又是財(cái)政貨幣政策的最大失敗。而對外,所謂的“天下秩序”,于周邊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貢”方式,完全沒有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空間”、“地緣政治”意識,如此組織能力松散的帝國,無論它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發(fā)展經(jīng)濟(jì),能夠或者不能夠發(fā)生“資本主義萌芽”,而一旦遭遇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之打擊,其渙然瓦解卻是必然的。而國家既然已經(jīng)瓦解,至于發(fā)展什么“主義”才好,自然也都統(tǒng)統(tǒng)變成空談了。
所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首先肇始于中國革命以建立基層組織的方式,極大提高了社會組織能力和國家效率,然后,國家才能把社會剩余有組織地投資于長期發(fā)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國家財(cái)政,在此基礎(chǔ)上方有國家發(fā)行貨幣之主權(quán),而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及其勝利,更是實(shí)實(shí)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緣政治的新格局,這種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之密切結(jié)合,靠的是無數(shù)革命前輩流血犧牲、艱苦奮斗,如此才談得上今天的“偉大復(fù)興”,而至于是否采用資本主義這副靈丹妙藥來謀發(fā)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會組織強(qiáng)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國家能力持續(xù)增長,是否有利于保衛(wèi)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術(shù)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實(shí)際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國的復(fù)興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這個(gè)真理、這個(gè)道路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fā)展中國”。這已經(jīng)為歷史所證實(shí)。
研究中國歷史,上要看貨幣財(cái)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shí)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lián)系和互動(dòng)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獲。在嚴(yán)肅的歷史問題面前,任何輕薄的態(tài)度、任何教條主義的盲從都是必須杜絕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寬慰的是,上述淺見,并不是盲從得到,而是從自己的讀書、思考和摸索中得來的。幾年來,就這樣一邊讀書,一邊思考,逐漸積累了一點(diǎn)筆記、一系列的問題,不過時(shí)間一長,反而倒是更沒有把這些學(xué)習(xí)體會寫出來的勇氣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問題,自然也就隨時(shí)光流失,逐漸淡忘了。
真正的寫作機(jī)緣來自赴美前學(xué)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蔣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個(gè)學(xué)術(shù)講座,由于參加講座者都來自基層,以從事財(cái)政和稅務(wù)工作的同志為主,既是學(xué)校的任務(wù),于我自然是一個(gè)很艱巨的工作,這就迫使我不能不緊急準(zhǔn)備一個(gè)初步的講稿,這樣幾天下來突擊搞了幾萬字的稿子,由于對當(dāng)?shù)氐膱D書館沒有信心,所以還帶了不少參考書到山西。我本是個(gè)過于認(rèn)真又不堪大任的人,這次面對的又是上千人基層干部的大課堂,講座結(jié)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給山西的同志(特別是曾被授予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wù)員”稱號的李晉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煩。但是,期間參觀八路軍太行紀(jì)念館,以及抗戰(zhàn)最艱苦時(shí)期建立的八路軍總部(雖曰“總部”,實(shí)際上不過農(nóng)舍三小間而已)的經(jīng)歷,對我觸動(dòng)非常之大,應(yīng)該感謝這次較長期地面對基層的機(jī)遇,它使我近距離地感受到:我們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義,我們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撓,絕大多數(shù)在基層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勞儉樸,中國歷史的展開是如此的篳路藍(lán)縷、波瀾壯闊,中國改革和中國革命的大業(yè),確是由生活在最基層的老百姓苦苦支撐起來的,這真是“作始也簡,其成也巨”!
太行山里本來也沒有什么書可讀,躺在賓館養(yǎng)病的時(shí)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講座前許多沒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這突乎其來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進(jìn)益的一個(gè)機(jī)緣,在這樣一個(gè)機(jī)緣之后,我領(lǐng)會了一些以前不甚領(lǐng)會的書上的語句,尤其包括歷史上的改革與革命。
二
中國改革與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結(jié)果,革命當(dāng)然不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后的原因。而對于“中國近代何以落伍”這個(gè)大題目,則大致又有幾種回答:其一,是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全球擴(kuò)張所致;其二,則是一般地、抽象地將其歸之于中國在制度、技術(shù)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歐的先天優(yōu)勢(以馬科斯·韋伯的理論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gè)以“天下”和“世界”為擔(dān)當(dāng)?shù)奈拿鳎Y本主義則是自1500年以來從地中海地區(qū)發(fā)展起來,以金融和軍事技術(shù)為核心,向世界擴(kuò)張的體系。這兩種有深刻歷史傳統(tǒng)的組織形式,在500年歷史間漫長的“互動(dòng)”、博弈,才構(gòu)成了我們解釋500年來世界大勢和中國“天下興亡”的關(guān)鍵。從這個(gè)角度說,那些構(gòu)成中國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國長期繁榮的因素,這正如我們文明中固有亟需變革的弊端,但其中卻同時(shí)也蘊(yùn)涵著近代改革與革命以及中國現(xiàn)代復(fù)興的種子。只有了解中國文明形成的長期性、歷史性、復(fù)雜性,同時(shí)又了解資本主義制度產(chǎn)生的歷史性和復(fù)雜性,而不是抽象地將問題歸之于抽象的“制度”和“體制”而簡單地打發(fā)掉,我們才能對于上述重大歷史課題作出真正有意義的探究。
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于“專制制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quán)利”,這其實(shí)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于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脫離太遠(yuǎn)的空洞教條。對其淺陋機(jī)械,前人已多有譏評。如錢穆就曾說:“談?wù)哂忠芍袊茻o民權(quán),無憲法。然民權(quán)之表達(dá)亦各有其方式及機(jī)構(gòu),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jī)構(gòu),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行之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yōu)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jī)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wù)成績規(guī)程,以為官位進(jìn)退之準(zhǔn)則,則下情上達(dá),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quán)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rèn)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quán),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實(shí)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shí)未能切實(shí)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之兩大骨干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于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yīng)食之惡果也。” [①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商務(wù)印書館,2009年,第15-16頁。]
中國當(dāng)然不是從來沒有制度。自上古以來,就有以黃帝為代表的“血緣世系”以及以堯舜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個(gè)世系而言,權(quán)力的合法性來自貴族血緣承繼;就后一個(gè)世系而言,權(quán)力始終是向平民開放的,這就是所謂:“人人皆可為堯舜”。而這里的“平民”,更不專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農(nóng)工商各階層——特別是包括少數(shù)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數(shù)民族血統(tǒng)者,太祖朱元璋以貧苦農(nóng)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來自于堯舜的名分世系。這兩個(gè)世系的互動(dòng)沿革,就是所謂“多元一體”的制度基礎(chǔ)。從歷史的長時(shí)段看去,倡導(dǎo)“天下為公”,不斷向平民、向少數(shù)民族開放權(quán)力的堯舜世系、堯舜體制,是比導(dǎo)致羅馬帝國迅速崩潰、貴族院壟斷權(quán)力的“憲政”更合理、更進(jìn)步、更能經(jīng)受歷史考驗(yàn)的制度,這已經(jīng)為中國的長期統(tǒng)一、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所證實(shí)。
作為最后一個(gè)漢家王朝,明朝無疑處于中國制度的重要轉(zhuǎn)折期,從體制的上層看,其主要特征表現(xiàn)為:它是歷史上皇權(quán)與士大夫階級沖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廢除了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這成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極大變動(dòng)。從此天子直接面對六部,六部有建議權(quán),而天子則獨(dú)攬決策權(quán),另設(shè)內(nèi)閣大學(xué)士,為天子襄理文墨,但內(nèi)閣大學(xué)士沒有建議權(quán),為了避免皇帝與六部之間發(fā)生直接沖突,遂設(shè)司禮監(jiān)居中傳遞協(xié)調(diào)。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間,皇權(quán)與六部之間的沖突,終于達(dá)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階段,竟造成這三任皇帝幾乎不見六部官員的局面,此后,作為皇帝代言人的內(nèi)閣大學(xué)士和司禮監(jiān),與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間的沖突更是日益加劇、不可協(xié)調(diào)。而正是皇權(quán)與官僚體制之間的激烈沖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來國家行政效率、國家組織效率的迅速衰敗。
而這一時(shí)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變革時(shí)期,因?yàn)橐粋€(gè)銀行家、戰(zhàn)爭和國家密切結(jié)合的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與國家合一的體制,此時(shí)正在歐洲勃然興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國,國家體制的上中下結(jié)構(gòu)卻開始走向脫節(jié),以至于國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動(dòng)員官吏,反而總是被龐大的官吏集團(tuán)所阻礙,國家組織效率的嚴(yán)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經(jīng)濟(jì)改革都不能真正實(shí)行,實(shí)際上,最終導(dǎo)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權(quán)專制的原因,更有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階級之顢頇獨(dú)斷。無能而顢頇的士大夫階級為了一己之私,妄圖以道學(xué)的專制壟斷社會權(quán)力,這種“士大夫階級的道學(xué)專制”,更促成了體制從內(nèi)部的解體。而正是由此看來,錢穆的博學(xué),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學(xué),因?yàn)樵谒抢铮瑹o論均田重農(nóng)還是平等夷狄,這些都不算數(shù),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專制。而他所同情、追隨的國民黨,雖曾標(biāo)榜、號稱要繼承中國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權(quán)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國式的“考試”與“監(jiān)察”兩院,以成為“五權(quán)”憲法,而這種精英運(yùn)動(dòng)的體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歷史所證明。
不過,確如錢穆指出:民權(quán)的表達(dá)和實(shí)行不能單靠一紙憲法和幾個(gè)代議士,關(guān)鍵在于形成下情上達(dá)的有效機(jī)制,他的這種看法倒是真有啟示性的。而且,毫無疑問的是,誠然如他指出:中國作為一個(gè)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說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制度”而只有“專制”,例如所謂公田與私田、科舉與選舉、郡縣與封建的制度爭論,實(shí)際上就一直貫串于中國歷史之中,并構(gòu)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改革與革命的真正動(dòng)力。看不到這一點(diǎn),自然也就不能說對中國的文明有起碼的了解,那甚至就會淪為錢穆所譏諷的: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惡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擔(dān)起“改革的后果與代價(jià)”,這往往就與精英們沒有知識和眼光,只會看見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關(guān)系。
而與錢穆比較起來,黃仁宇先生雖未打過仗,畢竟吃過糧(古人只把“軍糧”稱為糧),因此,他的有些話恐怕還算是比較到家的。他說:“過去的中國百年史,過于重視上層結(jié)構(gòu),很少涉及低層。比如說,民國初年的立憲運(yùn)動(dòng)與政黨,他們本身對社會是一種外來異物(foreign body)。其領(lǐng)導(dǎo)人不乏高遠(yuǎn)的理想,而他們身后卻無支持的選民(constituency),滿腹經(jīng)綸自然也無從化為具體方案,更何況滲入民間,所以一遇軍閥逞兇,就無能為力,而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也因而消失。” [ ①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j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第454頁。]說到制度變革,孫中山以來的改革家們其實(shí)最終也都不得不認(rèn)識到:這絕非立一紙憲草、推幾個(gè)“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這里的道理,就在于“變制度易,變社會難”(這一點(diǎn)魯迅等“先覺者”其實(shí)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無可措手”地痛感著)。因此,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那就非要從基層做起、從中國人口的大多數(shù)——農(nóng)民做起、從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變革社會,就非要找到、找準(zhǔn)中國社會的真正主體不可。以為單靠幾個(gè)“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爛之舌即可變革中國,這不過就是黃口小兒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說:500年來,中國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層和精英,而精英們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們總是要咒罵下層民眾“不成熟”——這實(shí)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至于說到變革中國的主體,近代中國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為,曾寄望于作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孫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黨,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變革中國、特別是進(jìn)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決土地制度問題、訓(xùn)練和組織廣大農(nóng)民,從勞苦大眾、從最基層出發(fā)改造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這才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功領(lǐng)導(dǎo)中國完成民族革命,再領(lǐng)導(dǎo)中國走向社會改革與社會革命的關(guān)鍵。而倘若放棄了這根本關(guān)鍵,汲汲于從上層、從書生們的狹小視角空談所謂的“制度”和“技術(shù)”之優(yōu)劣,無論是搞“三權(quán)分立”還是玩什么“五權(quán)憲法”,那就不僅是短視,而且是舍本逐末,而這種“瞎折騰”,終將自食“改革造成的惡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時(shí)下人們恐怕都知道,近代以來,中國沒有科學(xué)、工業(yè)、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離開組織勞苦大眾特別是農(nóng)民這個(gè)中國社會主體,離開了改造土地制度這個(gè)中國經(jīng)濟(jì)的最深層的基礎(chǔ),如果沒有與基層現(xiàn)實(shí)密切聯(lián)系的革命政黨作為社會改造的利器,那就不會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國幾千年來皇權(quán)直接面對千百萬馬鈴薯一般小農(nóng)、毫無動(dòng)員效率可言的“一盤散沙”的社會結(jié)構(gòu),更不能得以根本改變。正是毛澤東、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一舉改造了中國的基層結(jié)構(gòu),歷史告訴我們:今天絕不能小視人民組織起來的力量,更不可小覷創(chuàng)立社會基層結(jié)構(gòu)的偉業(yè),因?yàn)樗环矫媸沟棉r(nóng)業(yè)上的剩余得以轉(zhuǎn)用到工商業(yè),同時(shí)又使得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反過來可以吸納大量的人口就業(yè)謀生,而且,國家從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財(cái)政管理,這又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獨(dú)立自主的發(fā)鈔權(quán)和貨幣主權(quán)。——但是,對于這一淺顯的道理,卻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認(rèn)的。以為靠“個(gè)人自由”、一紙憲草、幾個(gè)“民意代表”就能解決一切中國問題,這其實(shí)就是中國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見、偏見和一塌糊涂的“政見”。“豈有文章驚天下,漫道書生事不成,百年一覺浮漚里,悲欣交集說摩登”——其實(shí),就我個(gè)人來說,真正弄明白這個(gè)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2008年8月,我?guī)е@個(gè)初步的講稿到了紐約,當(dāng)時(shí)課程較多,沒有充分的精力再讀大量的書,只能找一些相關(guān)的英文書來讀,一邊再就舊稿提出的問題,重新思索一番。而在美國教書時(shí)比較談得來的朋友,如康奈爾大學(xué)的顏海平教授、紐約大學(xué)的張旭東、廖世奇教授在看了這個(gè)初稿之后,都認(rèn)為我應(yīng)該繼續(xù)寫下去,于是在他們的鼓勵(lì)下,我就不時(shí)在舊稿上改動(dòng)一點(diǎn),日積月累,這樣改來改去,終于成為了本書的第一部分:《漫長的16世紀(jì)》。
哈德遜河畔仲秋望月,中央公園圣誕踏雪,第八街上法式公寓里徹夜的燈火,寒來暑往,幾度合上最后的書頁,匆匆走出辦公室,門口的百老匯大街已經(jīng)是凌晨時(shí)光,——如此情景,今天依然歷歷在目。喧囂的世界金融中心紐約,于我竟是個(gè)讀書寫作的好地方。如今披閱舊稿,其中仿佛還散發(fā)著那些艱苦時(shí)光的余溫。
回國以來幾個(gè)月,給北大文科的研究生同學(xué)開一門“現(xiàn)代西洋理論閱讀”課,由“客座”身份重歸主人地位,心情自然大為舒暢。而這門課實(shí)際上就是閱讀西方研究中國和中國歷史的著作,課程的講義除了《漫長的16世紀(jì)》一部分外,更加入了《漫長的19世紀(jì)》一部分,由于聽課的同學(xué)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xué)各個(gè)專業(yè),所以他們給我的啟發(fā)是很深的,很多過去想不清楚的問題,這次倒是在課堂上反而討論出了眉目;結(jié)果是臨到學(xué)期結(jié)束,大家興猶未盡,對我來說,一本書的大體框架,也算初步完成了。
三
西洋的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是比較重視哲學(xué)和思想的,這可能是黑格爾的傳統(tǒng)。它有很大的好處,就是綱舉目張,可以根據(jù)一種哲學(xué)、一種思想來解說歷史。但歷史畢竟不是思想史和哲學(xué)史,本書所探究的這500年的世界史之復(fù)雜程度,就完全超乎人們的想象。知道了西洋怎么樣,就照貓畫虎,開口即說中國怎么樣,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樣,就說明代如何如何,那么歷史研究就變得索然無趣,好像幾個(gè)公式就能解決問題似的。
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沒有思想史的研究、經(jīng)濟(jì)史的研究和社會史的研究——寬泛地說,也就是我們不能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史學(xué)傳統(tǒng)。沒有了這樣的研究傳統(tǒng),歷史研究就會墮落為以“帝王家事”治天下的“演義”,這在中國歷史上叫做“道學(xué)家”的邏輯,在中國民間叫說書人的邏輯,在這種邏輯的支配下,歷史只能等于統(tǒng)治者的歷史、甚至是統(tǒng)治者的家事、家計(jì),乃至淪為胡編亂造的逸事,所表彰者無非道學(xué)家們自我標(biāo)榜的“氣節(jié)”和“氣功”而已。這本身就是不知何謂歷史,其實(shí)就是一種愚昧。
無論如何,用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來解釋歷史、觀察歷史,這是我們必須堅(jiān)持的正確方向。在這方面,我們的前人已經(jīng)給我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xiàn)、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比如用小自耕農(nóng)發(fā)生、發(fā)展得比較早而且成熟,從而造成生產(chǎn)方式的過于分散和靈活,來解釋中國為什么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革命、產(chǎn)業(yè)革命(郭沫若);比如從國外資本、國內(nèi)稅收、地主地租的三重負(fù)擔(dān)壓迫,來解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性(陳翰笙);再比如自古中國的商人就不事生產(chǎn),商與生產(chǎn)相脫離,尤其是自宋發(fā)明“開中法”以來,國家竟然從組織社會活動(dòng)、特別是商業(yè)活動(dòng)中一概退出,而將貿(mào)易、運(yùn)輸乃至軍需轉(zhuǎn)運(yùn)這類活動(dòng)也一概委之于商和地方豪紳,從而造成國家與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脫節(jié)、商人與生產(chǎn)脫節(jié),以此來解釋國家資本、民族國家在現(xiàn)代中國的必要性(陶希圣)——無論這些前輩的政治觀點(diǎn)如何、立場如何,他們都是從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演化出發(fā),給我們指出了歷史發(fā)展的道路,初步厘清了歷史的脈絡(luò)。
前面已經(jīng)說過,治史者最難得的是有三重視野: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cái)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致力于這項(xiàng)工作的黃仁宇曾經(jīng)感慨說:“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視野,則在檢討中國現(xiàn)代史時(shí),必須先看清當(dāng)中的大輪廓。在社會全面解體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時(shí)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可能前后牽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即使親臨其境的人物,如克倫威爾、丹東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進(jìn)歷史的工具,也難看清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真實(shí)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目的的分析而不綜合,難能盡到歷史家的任務(wù)。我們縱使把郭松齡和殷汝耕的事跡寫得不失毫厘,又牽涉到本莊繁和岡村寧次的秘幕,在當(dāng)中更投入梅蘭芳和阮玲玉的瑣聞軼事,也只是增長歷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shí)性格。”——而他這里所說的“中國長期革命”,就是指從19世紀(jì)到20世紀(jì)的“漫長的革命”,而上述視野,概括起來說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今天歷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實(shí)。因?yàn)闆]有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分析,沒有思想史、社會史和經(jīng)濟(jì)史的綱領(lǐng),沒有社會各階級分析的觀點(diǎn),也就不能解釋歷史的發(fā)展和變化,這樣就變成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事實(shí),不見發(fā)展、變化、運(yùn)動(dòng)的邏輯。歷史的實(shí)質(zhì)全在變化,而這樣的歷史研究,卻非但不關(guān)心歷史變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會現(xiàn)實(shí)變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幾本中國古書和外國新書的知識,乃至名人軼事,去批評、點(diǎn)綴和套用現(xiàn)實(shí)的變化,而這種對于變化的拒絕,其實(shí)也正是對于歷史本身的拒絕。
四
今天的我們,正處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重大變革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視的大現(xiàn)實(shí),這是500年人類歷史中最為天翻地覆的大變化。對于這個(gè)大變化,既有的知識是不夠了,任何人都必須重新學(xué)習(xí)、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維教授最近從國外回來休假,找我長談,他的一個(gè)說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從海外看中國,60年至為成功,500年來也有不少好的東西,以至于當(dāng)今世界上有“中國模式”之說;不過反過來,有些國內(nèi)人看自己,特別倘若是聽某些知識界“高人”說話,卻幾乎是一派悲觀喪氣,甚至以為前景可憂,“崩潰”在即——而他們千憂百轉(zhuǎn),其實(shí)就憂在“政治體制”。
“憂患”當(dāng)然不是壞事,但“憂患”應(yīng)該是憂天下、憂國家、憂老百姓,絕不是憂自己,更不能因?yàn)槭澜鐩]有按照自己的辦法來,甚至沒有因?yàn)椤按h”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職,就斤斤兩兩、患得患失。正因?yàn)槊裰鳌⒆杂墒钱?dāng)世的好東西,時(shí)賢無論“左右”,才紛紛作“為民請命”狀,拉大旗作虎皮,這本不奇怪。但是我們絕不該忘記,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先驅(qū)都曾經(jīng)反復(fù)告誡我們說:如果把民主講成了抽象、簡單的“官民對立”,那就是最大的膚淺和不及格,因?yàn)檫@樣做起碼就放跑了利益集團(tuán)和地方分離勢力,而在近代以來的語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國主義列強(qiáng)的壓榨。如果那樣搞,所謂“民主”就很容易成為某些人要特權(quán)、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淪為列強(qiáng)們壓迫中國的口實(shí)。
官僚政治不好,其惡性膨脹于國家人民不利,這自是誰都知道的最淺顯道理,不過歷史卻也總是沒有那么簡單,比如我們還是要知道:自古以來講“官民對立”,這里所謂的“民”,其實(shí)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時(shí)賢所謂“屁民”)。而在這個(gè)意義上,國家與豪強(qiáng)巨族、土豪劣紳之間的矛盾,往往也就體現(xiàn)為代表國家稅收利益的官僚與“豪民”之間的矛盾,所謂“官家之惠,優(yōu)于三代,豪強(qiáng)之暴,酷于亡秦”(荀悅《漢紀(jì)論》),這種出于官僚之口的“官民對立”,表達(dá)的恰恰是對土豪劣紳、豪門巨族的指斥和控訴,代表的其實(shí)就是“國家”與“小民”立場的重合,它同時(shí)也表明國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實(shí)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敵人,而這個(gè)敵人也就是豪強(qiáng)和“豪民”。
因此,商鞅廢井田,楊炎行兩稅法,張居正舉“一條鞭”,其根本出發(fā)點(diǎn)盡管不能說是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著想考慮,但是,他們要打擊豪強(qiáng),要把稅收加在豪強(qiáng)和豪門頭上這一點(diǎn),卻是共通的,也是無疑的;這就是王安石所謂“擇其富者而稅之,擇其可稅者而稅之”。現(xiàn)代中國對于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最精深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王亞南(《資本論》的譯者),他這樣告訴我們說:只有看到官僚制度的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與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面,更有與地方勢力、特權(quán)利益集團(tuán)相矛盾的另一面,我們才能了解官僚制度的彈性和歷史發(fā)展。因此,在這個(gè)意義上說,政治改革的關(guān)鍵,并不在于抽象地講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的對立。至于今天的中國“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個(gè)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而抽象地講“官民對立”,則必定流于喪失和缺乏階級分析方法的膚淺。我們只有認(rèn)識到:國家從來就不是抽象的,甚至只有認(rèn)識到國家總是有階級性的(如美聯(lián)儲掌握發(fā)鈔權(quán),這就是美國國家“階級性”之體現(xiàn)),我們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國家體現(xiàn)勞動(dòng)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國家成為特權(quán)利益集團(tuán)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對立”說,表面上看似義正詞嚴(yán)反對官僚政治,實(shí)則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強(qiáng)”一邊,為了特權(quán)階層和豪強(qiáng)向國家討利益和爭權(quán)力,其實(shí)它也從來并不是一概地反對國家,[ ①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1年,第78頁。]因?yàn)閺臍v史上看,他們要的往往就是奴隸主、地主豪紳和買辦資產(chǎn)階級支配的國家,而他們極力反對和限制的,其實(shí)是勞動(dòng)者當(dāng)家作主的國家而已。
中國近代改革的先驅(qū)康有為說過:“故國無論君主民主,未有不中央集權(quán)也”,“政府者,集合管理眾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聞以地方各立為分權(quán)也”,這是考慮到中國歷史的深層動(dòng)因和內(nèi)外形勢而得出的結(jié)論。康有為進(jìn)而指出:體制改革的真正目標(biāo),就是“民主政治”與“政治統(tǒng)一”的結(jié)合,就是人民與政府的結(jié)合,如果不實(shí)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參與,就不能避免動(dòng)亂,如果不打擊利益集團(tuán)和地方勢力,如果不能反對帝國主義列強(qiáng),如果沒有一個(gè)強(qiáng)大的、為人民服務(wù)的政府,不但現(xiàn)代中國在近代以來列強(qiáng)競爭的環(huán)境里不能圖存,一切事情都會被內(nèi)部利益集團(tuán)的爭權(quán)奪利、家計(jì)私利所毀掉,那樣國家就會分裂,人民就會真正受苦。這也是歷史的結(jié)論。
今天的中國自然不是沒有問題,相反,問題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yàn)槿绱耍覀儾挪荒軐栴}簡單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脫離開社會階級分析和世界局勢的視野看歷史、看現(xiàn)實(shí)。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認(rèn)識到:保持國家里面勞動(dòng)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國家淪為特權(quán)階層、買辦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工具,特別是在思想文化領(lǐng)域里保衛(wèi)中國革命歷史敘述的合法性——于今天而言這是多么艱巨而光榮的任務(wù)。我們常說要不忘歷史,而老百姓把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只有從這樣樸素的視野才能看到,中國今天的成就當(dāng)然既不是吹出來的,更不是“粉飾”而能得來的,因?yàn)檫@就是中國歷史和世界史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如果把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之于“上層專制體制”,那么,我們是否反過來,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歸之于“上層專制體制”呢?我倒是認(rèn)為,與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勞動(dòng)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結(jié)果,是漫長的社會生產(chǎn)方式變革的結(jié)果,是世界廣泛聯(lián)系和互動(dòng)的結(jié)果——尤其是漫長而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結(jié)果。從這個(gè)角度說來,倘若說500年來中國體制中沒有好東西,中國革命形成的體制是一團(tuán)漆黑,非要拆了故宮建白宮,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墳而后快,這是不懂自己的歷史,這也就是割斷自己的歷史。這種歪曲歷史的行徑是絕不能允許的。
五
說到體制改革,從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張居正,改革、改制一向就是歷代儒家追求的歷史目標(biāo)。宋代以來行“開中法”,放手讓商人代替國家組織社會、從事長途貿(mào)易甚至包辦軍需,這就是因?yàn)榛蕶?quán)直接面對小農(nóng),國家沒有組織效率。明代大行“一條鞭”,擇其可稅者而稅之,也是考慮到國家直接面向千百萬零散小農(nóng)征稅成本太高的緣故。王安石興“青苗法”,欲使國家財(cái)政直接補(bǔ)助小農(nóng),其出發(fā)點(diǎn)更不可謂不好,但是,由于基層沒有組織,地方全為酷吏、土豪控制,王大人所補(bǔ)貼的對象,不幸最終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他的“青苗法”,就幾乎淪為今天所謂的鼓勵(lì)農(nóng)民“種大棚”(時(shí)下民諺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窮,種大棚)。500年來,改革的目標(biāo)何嘗不是提高國家組織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則全由于沒有完成建設(shè)基層組織的任務(wù),所以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層的酷吏與土豪,結(jié)果這些以反封建為目標(biāo)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至于將組織社會的任務(wù)全盤交給商人和市場,1567年之后更將貨幣委之于進(jìn)口白銀,這也并非國家迷信道學(xué),傳統(tǒng)政治格外喜歡無為,而是宗法國家里,皇權(quán)對小農(nóng)的“兩張皮”結(jié)構(gòu)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國家欲動(dòng)員社會而沒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近代以來,宗法國家瓦解,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開始,打倒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chǎn)階級,是為了奪回國家財(cái)政和貨幣主權(quán),打倒封建主義鏟除土豪劣紳,則是為了建立基層組織。“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革與革命被中國文明視為“天命”,一卷《大同書》唱響了紅旗,改革與革命的目標(biāo)并不僅僅是改造中國,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們應(yīng)該清醒地意識到:當(dāng)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國家與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謂“官民對立”),而當(dāng)下的社會財(cái)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實(shí)則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發(fā)達(dá)資本主義國家聯(lián)合推出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政策,它以貨幣投資政策的巨大調(diào)整(以維持美元和美國債券價(jià)值為主要目標(biāo)),又一次使得資本主義凌駕于“世界經(jīng)濟(jì)”之上。如果費(fèi)爾南·布羅代爾在世,他一定會驚呼這是堪比19世紀(jì)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結(jié)構(gòu)“大轉(zhuǎn)型”。這就是為什么,過去的幾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經(jīng)歷了“漫長的19世紀(jì)”的回潮和復(fù)辟。綿延的戰(zhàn)爭和最終無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機(jī),其實(shí)都是這次“大轉(zhuǎn)型”的結(jié)果,今天看來,如果沒有中國最終頂住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面統(tǒng)治,世界經(jīng)濟(jì)和世界形勢恐怕就不堪設(shè)想。
基層組織和上層財(cái)政金融之外,我們還必須看世界大勢。只有把握世界大勢,才能認(rèn)識到:當(dāng)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壟斷體制,而軍事優(yōu)勢則是最直接、最強(qiáng)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權(quán)軟刀子殺人不見血,為“整人”而定的國內(nèi)、國際“規(guī)則”,恐怕也不見得全是政客們想出來的——只是少見我們的道學(xué)家們因資本金融壟斷而“憂”、因帝國主義軍事壟斷而“憂”、因買辦資產(chǎn)階級腐敗透頂?shù)乃接谢叨皯n”罷了。
其實(shí),體制既然無非就是組織、組織能力,而關(guān)鍵就在把誰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反抗誰、又要維護(hù)誰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體制”和“反動(dòng)的體制”這兩種,而從來就沒有過什么抽象的、一勞永逸的“體制”和“反體制”。本書的一個(gè)基本觀點(diǎn)就是:我們只有從生產(chǎn)方式的“發(fā)展”與“組織”之間的關(guān)系角度,從復(fù)雜的社會階級斗爭的角度,才能去正確分析、了解歷史變化發(fā)展的真實(shí)。500年來,中國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yàn)樯a(chǎn)不發(fā)展、市場不發(fā)達(dá),更不是由于什么“體制干預(yù)”過多,而恰恰是由于“體制”的無為、體制的“無力”和低效率。廣大的勞動(dòng)階級(特別是農(nóng)民)長期處于一盤散沙狀態(tài),中國基層社會更與上層完全脫節(jié),以至于像黃仁宇所說:經(jīng)濟(jì)雖大有發(fā)展,而社會卻全無組織效率,從而無法將社會財(cái)富組織為國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體制”的方式參與這種發(fā)展、保證這種發(fā)展、推動(dòng)這種發(fā)展,結(jié)果反而在近代為外國和外部的金融資本和武力、為內(nèi)外特權(quán)利益集團(tuán)之勾結(jié)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精英”、讀書人對于什么是社會生產(chǎn)組織,特別是對于社會各階級斗爭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對金融組織、貨幣組織、稅收體制,則更是一竅不通、一塌糊涂;既將一切簡單地歸之為“體制”,而同時(shí)對于“體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膚淺,平日袖手談心性,事后著書罵“屁民”,無論天下興亡多少事,永遠(yuǎn)正確的反正只有他自己。這種“反體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評價(jià)估計(jì),也不過就是“道學(xué)家們”的“發(fā)脾氣”而已,而自明以來,這種士大夫階級的“氣功”,對于國家和人民,從來就沒有過什么真正、切實(shí)的補(bǔ)益。這也就是張江陵所謂“國家以高官厚祿養(yǎng)此輩,真犬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謂“國家以此為學(xué)為官,與用牧豬奴何異?”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五星中的四顆星分別是工人、農(nóng)民、小資產(chǎn)階級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上述四個(gè)階級的聯(lián)合,是因?yàn)樗麄冇兄餐臄橙恕I辦資產(chǎn)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因反對共同的敵人而有著共同的利益。而與1688年拿著銀行家資產(chǎn)階級的錢上臺的英國王室革命不同,中國共產(chǎn)黨人是靠工農(nóng)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黨人不欠資本家的錢,因此就沒有格外要訂立一個(gè)契約專門照顧資產(chǎn)階級利益,與之立憲的任何理由。嚷嚷著要單獨(dú)為某一個(gè)階級立憲,其實(shí)質(zhì)就是要破壞四個(gè)階級的聯(lián)合。歷史證明,當(dāng)工農(nóng)不愿意與后二者聯(lián)合的時(shí)候,固然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chǎn)階級;而當(dāng)著小資產(chǎn)階級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忘記了工農(nóng)的利益與自己根本利益的聯(lián)系的時(shí)候,他們更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同樣也正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chǎn)階級,那種不自量力的狂熱,使得他們只會在歷史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只有當(dāng)上述四個(gè)階級聯(lián)合起來組織起一個(gè)強(qiáng)大的體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就是我們這個(gè)體制的根本目標(biāo)。這個(gè)目標(biāo),當(dāng)然是要讓勞動(dòng)者越來越有可能控制資本,讓中國越來越有可能擺脫帝國主義的軍事、金融控制——從大的方向說,這是真正的“通三統(tǒng)”、“復(fù)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順天應(yīng)時(shí)”的體制改革和體制革命。如果沒有這樣的體制革命,那么,資本控制勞動(dòng)和市場、西方控制世界、少數(shù)人控制絕大多數(shù)資源、少數(shù)人壓迫剝削多數(shù)人的體制就會一統(tǒng)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國的發(fā)展談不上、和諧的世界談不上,公平和正義也就談不上了。
早在68年前,毛澤東就批評過這樣的學(xué)風(fēng):“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rèn)真地研究現(xiàn)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rèn)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他還說:“你們看,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chuàng)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xué)形態(tài)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jīng)濟(jì)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從鴉片戰(zhàn)爭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chǎn)生一本合乎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實(shí)際的、真正科學(xué)的理論,像在中國經(jīng)濟(jì)問題方面,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jīng)高了呢?——實(shí)在不能說。”今天重讀他的這些話,作為讀書人和教書匠,實(shí)在是應(yīng)該深以為警怵的。
20世紀(jì)曾被稱為“革命的世紀(jì)”,盡管這并不是本書這一卷論述的主題,但是,上面這些話,既可以說是游離于本卷主題之外,也算是對本書第二卷(《1500年以來的中國改革與革命》)的預(yù)告。故算是有感而發(fā),不平則鳴。而這里的所謂“不平”,特別是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及其成就——一個(gè)勞動(dòng)者階級當(dāng)家作主的國家體制,近些年來在中國輿論界當(dāng)權(quán)的騙子們那里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所表達(dá)的憤懣、不滿和抗議。
顧炎武的《精衛(wèi)》,一直很喜歡。詩曰: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shí)。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在這個(gè)意義上,讀歷史、研究歷史是大有好處的,因?yàn)闅v史敘述著過去,也昭示著未來。歷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寫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六
本書準(zhǔn)備的材料原本是寫三卷,與編輯者商量,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卷。
這當(dāng)然不能算是史學(xué),連歷史研究可能也談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結(jié)論,同時(shí)又把中國史與西方歷史打通來看,把世界史理解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動(dòng)史,對我這個(gè)讀書不多的人來說,這可能多少是需要點(diǎn)勇氣的。
我在這里要敬表謝意的,是這些年來在學(xué)術(shù)上幫助、教誨我的不同學(xué)科的朋友們,如黃平、汪暉、張承志、張旭東、李零、李書磊、姚洋、顏海平、嚴(yán)海蓉、林春等等,至于需要感謝的北京大學(xué)的師友們,更是不能一一列舉。而尤其要敬表感激的,是張國有教授的教誨和幫助,無論作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前輩還是大學(xué)校長,他對于年輕人的一貫理解、寬容、支持和關(guān)懷,使我得以真切地感受北京大學(xué)光榮的歷史和傳統(tǒng),也將永遠(yuǎn)激勵(lì)我把“為中國讀書”、“為人民服務(wù)”作為人生目標(biāo)去追求。
胡少卿先生奔走聯(lián)絡(luò),親自編輯,助成此書面世,這體現(xiàn)了北大師生之間的平等、友誼與默契,更體現(xiàn)了北大“團(tuán)結(jié)緊張、嚴(yán)肅活潑”的學(xué)習(xí)和工作作風(fēng)。
2009年9月2日初稿
國慶節(jié)改定于北京
咨詢電話:010-62760856-11/0
郵 箱: [email protected]
Q Q: 909077839
烏有之鄉(xiāng)淘寶網(wǎng)店>>>![]() 烏有之鄉(xiāng)百度網(wǎng)店>>>
烏有之鄉(xiāng)百度網(wǎng)店>>>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