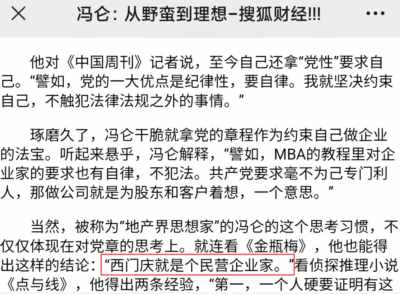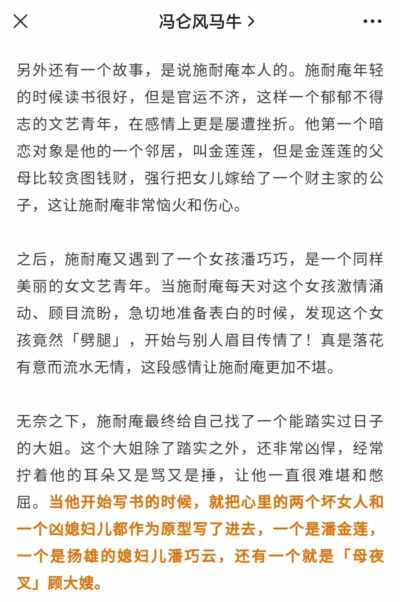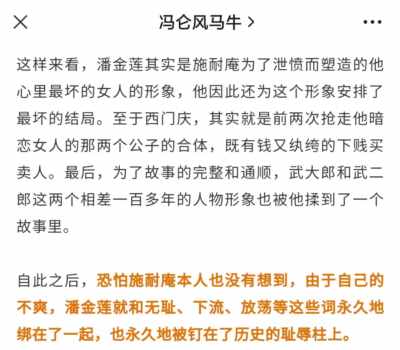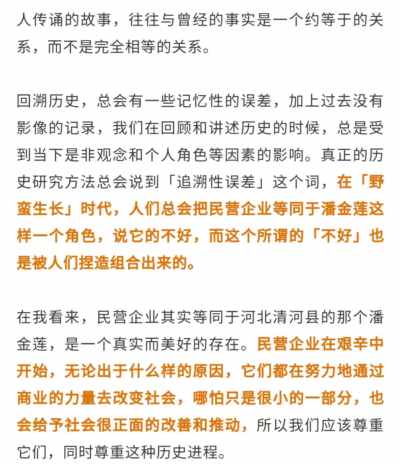2013年1月,《中國周刊》雜志刊登過一篇專訪地產商馮侖的報道《馮侖:從野蠻到理想》。馮侖在訪談中語出驚人:“西門慶就是個民營企業家”。
后來,馮侖參加深圳博商匯舉辦的“深圳市民營企業家盛典”,對西門慶給出了更高的評價:
“西門慶其實就與潘金蓮做了一件事,卻被后人記住了,而被大家忽略的是西門慶其實是一位出色的民營企業家。”
2016年底,馮小剛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上映的時候,“馮侖風馬牛”公眾號刊登了馮侖“西門慶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馮侖:潘金蓮的姿勢》。
在這篇文章中,馮侖將“潘金蓮”比喻成“民營企業”。在馮侖看來,參加過農民起義軍的施耐庵是為了泄私憤才塑造了潘金蓮這個壞女人形象,導致后來人對西門慶和潘金蓮產生了極大的誤解,破壞了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家的形象。馮侖在文章中稱稱:
在「野蠻生長」時代,人們總會把民營企業等同于潘金蓮這樣一個角色,說它的不好,而這個所謂的「不好」也是被人們捏造組合出來的……在我看來,民營企業其實等同于河北清河縣的那個潘金蓮,是一個真實而美好的存在。
筆者并不喜歡馮侖先生的這后一個比喻,這顯然有將潘金蓮物化的嫌疑,正如毛主席所評價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暴露了封建統治,暴露了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不好。”
不過,既然馮侖先生將西門慶比喻成了經營“民營企業”(潘金蓮)的“出色的民營企業家”,那也只好先沿著馮侖先生的這個設定來討論。
馮侖先生訪談中聲稱他是通過讀《金瓶梅》,得出“西門慶就是個民營企業家”,而且是“出色的民營企業家”這個結論的。我們不妨也回到《金瓶梅》的原著,看看西門慶究竟是個怎樣一個“出色的民營企業家”。
按照《金瓶梅》原著的描述,西門慶的原有資本并不雄厚,他出生于“清河縣中一個殷實的人家”,父親西門達是個開生藥鋪子的。但西門慶通過不長時間的經營,實現了資本暴增、經濟實力急劇膨脹,不僅在商業界產生很大影響,而且對政界也產生極大反響。
《金瓶梅》第一回說他“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專在縣里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這里“放官吏債”,即把國家財產拿出來放債,收取利息;“把攬說事過錢”即替人打官司,替別人說情或辦事,從中收取別人的感謝費。不難看出,西門慶的社會活動能力是相當大的,“放官吏債”也是挺有風險的。
單靠這些小打小敲滿足不了西門慶斂財的欲望,通過婚姻來謀取大筆的嫁資是西門慶積累資本的主要手段。如他先后騙取了富孀孟玉樓、太監侄媳李瓶兒,兩位小妾的到來為他帶來了巨額財產。
此外,西門慶深知,“馬無外草不肥,人無外財不富”,在他積聚資本的過程中尤其重視對外財的掠奪。如女婿陳經濟,因為其父陳洪東窗事發,遂將家產轉移到丈人西門慶家保存,最后也被西門慶占為己有。
利用女人攫取金錢和權力,利用手中權力或者私人關系網,放官債或替人包攬訴訟——優秀民營企業家西門大官人的手段放到現代社會也毫不過時。90年代,香港出了有很多“爭奪家產”題材的電視劇,例如那部當年收視率力壓《大時代》的《巨人》。而這些“奪產”電視劇的很多橋段,與西門慶的手段其實是相似的。
“出色的民營企業家”西門慶有了錢就開始貪淫好色,勾引良家婦女,這在常人看到是道德敗壞的,但可能在馮侖先生看來只是小節——“食色,性也”嘛,今天的大老板也大多如此。
西門慶的另一個高明之處,在于他很會規避法律風險,做“守法”企業家,這可能也是馮侖先生欣賞西門慶的地方所在。在今年3月17日的亞布力論壇上,馮侖先生還在講:
“讓我回過頭來想,三十年了,今天剩下來的實際上都像企業家,不在了的,都是江湖上有點像大哥……到今天,關于賺錢的法律有將近400個……這些東西規范了你的行為,所以今天創業的人,就在這個空間里能夠活下來,就真是企業家。”
從這一點講,西門慶的確“出色”,可謂是精通大宋律法。
西門慶是一個精明的商人,但使他在同行中遙遙領先的,其實完全在于他慣常使用的手段——通過不正當競爭和勾結官府以謀取優惠的經商條件。
如新中的狀元蔡一權在回鄉探親時路過清河縣,應邀請到西門家打秋風,不僅有好酒好菜和美色伺候,臨走還借去白銀一百兩。后蔡一權任兩淮巡鹽史,還將山東巡案宋喬年介紹給西門慶,使西門慶有了更多的途徑勾結官府。再后來西門慶販鹽,經營鹽運業,蔡狀元行使兩淮鹽運使之權,讓西門慶比別的鹽商早掣取一個月鹽引,使西門慶在短短一個月輕而易舉的謀取了兩萬兩銀子的暴利!
原先清河縣只有西門慶一家藥店,后來醫生蔣竹山在李瓶兒的幫助下也開了一家中藥店。于是西門慶唆使地痞流氓無賴,多次到蔣竹山的藥店鬧事,還偽造票據,硬賴他欠賬不還并訴之官府,把蔣竹山打的半死,迫使他拆了藥鋪。這樣,西門慶的藥店生意依舊紅火。
這種不正當的競爭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如他善于打通關節,買通鈔關錢主事,大筆逃稅漏稅;再如,從西門慶的經營方式來說,他的商業活動主要靠家人,奴仆或與別人合伙,或假托他人名義進行的,自己則躲在幕后操縱,因此他的違法經營很難被別人抓住把柄。
即便就是馮侖先生在深圳博商匯講的“西門慶其實就與潘金蓮做了一件事,卻被后人記住了”——這件事即便在欣賞西門慶的馮侖先生看來也是“錯”事,那就是西門慶為了獨占潘金蓮,毒死武大郎;然而,西門慶卻是巧妙地利用了大宋律法,逃避了法律的制裁,那就是賄賂縣官屬吏,收買驗尸官何九叔,偽造了武大病故的尸檢結論。這樣的做法,即便放到今天去打官司,西門慶也能夠以“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所以,武松在懷疑哥哥武大死因,初步取得關鍵物證之后,前往縣衙擊鼓,狀告西門慶謀嫂殺兄,被知縣以證據不足駁回。
從西門慶的這些手段看,陽谷縣的營商環境不可謂不好。不過馮侖先生既然把潘金蓮比作“民營企業”,那潘金蓮的原配、經營燒餅攤的武大郎不也算是民營企業家嗎?為何陽谷縣令不善待武大郎?這其實就是資本運動的必然規律——“大魚吃小魚”,同樣是民營企業家,還得看“資本量”,雖然“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所以,大宋律法的天平總是向更有資本的西門慶傾斜。
“遺憾”的是,西門慶這一次碰上了身為“都頭”而精通刑偵,同樣精通大宋律法,而且武力值爆表的武松。
雖然明知西門慶是利用了法律“漏洞”,逃避了法律制裁,但嫉惡如仇的武松并沒有一時沖動,而是展開了一系列非常冷靜、非常理智的行動,最終使罪犯伏誅。
破案關鍵在取證。于是武松首先去找仵作何九叔,取得了證明武大郎死于中毒的兩塊骨殖,以及西門慶賄賂的證據——一錠白銀;第二步,武松又找到了關鍵目擊證人——鄆哥;第三步就是要取得當事人(潘金蓮、西門慶、王婆)的口供,但潘金蓮等人顯然不會主動承認罪行。
起初,武松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去辦理武大郎遇害一案。因為按照大宋律法,就足以治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死罪,為兄報仇。
通奸者按《宋刑統·雜律》“諸色犯奸”條規定:“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謀殺從犯者按《宋刑統·賊盜律》“謀殺劫囚”條規定:“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不加功者流三千里……”西門慶為潘金蓮毒殺武大郎提供了協助,所以,即便兩罪并罰,“加功者”西門慶應處以絞刑。
至于潘金蓮,除了通奸罪,更有謀殺親夫罪,足以斬首。依《宋刑統·賊盜律》謀殺條:“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
(以上內容截取自2018年3月30日《人民法院報》第7版文章《武松復仇案件的法律評析》)
所以,武松在初步取得前兩項證據之后,就跑到縣衙報官,希望知縣依法提審潘金蓮等嫌疑人。然而,收了西門慶好處的知縣大人,卻對西門慶等人采取了“不捕不訴”的態度,再以證據不足唯有駁回了武松的訴訟,這就導致案件偵破陷入僵局。
武松并沒有氣餒。他先穩住潘金蓮說:“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眾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眾鄰。”潘金蓮不知道武松的意圖,也就照辦了。
等到武松請了一眾鄰舍街坊,武松當著眾人的面讓王婆、潘金蓮等人對質,成功取得了潘金蓮和王婆的口供。不僅如此,武松還在現場要求一位鄰居負責記錄口供,另外四位鄰居簽字畫押,從而獲取了最為關鍵的證據,而且通過現場目擊證人保證了證據的有效性。
不過,武松已經知道西門慶買通了陽谷縣令,即便證據確鑿,陽谷縣令也很有可能依法幫西門慶脫罪,讓潘金蓮和王婆當替死鬼;而自己一個小小的都頭是沒有權力去查辦陽谷縣令的,更不可能扳倒陽谷縣令。
于是,武松先是當場擊殺潘金蓮,留下王婆(除了能減輕武松的罪刑,還能保留關鍵人證),然后大搖大擺地殺上獅子樓,再當著眾人的面,揭露西門慶的罪行,殺了西門慶。
身負兩命的武松依然還在冷靜地取證,他對圍觀的鄰舍街坊講:“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卻才甚是驚嚇了高鄰。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今去縣里首告,休要管小人罪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
這種做法一方面向社會輿論公布了西門慶等人的罪行,使得陽谷縣令無法再包庇西門慶;另一方面證實了自己擊殺西門慶,是為復仇的“故殺”(因故殺人)。
后一方面非常關鍵。《宋刑統·賊盜律》“親屬被殺私和”條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及夫為人所殺,私和者流二千里,周親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遞減一等,受財重者,各準盜論。雖不私和,知殺周親以上親,經三十日不告者,各減二等。”
按照大宋律法,當時的司法制度是倡導和支持“有仇必報”這一樸素道德信念的,而武松本身又有軍功在身。所以,縣令最后為了撫平民意,不得不以“忠義”為由,將背負了兩條人命的武松輕判了個“脊杖四十,刺配兩千里外”。
由此可見,武松真是一位智勇兼備,知法、懂法、用法的英雄好漢。難怪毛主席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曾詼諧地說,“李逵、武松、魯智深,這3個人我看可進共產黨,沒人推薦,我來介紹。”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