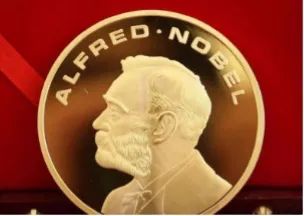
二戰后,西方大國無法像過去那樣進行殖民統治,越發重視通過“思想殖民”方式對非西方國家進行間接控制。在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武器中,最隱蔽的做法之一,就是通過頒發各種國際獎項,來塑造和引導非西方國家的價值體系,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所謂審美標準。
這是因為,人類從認知到實踐本身就是個環環相扣的鏈式反應過程:政策觀取決于戰略觀,戰略觀取決于價值觀,價值觀又受審美觀影響。審美觀可以說是國家意識形態鏈條的源頭之一。正像科學體系建構的前提是若干毋庸置疑的公理,每個國家價值體系大廈的根基,同樣是不證自明的是非標準和審美標準。一旦審美觀發生顛覆性變化,便會不知不覺地改變一個民族的價值觀,最終導致災難性的戰略和政策。國際大獎看似只頒給少數群體,實則具有很強的示范帶動效應。
在這方面,諾貝爾獎知名度高,同時意識形態色彩也較為明顯,是西方重構和引導非西方國家價值體系的重量級武器。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以來,以1974年哈耶克和1976年米爾頓·弗里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為標志,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時代。但這些經濟學理論并未促進世界經濟增長,而是拉大了國內和國際貧富差距。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應對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負有一定責任。在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普通勞動者乃至國家都是全球利益再分配的輸家,唯有大資本力量成為真正的贏家。
從國際戰略角度看,諾貝爾文學獎和和平獎經常被西方國家當作實現地緣戰略的重要工具,目的就是將那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或地區收編到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中來。在這方面,蘇東陣營的經歷最為典型。冷戰時期,西方為從思想上瓦解蘇東陣營,頻頻給蘇東國家的異見作家頒發諾貝爾文學獎。蘇聯共有5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蒲寧(1933年)、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肖洛霍夫(1965年)、索爾仁尼琴(1970年)、約瑟夫·布羅茨基(1987年)。這些作家的作品大多或隱或現地帶有解構革命、反抗蘇聯政府色彩,因而符合西方解構蘇聯價值體系的口味。
蘇聯解體后,西方國家將戰略重心轉向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世界成為西方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點對象。在此背景下,伊斯蘭世界的作家,如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穆克、旅法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旅法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雷、尼日利亞作家奇努阿·阿切貝、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等等,一夜之間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其中,埃及作家馬赫福茲、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先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盡管很難一一甄別這些作家的作品,但它們無疑是符合西方精英口味的。
諾貝爾和平獎看似是推動世界和平,褒獎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的人士和組織,實則同樣是西方國家收服非西方世界的糖衣炮彈。挪威本身就是北約成員國,與美國、英國關系密切。有學者尖銳指出,諾貝爾和平獎實際是個支持戰爭的獎項,并列舉出5個證據:一是該獎項刻意塑造“我們是好人”的宏大敘事,據此有權決定世界其他國家的命運;二是美化非西方國家的持不同政見者,為西方國家策動政權更替創造條件;三是通過制造特殊議題(如保護婦女權益等),為西方國家發動戰爭制造理由;四是渲染對手使用各種不人道的武器(如化學武器、凝固汽油彈等)的話題,借以發動戰爭或進行制裁,如禁止化學武器組織就獲得2013年諾貝爾和平獎;五是褒獎有利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利益的和平條約,如1990年戈爾巴喬夫因向西方讓步而獲獎。
近些年來,伊斯蘭世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士也在增多。2003年,伊朗社會活動家希爾琳·艾芭迪因“為民主和人權,特別是為婦女和兒童的權益所作出的努力”獲得和平獎;2005年,埃及的穆罕默德·巴拉迪,因擔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期間,“在防止核能用于軍事目的,并確保安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作出巨大努力”而獲獎;2011年,也門的塔瓦庫·卡曼,利比里亞的埃倫·約翰遜-瑟利夫和萊伊曼·古博薇因“為女性安全以及女性全面參與和平建設工作權利所做的非暴力斗爭”,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14年,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尤薩夫扎伊和印度人權活動家凱拉什·薩蒂亞爾蒂,因“反抗針對兒童和年輕人的壓迫,捍衛了兒童受教育的權利”共同獲得和平獎;2015年,名不見經傳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組織,因“對促進突尼斯多元民主進程做出決定性貢獻”獲得和平獎。這些獲獎者“事跡”各異,但無不符合西方國家引導伊斯蘭世界價值觀的總體要求。吊詭的是,就在這些伊斯蘭世界人士頻頻獲得諾貝爾獎的同時,伊斯蘭世界卻飽受西方欺凌,日漸陷入政治動蕩和經濟蕭條交織的黑暗深淵。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隨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圍堵和遏制力度增多,中國所謂“異見人士”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和概率也在增加。這恰恰表明,“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距離中國越來越近。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