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智能手機下單購物,等無人車將包裹送到家中,用語音控制家里的音箱播放音樂,帶上AR眼鏡玩一款身臨其境的游戲……越來越多的技術正與我們的生活融為一體,為我們創造出前所未有的便利,但絕少有人思考,我們為此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一部智能手機的背后,可能是剛果童工的廉價勞動;無人車的發展,敲響了大批司機失業的警鐘;智能家居入侵我們的住宅,收集我們最私密的信息;AR技術讓我們在現實和虛擬里迷失……
這些技術是如何運作的?它們對我們構成怎樣的挑戰?誰從這些技術中受益、誰又從中受害?Verso出版社的新書《激進的技術:日常生活的設計》(Radical Technologies: The Design of Everyday Life)將這些技術逐一剖析。作者Adam Greenfield是杰出的科技思想家,曾于十年前擔任諾基亞副總裁,近年則專攻科技與城市空間、共享經濟與社會發展議題。
土逗公社對Adam Greenfield進行了專訪,著重探討了近年來被熱炒、但普通人較難理解的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是一種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用密碼技術控制貨幣的生產和轉移,無需經過銀行等中心化機構。獲取新比特幣需要用電腦解答數學難題,這一過程被稱為“挖礦”,操作者被稱為“礦工”。目前,各國對比特幣的接受情況不一。
問:比特幣這個話題看起來蠻重要,但普通人理解起來頗有難度。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比特幣,它是如何存在的?它的價值來自哪里?
答:首先我必須承認,我還不知道比特幣是否有任何價值。圍繞加密貨幣和比特幣的宣傳不計其數,但并沒有什么有意思的東西。到頭來它可能什么都不是。但當你評估未來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時,審視一個可能性不高、但影響很大的事件,仍然是重要的。如果區塊鏈技術真的是21世紀組織社會經濟體系的方式,它將產生巨大的影響,理解它為何物就會顯得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異乎尋常地復雜,不是研究一兩次就能弄懂的東西。它是如此反直覺、如此古怪,以至于我無法想象它是由人類創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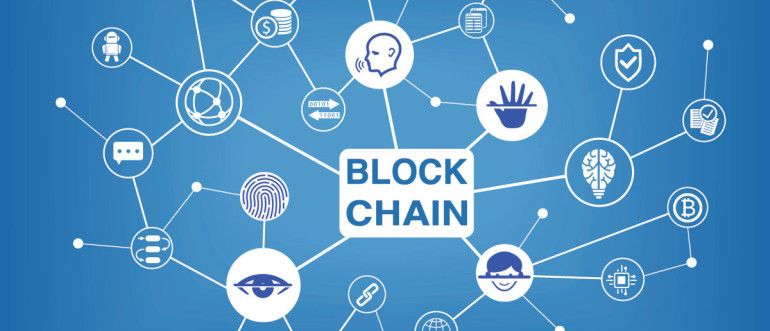
摘自Wikipedia:區塊鏈(blockchain/block chain)是用分布式數據庫識別、傳播和記載信息的智能化對等網絡, 也稱為價值互聯網。中本聰在2008年,于《比特幣白皮書》中提出“區塊鏈”概念,并在2009年創立了比特幣社會網絡,開發出第一個區塊,即“創世區塊”。圖片來源:網絡
另一點我們討論區塊鏈時要牢記的,是加密貨幣的設計是由一種特定的政治抱負所激發的。區塊鏈技術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參與設計它的人們從根本上喪失了對中心化機制的信任,無論這些機制是國家的還是私人的。他們(區塊鏈的創造者們)從根本上想要將事物去中心化,令世界由獨立的個體組成,這些個體彼此建立契約式的私人關系,這樣整個世界就絕少有自愿連結的個體之上的組織存在。
這是無政府主義的想法,但這是右翼無政府主義的想法。這是無政府主義資本家對世界的構想,他們很少談論平等,很少談論當前權力關系下受壓迫的人類的解放。實際上,就目前而言,它傾向于讓有權力的人變得更有權力,讓懂金融的人更富有。它有意地賦予一些人和機構更大的權力,卻將另一些機構的權力榨干,后者之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國家。
每一筆比特幣交易都不是由中央賬本(ledger)確認生效的,而是由去中心化的賬本來確認。比特幣網絡中的每臺電腦都持有這個賬本的副本。這意味著并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告訴大家,這筆錢值錢。如果你從根本上相信國家是無權者、被壓迫者的守護人,那么任何傷害國家的事物都將傷害這些人。但如果你認為國家才是壓迫者,那么你就能理解這些人為什么想瓦解國家。
問:作為一種虛擬貨幣,比特幣如何解決“信任”的問題?當大部分商品未能用比特幣交易、大部分政府未能允許比特幣與實體貨幣兌換時,人們為何對這種貨幣抱有信心?
答:我不認為它真的“解決”了信任問題,它只是“延后”了這個問題。它令你不必再信任一個機構,但你要把信任轉移到算法,以及運行這套算法的、跑代碼的機器網絡之上。如果你不信任那套代碼,就談不上信任比特幣。
當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設計比特幣初始協議的時候,我記得他在那篇最初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有人在比特幣網絡擁有51%的計算能力(computing power),他們就能改寫區塊鏈,寫上任何他們想寫的東西。但中本聰認為,考慮到整個世界的計算能力,控制51%的計算能力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大約在2014年,就在他寫下那篇文章六年之后,這已經變得非常可能。就在我們坐在這里的時候,兩個中國的比特幣礦場之間的計算能力可能已經超過了50%,如果他們決定聯手,一場51%的攻擊就是可能的。
問:你提到中國的比特幣礦場。這些礦場是中國公司持有的還是海外資本持有的?
答:很難說是誰持有的,它們的所有權可能分散在層層嵌套的公司之中。但有趣的是,每當我查看比特幣的交易,總能看到人民幣兌換入比特幣。事情很顯然,富有的中國人通過投資比特幣將他們的錢轉移出去,就像他們投資倫敦的房地產一樣。如果說有什么人從比特幣和區塊鏈中獲益,我猜當數中國的富豪們。

圖片來源:網絡
問:中國除了有使用比特幣的富豪,也有挖礦的礦工們。一些比特幣礦場之所以選址四川,也是因為那里電費便宜、氣溫較低以及人力成本低。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否成為了生產比特幣的“世界工廠”?
答:中國確實存在一些既有的條件,包括物質的、氣候的、人力的、技術的,這些條件疊加起來,令中國在比特幣的格局中處于相應的位置。其結果顯示,比特幣的世界并不是平的。比特幣并非如它的發明者可能設想的那樣,可以消除地區間的差異。這是連非常聰明的人都時不時會犯的錯誤,即認為技術是自主的。事實上,當你把一項技術帶到這個世界,它往往會成為現有社會結構的一部分。這一結構根深蒂固,很難通過創造一項新技術改變什么。
問:比特幣的價格近期不斷打破紀錄,有分析認為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亞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答:比特幣價格飛升,是因為它承擔的兩種職能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張力。任何被當作貨幣的東西都有三種基本職能:作為交換媒介——我給你一個豬肉包,你給我一美元,我們認為這兩種東西是等價的;作為記賬單位——用它來給資產和債務標價;作為價值儲存——我存下五美元,期待它升值,這更像是一種投資。比特幣的問題或者說設計上的缺點在于,它必須讓這兩種職能同時起作用。一方面它是交換媒介,比如我向你買東西,付給你比特幣;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投機性商品,在這種情況下它更像是黃金。

比特幣價格的網站 https://price.bitcoin.com,圖片來源:bitoin.com
目前對比特幣的興趣主要來自亞洲,但比特幣在西方有深刻的市場定位。另類右翼(alt-right)人士對比特幣很感興趣。這就像表明你自己的政治態度,通過表達對比特幣的興趣,通過使用比特幣這個詞。
問:比特幣社區主要是由另類右翼人士組成的嗎?
答:在2017年、在西方,我認為可以這么說。如果這不是客觀事實,至少我感覺是這樣。
問:所以對比特幣的興趣與它背后的意識形態有關?
答:我認為這在某種層面上是正確的。有一群核心人士理解加密貨幣最初的意識形態,并為其投資。由于初始用戶群內意識形態的連續性,一種由無政府主義資本家發明的技術,會出于某種理由,吸引別的無政府主義資本家、技術自由意志主義者、激進的個人主義者、自我中心的無政府主義者。
但我認為也有些人不了解比特幣產生的政治背景,也不知道它來自什么樣的社區,而只是意識到這種貨幣和他們政治觀念體系之間有某種自洽。這些人構成了比特幣的第二波擁躉,他們和比特幣的發明者們沒有很深的聯系,他們更年輕、更精通網絡,所以我用了“另類右翼”這個詞。我認為這些人在比特幣身上找到了親近感,但他們未必完全了解了比特幣是什么。
問:也有新聞說很多日本和韓國的家庭主婦在炒比特幣,她們的身份好像跟上述比特幣社區相去甚遠。而且通常會認為,她們是較為保守的投資者,為什么她們會對這樣高風險的產品感興趣?
答:僅僅作為猜測的話,我認為是社會感染效應很強,特別是在我稱之為“后儒家社會”(post-Confucian societies)的地方。在日本和韓國,像安利這樣的多層次直銷公司大獲成功是有原因的,甚至在韓國,這些營銷一度是違法的,因為它太有效了,人們會用自己的家庭、學校網絡來說服別人購買他們原本不需要的東西,并且成為安利的經銷商。我認為對于比特幣而言,可能也有同樣的原理在起作用。這就像是安利一樣的龐氏騙局,盡管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比特幣被設計成永久通縮的(permanently deflationary),可被挖的比特幣總數有一個上限,出于計算的原因,它會一直變得越來越難挖。理論上,每一比特幣的價值只會一直上升,這讓它看起來像是一項值得的投資。這或許是一些保守的投資者被比特幣吸引的原因。而且在韓國和日本,女性往往要對家庭財政負責,我猜她們是想(通過投資比特幣)保障家庭的未來。但問題在于,這些錢進入比特幣的投機市場,可能會突然造成損失。如果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決定人們不能用比特幣購買任何東西,那么你的投資很快會變成零。
問:在上午的新書發布會中,你提到在科技發展的早期,科技圈曾經有一種“解放的文化”(a culture of liberation),這種文化為什么消失了?
答:有至少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我說的是事實,但不是完整的事實。完整的事實是,我談論的那些當時充滿希望的、思想開放的技術文化,已經是一種軍事工業的文化,因此這種對 “解放”的文化興趣是建立在軍事工業向科技發展投資的基礎上的。那就是復雜的現實。你會看到這些人(科技發明者)最終是在軍隊或企業的合同下工作的。那不是完全地、純粹地關于“解放”——其中可能有對“解放”的真誠的興趣,但那是在更深層次的事物和文化之上的對“解放”的興趣。
其次,個人的“解放(liberation)”和集體的“解放(emancipation)”之間必然存在張力。這些技術非常擅長賦權于個人,它可以令一群排隊等地鐵的人看著完全不同的東西。即使他們都在用Facebook,他們看到的也是不同面的世界,而其他人對此無法感知。因此我的感覺是,技術的個人主義面向超越并最終壓倒了解放集體的愿望。如果這些網絡、技術、交互功能能被設計得不同一些——我不會說為時已晚,我們最終會到達這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設計互聯網協議。如果我們想賦權一群人、集體的人,我們必須深入了解這些層層疊疊的技術,并作出不同的決定。
我也是被技術賦權的個體,并從中獲益。而我確實認為,對個體的過分強調令我們錯過了某些東西。但是,如果我們完全走向反面,令技術只能賦權于集體而犧牲個人,我會報以同樣的不滿。坦白講,我并不適合一個凡是只講“集體”的世界,我不是好的團隊合作者,我作為個體比待在團體中更好。我們所在的世界創造了我,盡管它也令我看到了它深刻的局限。
問:你在發布會上也提到,新自由主義成為了當代科技發展主導的意識形態,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和“解放”?
答:我認為新自由主義非常危險的地方在于,它確實能夠解放人。它非常善于運用個人賦權的話語,讓我們感覺到自己的能動性,感覺自己能自主地做出選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擔起選擇的責任。在我們身處的如此復雜的世界,這會讓人精疲力盡,我們需要應對這種“選擇的負擔”。我們被要求在不同的醫療保險、不同的教育之間做出選擇,我們還被要求理解教育不僅僅是教育,而是一項對我們未來職場表現的“投資”。如果我們想將自己在經濟中的表現“最優化”,令我們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我們就不得不早早地做好這些長期決定。我不認為這是對我們心力的最好利用。
我不是在為刻意限制選擇的行為辯解,但我希望我們不用總是被期待成為精明的個體,在超越個人理解能力的復雜場域里行事;我希望作為普通的男男女女,我們不用被迫去理解復雜決策中的因果關系。從根本上來說,我對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感到不舒服,那是一個讓人疲倦、沮喪、情緒困難的世界,一個并不吸引人的世界,盡管那也還不是最壞的世界。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