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提出“打孔家店”,到隨后“打倒孔家店”成為流行口號,對現代中國思想、文化乃至學術等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打孔家店”與“打倒孔家店”盡管只有一字之差,其中卻有本質的差別。本文試圖對這兩個口號的源流做一考辨,并對其中的價值取向和思想理路進行梳理。
一
1921年6月16日,胡適給吳虞即將出版的文集作序,第一次提出了“打孔家店”。原文是:“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在這篇兩千字的序文中,胡適對吳虞給予高度評價,說“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同時,胡適提出了兩個重要概念:一個是“孔家店”,有老店和冒牌兩種,給儒家思想冠以字號稱謂,富有調侃意味;一個是“打”,拿下招牌,即對儒家思想的基本態度。關于“孔家店”的來由,錢玄同指出:“孔家店本是由‘吾家博士’看《水滸》高興時,擅替二先生開的,XY先生(錢玄同筆名——引者注)便以為著重點,論得‘成篇累牘’,以思想比貨物,似乎不怎么恰當。”
對于胡適提出的“打孔家店”主張,錢玄同予以積極回應。他說:“孔家店真是千該打,萬該打的東西;因為它是中國昏亂思想的大本營。它若不被打倒,則中國人的思想永無清明之一日;穆姑娘(Moral)無法來給我們治內,賽先生(Science)無法來給我們興學理財,臺先生(Democracy)無法來給我們經國惠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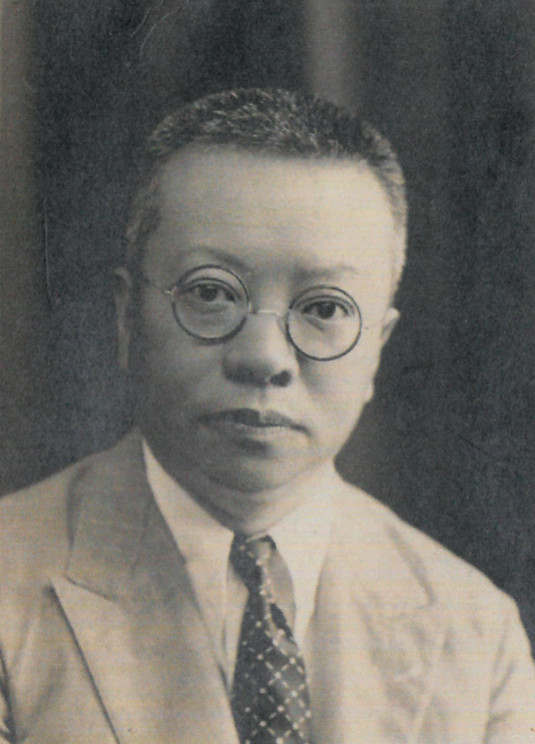
△ 錢玄同(1887—1939年)
錢玄同認為,在打孔家店之前,必須搞清楚兩個問題:“一,孔家店有‘老店’和‘冒牌’之分。這兩種都應該打;而冒牌的尤其應該大打特打,打得它一敗涂地,片甲不留!二,打手卻很有問題。簡單地說,便是思想行為至少要比冒牌的孔家店里的人們高明一些的才配得做打手。若與他們相等的便不配了。至于孔家店里的老伙計,只配做被打者,絕不配來做打手!”
為什么要打老牌孔家店,理由是:“這位孔老板,卻是紀元前六世紀到前五世紀的人,所以他的寶號中的貨物,無論在當時是否精致、堅固、美麗、適用,到了現在,早已蟲蛀、鼠傷、發霉、脫簽了,而且那種野蠻笨拙的古老式樣,也斷不能適用于現代,這是可以斷定的。所以把它調查明白了,拿它來摔破,搗爛,好叫大家不能再去用它,這是極應該的。”也就是說,孔家店無論式樣和內容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根本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至于冒牌的孔家店里的貨物,真是光怪陸離,什么都有。例如古文、駢文、八股、試帖、扶乩、求仙、狎優、狎娼……三天三夜也數說不盡”,因此必須狠打。
錢玄同不但反對儒家思想,而且反對所有中國傳統思想。他說:“此外則孔家店(無論老店或冒牌)中的思想固然是昏亂的思想,就是什么李家店、莊家店、韓家店、墨家店、陳家店、許家店中的思想,也與孔家店的同樣是昏亂思想,或且過之。”
對于胡適稱贊吳虞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錢玄同給予質疑。他有針對性地指出:“那部什么《文錄》中‘打孔家店’的話,汗漫支離,極無條理;若與胡適、陳獨秀、吳敬恒諸人‘打孔家店’的議論相較,大有天淵之別。”錢玄同認為,吳虞并不是什么打孔家店的英雄,只不過是孔家店的老伙計,“至于孔家店里的老伙計,只配做被打者,絕不配來做打手!”像胡適、顧頡剛那班整理國故者,才配做打孔家店的打手。
錢玄同說:“近來有些人如胡適、顧頡剛之流,他們都在那兒著手調查該店的貨物。調查的結果能否完全發見真相,固然不能預測;但我認他們可以做打真正老牌的孔家店的打手,因為他們自己的思想是很清楚的,他們調查貨物的方法是很精密的。”周作人曾說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中間,主張反孔最為激進,而且到后來沒有變更的,莫過于他了”。這種態度和主張,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矯枉必須過正的典型表現。
胡適對“打孔家店”的表態,由于他特有的地位、立場和影響,傳播甚廣,同時也帶來非議。胡適在其一生的不同階段,對此都有解釋和辯護。1929年,胡適在批評國民黨打壓思想自由時指出:“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1932年,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中回應道:“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滿清之倒,豈辛亥一役為之?辛亥之役乃摧枯拉朽之業。我們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
1948年,胡適回答后學提問,再次談到“孔家店”。他說:“關于‘孔家店’,我向來不主張輕視或武斷地抹殺。你看見我的《說儒》篇嗎?那是很重視孔子的歷史地位的。但那是馮友蘭先生們不會了解的。”胡適晚年談到這樁公案時,特別聲明,“并不要打倒孔家店”。他說:“有許多人認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我對十二世紀‘新儒學’(Neo-Confucianism)(‘理學’)的開山宗師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胡適這一系列表白,足以說明胡適所謂的“打孔家店”并不是徹底摧毀和全盤否定儒家文化。
二
著名啟蒙大師梁啟超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激烈反傳統,一方面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給予批評。他說:“近來有許多新奇偏激的議論,在社會上漸漸有了勢力。所以一般人對于儒家哲學,異常懷疑。青年腦筋中,充滿了一種反常的思想。如所謂‘專打孔家店’,‘線裝書應當拋在茅坑里三千年’等等。此種議論,原來可比得一種劇烈性的藥品。無論怎樣好的學說,經過若干時代以后,總會變質,攙雜許多凝滯腐敗的成分在里頭。譬諸人身血管變成硬化,漸漸與健康有妨礙。因此,須有些大黃芒硝一類瞑眩之藥瀉他一瀉。所以那些奇論,我也承認它們有相當的功用。但要知道,藥到底是藥,不能拿來當飯吃。若因為這種議論新奇可喜,便根本把儒家道術的價值抹殺,那便不是求真求善的態度了。”
梁啟超還從歷史、時代、儒學屬性、儒學價值、儒學與科學五個方面做了簡要分析,提醒時人應該客觀審視儒學,不要簡單否定,一概打倒。他說:“誠然儒家以外,還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學,不算中國文化全體;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為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如果要專打孔家店,要把線裝書拋在茅坑里三千年,除非認過去現在的中國人完全沒有受過文化的洗禮。這話我們肯甘心嗎?”
梁啟超的得意門生張君勱對“打倒孔家店”給予批評。他說:“五四運動以后之‘打倒孔家店’、‘打倒舊禮教’等口號,是消滅自己的志氣而長他人威風的做法。須知新舊文化之并存,猶之佛教輸入而并不妨礙孔門人倫之說。歐洲有了耶教,何嘗能阻止科學技術民主政治之日興月盛?”
馮友蘭從捍衛儒家思想的角度,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打孔家店”的主張做了批評。他指出:“民初人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底禮教’,對于孝特別攻擊。有人將‘萬惡淫為首’改為萬惡孝為首。他們以為,孔家店的人,大概都是特別愚昧底。他們不知道,人是社會的分子,而只將人作為家的分子。孔家店的人又大概都是特別殘酷,不講人道底。他們隨意定出了許多規矩,叫人照行,以至許多人為這些規矩犧牲。此即所謂‘吃人底禮教’。當成一種社會現象看,民初人這種見解,是中國社會轉變在某一階段內,所應有底現象。但若當成一種思想看,民初人此種見解,是極錯誤底。”“民初人自以為是了不得底聰明,但他們的自以為了不得底聰明,實在是他們的了不得底愚昧。”馮友蘭認為,民初人的錯誤是:“他們不知,人若只有某種生產工具,人只能用某種生產方法;用某種生產方法,只能有某種社會制度;有某種社會制度,只能有某種道德。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中,孝當然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
以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為主體的“學衡派”,對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打孔家店”主張給予了激烈回應。他們認為,這種對儒學和孔子的態度,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肆意攻擊和誹謗。學衡派主將吳宓專門撰寫文章,回擊新文化派,闡明孔子的價值和孔教的精義。他說:“自新潮澎湃,孔子乃為人攻擊之目標,學者以專打孔家店為號召,侮之曰孔老二,用其輕薄尖刻之筆,備致底譏。盲從之少年,習焉不察,遂共以孔子為迂腐陳舊之偶像,禮教流毒之罪人,以謾孔為當然,視尊圣如誑病。”
學衡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柳詒徵也有回應,他認為無論是打倒孔家店還是以孔教號召天下,都是對孔子和儒學的曲解。他說:“近年有所謂專打孔家店呵斥孔老頭子者,固無損于孔子毫末,實則自曝其陋劣。然若康有為陳某某等,以孔教號召天下,其庸妄亦與反對孔子者等。真知孔子之學者,必不以最淺陋之宗教方式,欺己欺人,且以誣蔑孔子也。”柳詒徵認為,孔子是中國文化中心的地位決不能動搖。他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又進一步提升了孔子的地位。
因此,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形成了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打孔家店與以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為中心的護孔家店的南北對峙。對此,南高學人津津樂道。比如,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郭斌龢說:“當舉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國舊文化之日,南高諸人獨奮起伸吭與之辨難。曰中國文化決不可打倒,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決不可打倒。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南高師生,足以當之。”后來有人在此說的基礎上繼續發揮說:“猶憶民國八九年間,當舉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國舊文化之日,本校學衡諸撰者,獨奮起與之辯難曰,中國舊文化決不可打倒。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決不能打倒。殆其后新說演變而為更荒謬之主張,其不忍數千年之文化,聽其淪喪者。又一反其所為,乃大聲疾呼:宏揚固有道德,建立本位文化,排斥浪漫思想者。”

△郭斌龢(1900—1987年)
1931年11月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郭斌龢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新孔學運動》,認為孔學是中國國魂,積極倡導孔學立國,挽救民族文化危機。其具體內容是:第一,發揚光大孔學中具有永久與普遍性的部分,如忠恕之道、個人節操的養成等等。第二,應保存有道德意志的天之觀念。第三,應積極實行知、仁、勇三達德,提倡儒俠合一、文人帶兵的風氣。第四,應使孔學想象化、具體化,使得產生新孔學的戲劇、圖畫、音樂、雕刻等藝術。郭斌龢的主張,得到其南高同仁的響應。但總體而言,其產生的影響并不是很大,主要局限在固有的圈子。
賀麟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孔的觀點。他說:“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一個大轉機。表面上,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遠超過前一時期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對儒家思想的提倡。”
賀麟進而指出:“新文化運動的最大貢獻在于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及束縛個性的傳統腐化部分。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
賀麟對胡適的批評儒學也予以積極評價。他說:“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號召的胡適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戰略,據他英文本《先秦名學史》的宣言,約有兩要點:第一,解除傳統道德的束縛;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諸子之學。但推翻傳統的舊道德,實為建設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預備工夫,提倡諸子哲學,正是改造儒家哲學的先驅。用諸子來發揮孔孟,發揮孔孟以吸取諸子的長處,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經不起諸子百家的攻擊、競爭、比賽,那也就不成其為儒家思想了。愈反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賀麟認為,代表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遭到系統批評是在新文化運動中,但儒學自身的危機卻很早就出現了。他說:“中國近百年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文化上有失調整,就不能應付新的文化局勢。中國近代政治軍事上的國恥,也許可以說是起于鴉片戰爭,中國學術文化上的國恥,卻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國青年們猛烈地反對,雖說是起于新文化運動,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無生氣,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需要的無能,卻早腐蝕在五四運動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權,喪失了新生命,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
三
1936年9月,時任中國共產黨北方局宣傳部長的陳伯達在《讀書生活》第4卷第9期上發表了《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己批判和關于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一文,率先倡議開展新啟蒙運動。隨后,艾思奇、張申府、何干之、胡繩等人起來響應,形成了一場新啟蒙運動,主題是繼承五四,超越五四。主要是提倡民主與科學,完成五四的未竟之業。“基本綱領,就是:繼續并擴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啟蒙運動,反對異民族的奴役,反對禮教,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喚起廣大人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
其中涉及對孔子及儒學的態度,“打倒孔家店”作為五四運動的精神被人為強化。陳伯達對此發表了一系列言論,反復強調。他說:“五四時代一批思想界的人物:如‘打倒孔家店’,‘反對玄學鬼’,在考古學上推翻傳統歷史的這一切老戰士,我們都應該重新考慮和他們進行合作。”又說:“接受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號召,繼續對于中國舊傳統思想,舊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統的批判。”陳伯達指出:“以《新青年》為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第一次以群眾的姿態,向‘中古的’傳統思想和外來的文化,公開宣告了反叛。‘打倒孔家店’,‘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提倡白話文’——這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口號。”
在這里,陳伯達把“打倒孔家店”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精神,并將其列在首位,絕不是信筆一揮,而是有深刻含義的。陳伯達說:“我們的新啟蒙運動,是當前文化上的救亡運動,也即是繼續戊戌以來啟蒙運動的事業。我們的新啟蒙運動是五四以來更廣闊,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五四時代的口號,如‘打倒孔家店’,‘德賽二先生’的口號,仍為我們的新啟蒙運動所接受,而同時需要新酒裝進舊瓶,特別是要多面地具體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運動相聯結。這些口號的接受,也就是我們和五四時代的人物合作的要點。”
陳伯達在回應學者質疑時說:“在我所有的文章中,關于這點(指文化運動的派別——引者注),我實在采取了審慎的態度。比如關于孔子的問題,我算是強調地指出了孔教的奴役作用,但還是留了與崇信孔子者合作的余地。艾思奇先生在一些文章中關于‘孔家店’的態度,我認為是完全正確的。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在目前應由反獨斷反禮教反復古的口號表現出來。”
新啟蒙運動的另一個代表人物張申府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口號予以質疑,并響亮提出了他對孔子和儒學的主張:“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張申府說:“今日的新啟蒙運動,顯然是對歷來的一些啟蒙運動而言。對于以前的一些啟蒙運動,也顯然有所不同。比如,就拿五四時代的啟蒙運動來看,那時有兩個頗似新穎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德賽二先生’。我認為這兩個口號不但不夠,亦且不妥。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許孔子已經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惡流卻仍然保留著,漫延著。至于科學與民主,本都是客觀的東西,而那時的文人濫調,卻把它人格化起來,稱什么先生,真無當于道理。至少就我個人而論,我以為對這兩口號至少都應下一轉語。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

△ 張申府(1893—1986年)
張申府強調指出:“五四時代的啟蒙運動,實在不夠深入,不夠廣泛,不夠批判。在深入上,在廣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啟蒙運動都需要多進幾步。”1940年到1942年,張申府又對他的觀點做了重申:“‘線裝書扔在茅廁里’。羊皮典束之高閣上。人人師心憑臆,各簧鼓其所好。天下從此,四無猖狂。”“狂妄者說,‘打倒孔家店。’孔家本無店,要打倒那里?我嘗救正說,‘救出孔夫子。’仲尼本自在,救也用不著。”這時張申府的思想又變化了,認為孔子根本沒有必要救,言下之意是孔子思想本身不朽。
四
通過上述對歷史文獻的初步梳理,我們不難發現,“打倒孔家店”確實是從“打孔家店”衍化而來,而且是以訛傳訛。比如,陳伯達1937年發表的《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文中,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將胡適評價吳虞的話語加以錯誤引用,將“打孔家店”演繹為“打倒孔家店”。陳伯達說:“吳虞——這位曾被胡適稱為‘四川省雙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卻是最無忌憚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歷史污穢。”
另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何干之也同樣錯誤引用。他說:“吳虞,胡適之先生叫他做‘四川省雙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的文筆很質樸,思想很謹嚴,意志很堅強。他以淵博的知識,嚴肅的理知,平淡的筆法,來描出儒教的虛偽,揭破舊思想的遺毒。”兩個人在其引用中,都明顯引錯了兩個地方:一是將“只手”錯引為“雙手”;一是將“打孔家店”錯引為“打倒孔家店”。范文瀾也有類似提法:“五四運動‘名將’之一的吳虞先生,曾被稱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對此,當代學者王東有一段評論。他說:“細致分析起來,從胡適的原來提法,到陳伯達的后來概括,至少發生了五點微妙變化:一是從一句幽默戲言,變成了理論口號;二是從胡適對吳虞的介紹,變成了胡適本人的主張;三是從五四后期的個別提法,變成五四時代的主要口號;四是從胡適個人的一個說法,變成了整個五四運動的理論綱領;五是從‘打孔家店’,變成了‘打倒孔家店’”。陳伯達等人將“打孔家店”衍化為“打倒孔家店”,目的是其對中國傳統儒學進行系統而徹底地批判有合法思想來源,某種意義上帶有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文化價值認同。如果僅僅把這一變化歸結于陳伯達的個人思想或個體認知,既不客觀,而且顯失公平。
另外,王東認為:“‘只手打孔家店’這個提法,經過30、40年代陳伯達等人加工改造,變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開始被曲解夸大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綱領性口號。”這個論斷也只說明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其實,按照嚴格的時間概念,就目前所看到的資料,最早提出或者說把“打孔家店”衍化為“打倒孔家店”的,并不是陳伯達,而是郭斌龢。他在1935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打倒孔家店”這一說法,而且予以隨意夸大。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郭斌龢提出“打倒孔家店”概念,并不是他及南高學派的文化主張,而是將其發明權冠之于五四新文化派。以北京大學為核心的新文化派是主張“打孔家店”的,而以東南大學為核心的學衡派是注重護孔家店的,兩派旗幟鮮明,明顯對立。在當時那個特定時代,“打倒孔家店”不得人心。南高學人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視之為“打倒孔家店”的重鎮,目的顯然是樹立一個反擊的靶子,借以孤立或矮化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提升他們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響。
對于孔家店是“打”還是“打倒”,長期以來大多數學者沒有注意到二者的差別和異同,混用者居多,而且不少人認為兩個意思完全相同,沒有差別。但是,也有一些學者發現并注意到這一問題。
比如,王東教授從文字字義上做了比較分析,指出:“‘打’在這里主要是進攻、挑戰之意,而‘打倒’則是徹底推翻、完全否定之意,二者之間雖是一字之差,卻有質與量上的微妙差異,程度上大為不同,不可混淆。”宋仲福、趙吉惠教授從內容上做了分析,指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胡適文‘打孔家店’一詞衍訛而來。但是,一字之差,卻反映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孔精神的兩種不同的理解和概括。‘打孔家店’即是批評儒學;‘打倒孔家店’卻是全面否定儒學。……‘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身的產物,而是由于歷史的誤會,后人給新文化運動的附加物。而這個附加物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這個運動的主要精神,還大大歪曲了它的精神”。耿云志指出:“人們往往抓住一兩句口號,一兩句概括的話,就望文生義,把胡適說的‘打孔家店’,說成是‘打倒孔家店’,更進一步把‘打倒孔家店’說成是‘打倒孔子’、‘打倒孔學’。其實‘打孔家店’與‘打倒孔家店’,意味已有不同,而‘打倒孔家店’與‘打倒孔子’、‘打倒孔學’就更不能同日而語了。”這種解讀,已經明晰了二者本質的不同。
另外,還有一個“孔老二”的問題。所謂“孔老二”,即對孔子的貶稱。馮友蘭說:“新文化運動對于孔丘和儒家思想完全否定,稱孔丘為‘孔老二’,儒家為‘孔家店’。當時流行的口號是‘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早在1927年,吳宓已經提到,新文化運動稱孔子為“孔老二”。對此,吳宓深表不滿,他認為,時人稱孔子為“孔老二”,有侮辱不敬之意,當然也屬大逆不道。
馮友蘭所說與事實不符。就我所看到的材料,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多數學人對孔子還是尊敬的,基本都稱其為孔子,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即使反傳統特別激烈的錢玄同,也沒有在稱呼上貶低孔子本人。對孔子名稱不大尊敬的,只有吳稚暉、魯迅、吳虞等少數人,如吳稚暉稱孔子為“死鬼”、“枯骨”,但也是與先秦諸子并列的,并不特意針對孔子。魯迅、吳虞稱孔子為“孔二先生”,暗含譏諷,卻也基本符合事實,因為孔子在家排行老二,老大名孟皮,字伯尼。至于什么“孔老二”甚至“打倒孔老二”的提法,純粹是后人強加的,和歷史事實相去甚遠。
“打孔家店”衍化為“打倒孔家店”,基本上反映了中國近代學人對中國文化的三種態度: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對中國文化中的劣根性及其與現代民主政治和社會生活不適應的部分做深入批判,同時繼承其合理精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者認為其批評中國文化力度不夠,要對中國維護傳統做徹底清算,甚至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認為其批評孔子及儒學是對中國文化的大不敬,將其視為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叛逆。
第一種態度是比較平和的,主張在批評的基礎上對中國文化做一系統整理,同時合理吸收和借鑒外來文化,試圖使中外文化結合和相互容納,進而創建新文化;第二種態度是比較激進的,主張全盤否定中國文化,試圖以外來文化取而代之,幾乎與當時的“全盤西化”不謀而合,表現為偏執與非理性;第三種態度以中國文化的衛道者自居,在新文化成為時代思潮時,繼續固守和堅持固有價值和思想理念,多少有點不識時務。
總之情況比較復雜。但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對孔家店是“打”還是“打倒”,明顯反映了中國近代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思想理路,同時也導致了迥然不同的后果與結局。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