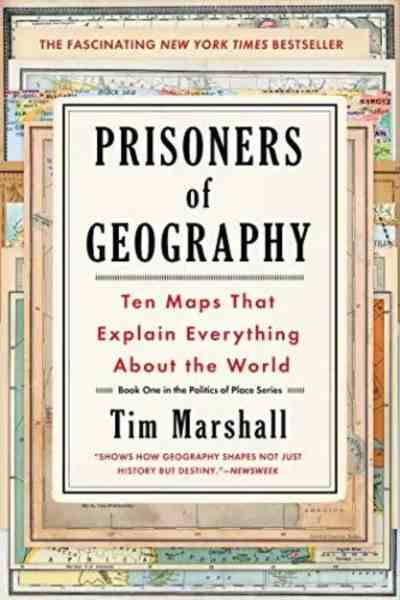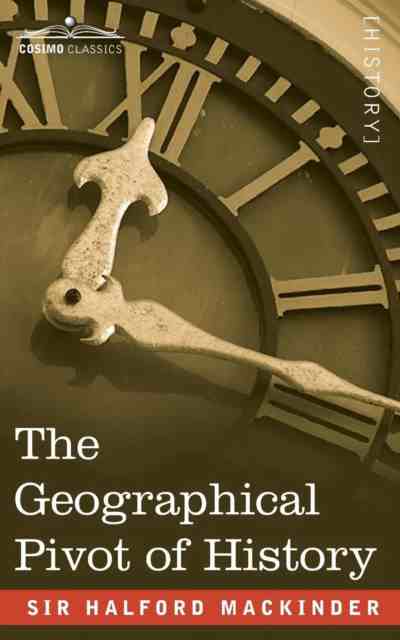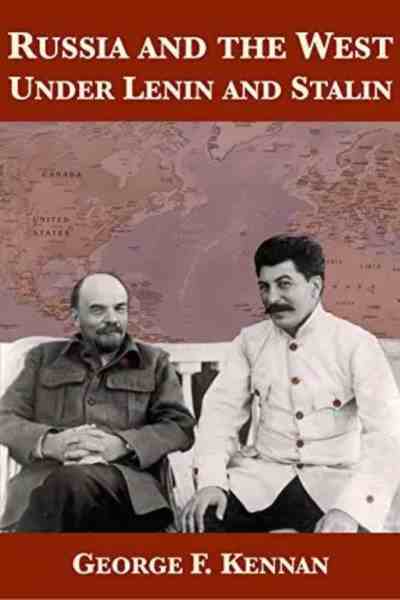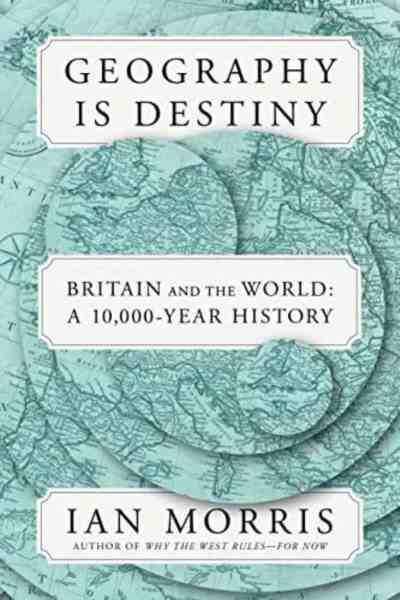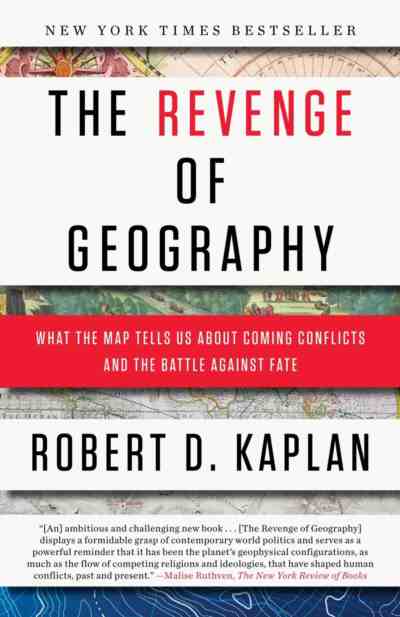文 | 丹尼爾·因莫瓦爾
譯 | 董璐瑤
俄烏沖突充滿了許多意外,而最大的意外是它竟然真實地發(fā)生了。去年,俄羅斯還處于和平狀態(tài),裹挾在復雜的全球經(jīng)濟中。俄羅斯是否真的僅僅為了擴大其已經(jīng)十分廣袤的領(lǐng)土,而不惜切斷貿(mào)易關(guān)系甚至并威脅發(fā)動核戰(zhàn)爭?盡管收到了包括普京在內(nèi)許多人的警告,但這次沖突仍然令人感到震驚。
蒂姆·馬歇爾 《地理的囚徒》
但記者蒂姆·馬歇爾(Tim Marshall)卻并不意外。在其2015年的大作《地理的囚徒》(Prisoners of Geography)的第一頁,馬歇爾邀請讀者思考俄羅斯的地形。俄羅斯被一圈山脈與冰雪環(huán)繞著,與中國的邊界受到山脈保護,高加索山脈阻隔了它與伊朗和土耳其。在俄羅斯和西歐之間有巴爾干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這些山脈幾乎構(gòu)成了另一道墻壁。在這些山脈以北,平坦走廊般的歐洲平原通過烏克蘭和波蘭連接起俄羅斯和其武裝良好的西鄰。在這條走廊上,你可以騎著自行車從巴黎到莫斯科。
你當然也可以開坦克。馬歇爾指出,俄羅斯自然條件上的差距使其屢屢受到攻擊。“普京沒有選擇,”馬歇爾總結(jié)道,“他至少必須嘗試控制西部的平原地區(qū)。”普京恰是如此行事,對無法通過更和平的手段加以控制的烏克蘭發(fā)動行動,馬歇爾對此感到遺憾,但又覺不足為奇。他寫道,地圖“禁錮”了領(lǐng)袖們,“留給他們的選擇和回旋余地比人們想象的要少。”
馬歇爾的思維模式有一個正式名稱:地緣政治學。雖然該詞常被寬泛地用來指代“國際關(guān)系”,但更準確地來說,它是指山脈、橋梁、水位等地理特征支配世界事務的觀點。地緣政治學家認為,思想、法律和文化雖然有趣,但要真正理解政治,人們必須認真鉆研地圖。這時,世界就會展現(xiàn)出一場零和競賽的形態(tài),每個鄰國都是潛在對手,而成功與否則取決于對領(lǐng)土的控制,就像棋盤游戲《風險》一樣。地緣政治學對人類動機采取憤世嫉俗的看法,類似于馬克思主義,只是用地形代替了階級斗爭作為歷史的動力。
地緣政治學與馬克思主義相似的另一點在于,許多人曾預測它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冷戰(zhàn)的結(jié)束而消亡。市場的擴張和新興技術(shù)的爆發(fā)式增長有望淘汰掉地理學。當海洋中充斥著集裝箱船只與反射自衛(wèi)星的信息時,誰還在乎控制馬六甲海峽或敖德薩港呢?2005年,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宣稱:“世界是平的。”這是對全球化的恰當比喻,因為貨物、思想與人類能夠順利地跨越國界。
然而,今天的世界似乎不再那么平坦。隨著供應鏈的斷裂和全球貿(mào)易的萎縮,地球上的地形似乎變得更加崎嶇不平。由唐納德·特朗普和奈杰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等人引導的對全球化的敵意,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呈現(xiàn)上升趨勢,而疫情又使其進一步加劇。冷戰(zhàn)結(jié)束時邊境墻的數(shù)量約為十座,而經(jīng)過過去十年的建墻高峰,現(xiàn)已達七十四座,且還在不斷攀升之中。如政治學家E?lisabeth Vallet所言,冷戰(zhàn)后對全球化的希望是一種“錯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是“世界的再領(lǐng)土化(reterritorialisation)”。
面對充滿敵意的新環(huán)境,領(lǐng)導人們抽走了書架上過時的戰(zhàn)略指南。2017年,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警告道:“經(jīng)歷了我們所謂的后冷戰(zhàn)時期的歷史假期之后,地緣政治不僅回歸了,而且是報復性地歸來了。”這種觀點公開地指導著俄羅斯的思維模式,普京在解釋其對烏克蘭采取行動時引用了“地緣政治現(xiàn)實”一詞。在其他地方,隨著對以貿(mào)易為基礎(chǔ)的開放的國際體系的信心減弱,馬歇爾、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喬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和彼得·澤漢(Peter Zeihan)等地圖解讀專家的著作正在向暢銷書排行榜挺進。
聽著地圖大師們的專業(yè)判斷,人們會想,從戰(zhàn)略取決于大草原與山地障礙的十三世紀至今,世界是否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地緣政治思維是不加掩飾的嚴峻,它對和平、正義和權(quán)利的希望持懷疑態(tài)度。然而,問題不在于它是否暗淡,而在于它是否正確。過去幾十年發(fā)生了重大的技術(shù)、知識與制度變革,但是我們是否仍然像馬歇爾所說的那樣,是“地理的囚徒”?
劉易斯·達特內(nèi)爾 《起源》
從長遠來看,我們是自身所處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其影響程度幾乎高到了令人尷尬的地步。環(huán)境允許人類便繁榮,環(huán)境不允許人類則滅亡。劉易斯·達特內(nèi)爾(Lewis Dartnell)在他那本精彩的《起源》(Origins)中寫道:“如果觀察一張構(gòu)造板塊邊界相互摩擦的地圖,將世界主要古代文明的地理位置疊加起來,就會發(fā)現(xiàn)一種驚人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這種關(guān)聯(lián)并非偶然。板塊碰撞產(chǎn)生了山脈和大河,大河將其沉積物帶到低地,使土壤變得肥沃。古希臘、埃及、波斯、亞述、印度河流域、中美洲和羅馬都靠近板塊邊緣。位于三個板塊的交匯處的新月地帶土地肥沃,從埃及延伸到伊朗豐富的農(nóng)業(yè)區(qū),最早出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文字和車輪。
正如美國南部的投票模式所顯示的一般,地理影響可以令人印象深刻地持續(xù)下去。美國南部深處的共和黨人很多,但有一條民主黨縣的弧線從其中穿過。科學家史蒂芬·杜赫(Steven Dutch)寫道,這一不同的線條形成了一個“對地質(zhì)學家來說一眼就能辨識的”形狀。它與數(shù)千萬年前的沉積物露出地面的巖層相吻合,這些沉積物在炎熱的白堊紀時期沉積,當時美國的大部分地區(qū)仍處于水面之下。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沉積物被壓縮成頁巖,而更久之后海水退去,它們被侵蝕暴露出來。杜赫解釋說,在19世紀,種植者們意識到這一因豐沃的黑土而被稱為“黑帶(Black Belt)”的地區(qū)是棉花的理想產(chǎn)地。為了采摘棉花,種植者帶來了奴隸,這些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此處,并經(jīng)常反對保守的政治家。達特內(nèi)爾指出,恰好處于白堊紀帶“要害處(smack in the middle)”的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也是民權(quán)運動的中心,小馬丁·路德·金曾在這里布道,羅莎·帕克斯也在這里引發(fā)了公交車抵制運動。
羅莎·帕克斯與馬丁·路德·金
當然,地緣政治家們更關(guān)心國際戰(zhàn)爭而不是地方選舉。在這一點上,其認知可以追溯到英國戰(zhàn)略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他基本上創(chuàng)立了地緣政治學。在其1904年的論文《歷史的地理樞紐》中,麥金德凝視著世界的浮雕地圖,認為歷史可以被看作歐亞大陸平原的游牧民族和沿海地區(qū)的航海民族之間長達數(shù)百年的斗爭。英國等國家曾因海洋霸權(quán)而繁榮發(fā)達,但現(xiàn)在所有可行的殖民地都有所屬,殖民之路已經(jīng)關(guān)閉,未來的擴張將涉及陸地沖突。麥金德認為,歐亞大陸“心臟地帶(heart-land)”的廣闊平原將成為世界戰(zhàn)爭的中心。
哈爾福德·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
麥金德并不完全正確,但其預測整體上卻足夠可取,如東歐沖突、英國海上力量的減弱、陸地大國德國與俄國的崛起。雖具體細節(jié)有所偏差,但是麥金德對帝國主義者耗盡殖民地并相互爭斗的設(shè)想是有預見性的。他預見到當這一天來臨時,歐亞大陸內(nèi)部地區(qū)將成為其目標。他后來寫道,心臟地帶“提供了最終統(tǒng)治世界的所有先決條件。”“誰統(tǒng)治了心臟地帶,誰就能指揮世界島(World-Island,指歐亞非大陸);誰統(tǒng)治了世界島,誰就能指揮世界。”
麥金德所言為一則警告,但認為麥金德?lián)碛?ldquo;最偉大的地理世界觀”的德國陸軍將軍卡爾·豪斯霍費爾卻將這視為建議。豪斯霍費爾將麥金德的見解納入了新興的地緣政治學領(lǐng)域,并在上世紀20年代將這一想法分享給阿道夫·希特勒和魯?shù)婪?middot;赫斯。希特勒總結(jié)說:“德國人民被囚禁在毫無可能性的領(lǐng)土范圍內(nèi)。”為了生存,他們必須“成為一個世界強國”,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轉(zhuǎn)向東方,也即麥金德所稱的心臟地帶。
阿道夫·希特勒堅信德國的命運在于東方,這與史蒂文·杜赫觀察到的白堊紀巖石預測選票相去甚遠。然而,這兩者的共通之處都是我們的土地決定了我們的思想的理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當軍隊為爭奪具有戰(zhàn)略價值的領(lǐng)土而發(fā)生沖突,并撕裂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qū)時,這一點似乎很難否認。經(jīng)歷過那場戰(zhàn)爭的麥金德認為沒有理由相信地理學的“頑固事實”會讓步。
哈福德·麥金德堅持認為地形圖仍然重要,但并非所有人都持同樣觀點。整個二十世紀,理想主義者都在尋找一種方法,使國際關(guān)系不至于像英國經(jīng)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說的那樣,是一場“永久的爭奪”。對于凱恩斯及其追隨者來說,貿(mào)易可能會實現(xiàn)這一目標。如果各國能夠依靠開放的商業(yè),就不必再為保障資源而奪取領(lǐng)土。對于其他理想主義者來說,航空時代的新興技術(shù)是關(guān)鍵,他們希望隨著所有地方通過天空共通相連,各國將停止對地理戰(zhàn)略位置的紛爭。
然而這只是希望,而非現(xiàn)實。冷戰(zhàn)將地球劃分為貿(mào)易集團和軍事聯(lián)盟,使各國領(lǐng)導人緊盯著地圖不放。1957年法國的棋盤游戲《征服世界》(La Conque?te du Monde)在美國帕克兄弟公司旗下以《風險》(Risk)之名廣泛銷售,促使孩子們也學會了閱讀地圖。這款游戲定調(diào)于19世紀,有騎兵和陳舊的火炮;但鑒于超級大國仍在瓜分世界,它也有著令人不適的相關(guān)性。
雖然地緣政治思想因與納粹有關(guān)聯(lián)而被淡化,但還是在冷戰(zhàn)中留下了痕跡。美國的重要戰(zhàn)略家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淡化了沖突中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凱南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片“無花果葉”般的象征性掩飾,蘇聯(lián)行為的真正原因源自“蘇聯(lián)人傳統(tǒng)本能的不安全感”,這一不安全感產(chǎn)生于幾個世紀以來“試圖在激烈的游牧民族附近的廣闊裸露平原上生活”。對于這個與麥金德理論有關(guān)的問題,凱南提出了一個與麥金德理論有關(guān)的解決方案:“遏制”。遏制并非要消滅共產(chǎn)主義,而是要對其施加限制。這場運動最終需要美國在世界各地進行干預,包括派遣270萬名軍人參加越南戰(zhàn)爭。對許多服役士兵來說,那場不成功的戰(zhàn)爭是一個“泥潭”。直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地理環(huán)境似乎才最終失去了控制力。
喬治·F·凱南 《列寧與斯大林下的俄羅斯與西方》
冷戰(zhàn)在經(jīng)濟上分裂了世界,其終結(jié)導致貿(mào)易壁壘轟然倒塌。90年代出現(xiàn)了貿(mào)易協(xié)定和機構(gòu)建設(shè)的熱潮,包括歐盟、北美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Nafta)、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以及高高在上的世界貿(mào)易組織。1988年至2008年期間,區(qū)域貿(mào)易協(xié)定的數(shù)量增加了四倍多,并通過更徹底的國家協(xié)調(diào)得到不斷深化。在此期間,貿(mào)易增長了兩倍,從不到全球GDP的六分之一上升到四分之一以上。
越是能通過貿(mào)易獲得重要資源的國家,就越?jīng)]有理由奪取土地。托馬斯·弗里德曼等樂觀主義者認為,那些與經(jīng)濟網(wǎng)絡(luò)緊密相連的國家會放棄發(fā)動戰(zhàn)爭,因為它們害怕喪失進入嗡鳴作響的經(jīng)濟網(wǎng)絡(luò)的機會。1996年,弗里德曼輕描淡寫地將此表述為預防沖突的“金拱門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沒有兩個擁有麥當勞的國家會彼此開戰(zhàn)。而且他也沒有更進一步。盡管擁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發(fā)生過幾次沖突,但自冷戰(zhàn)以來,個人在國家間戰(zhàn)爭中死亡的機率已經(jīng)大大降低。
在貿(mào)易減少戰(zhàn)爭可能性的同時,軍事技術(shù)改變了戰(zhàn)爭的形態(tài)。就在柏林墻倒塌的幾個月后,薩達姆·侯賽因領(lǐng)導了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這是一次老派的地緣政治行動。伊拉克當時已掌握了世界上第四大軍隊,通過奪取科威特,它將控制世界上五分之二的石油儲備。更重要的是,其強大的地面部隊被一大片無跡可尋的沙漠所遮擋,幾乎無法穿越。這是麥金德會欣賞的戰(zhàn)略。
但九十年代不再是麥金德的時代了。以美國為首的聯(lián)盟從路易斯安那州、英格蘭、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迪戈加西亞島派出轟炸機,在伊拉克上空投下有效載荷,在數(shù)小時內(nèi)使伊拉克大部分基礎(chǔ)設(shè)施癱瘓,薩達姆也同樣意識到了時代的更迭。隨后聯(lián)軍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空襲,利用GPS這一新的衛(wèi)星技術(shù),迅速穿越了被伊拉克人視為不可逾越的屏障的沙漠。一百個小時的地面戰(zhàn)斗足以擊敗伊拉克的殘兵敗將,伊拉克的高級軍官們事后指出,甚至沒有必要發(fā)動地面攻擊,因為再有幾個星期的懲罰性空襲,伊拉克就會從科威特撤軍。
九十年代的“戰(zhàn)場”到底是什么?海灣戰(zhàn)爭預示著一場被廣泛討論的“新軍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這場革命承諾以精確的空襲取代裝甲師、重炮和大型步兵。俄羅斯軍事理論家弗拉基米爾·斯利普琴科(Vladimir Slipchenko)指出,戰(zhàn)略家們熟悉的空間概念,如戰(zhàn)場、前線、后方和側(cè)翼正在失去意義。有了衛(wèi)星、飛機、GPS和現(xiàn)在的無人機,“戰(zhàn)斗空間”不再是地球上的褶皺地形,而不過是一張平坦的圖畫紙。
滿天航行的無人機并不意味著世界和平。但新技術(shù)的擁護者至少承諾了更清潔的戰(zhàn)斗,減少平民死亡、俘虜被俘與軍隊的派遣。軍事事務的革命使得以美國及其盟國為主的強國能夠以個人和網(wǎng)絡(luò)為目標,而不需劍指整個國家。這似乎標志著從國際戰(zhàn)爭轉(zhuǎn)向全球警務、從血腥的地緣政治轉(zhuǎn)向時而致命的全球化平穩(wěn)運行。
全球化實際上已經(jīng)取代了地緣政治學嗎? 地緣戰(zhàn)略家羅伯特·卡普蘭承認,“上世紀九十年代,由于空中力量的存在,地圖被縮減為二維。然而,“三維地圖”在“阿富汗的山區(qū)和伊拉克險惡的小巷中”復蘇。1991年的海灣戰(zhàn)爭和2003至2011年的伊拉克戰(zhàn)爭之間的對比很有說服力。這兩場戰(zhàn)爭都由全球超級大國領(lǐng)導著一個反對薩達姆的伊拉克聯(lián)盟。然而,在第一場戰(zhàn)爭中,投入空中力量得以取得迅速勝利;而第二場戰(zhàn)爭就像是美國制造的另一個泥潭。
自九十年代以來一直快速增長的全球出口,在2008年左右趨于平穩(wěn);而如今,“去全球化”在不久的將來是可能的,歐洲一體化也因英國脫歐面臨著巨大挫折。這仿佛在提示我們,當下歐洲也發(fā)生著一場土地戰(zhàn)爭。事實上,這是一場“麥當勞之戰(zhàn)”,這家快餐連鎖店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有數(shù)百家分店。在普京看來,無論俄羅斯從和平貿(mào)易中獲得多少經(jīng)濟利益,烏克蘭的暖水港、自然資源和對俄羅斯脆弱的西部的戰(zhàn)略緩沖區(qū),大概都超過了這些利益。正如卡普蘭所言,這是“地理的報復”。
伊恩·莫里斯 《地理即命運》
隨著“地理的復仇”,地緣政治理論家也開始回歸,他們往往與自稱是“私人全球情報公司”的斯特拉福(Stratfor)戰(zhàn)略預測公司有所關(guān)聯(lián)。被《巴倫周刊》稱為“影子中情局(shadow CIA)”的戰(zhàn)略預測公司以后冷戰(zhàn)理想主義的失敗為基礎(chǔ)。最近許多以地圖詮釋歷史的暢銷書都是在其下出版的。羅伯特·卡普蘭曾一度是其首席地緣政治分析家。《地理即命運》(Geography is Destiny)的作者伊恩·莫里斯曾在該組織的貢獻者委員會任職;地緣政治作家喬治·弗里德曼和彼得·澤漢分別是該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和副主席。不過英國作家蒂姆·馬歇爾從屬于不同網(wǎng)絡(luò),其《地理的囚徒》由一位前軍情六處處長作序。
2014年,通過維基解密上黑客發(fā)布的五封斯特拉福公司的電子郵件,公眾對該公司的工作有了些許認識。事實證明,這家公司并沒有將自己局限在制圖方面。它已經(jīng)進入了戰(zhàn)場,而且似乎與權(quán)力有一種明顯的親密關(guān)系。黑客們透露,斯特拉福公司已經(jīng)代表公司監(jiān)督社會活動家,曾一度提議為美國銀行調(diào)查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該公司的用戶和客戶包括陶氏化學公司、雷神公司、高盛公司、美林公司、貝氏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和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目前還不清楚的是,2020年被另一家情報公司收購的斯特拉福公司,是否只是美國安全機構(gòu)浩瀚海洋中一條中等規(guī)模的游魚。但泄露的電子郵件確實包括直接來自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nèi)塔尼亞胡的情報,內(nèi)容涉及伊朗核計劃、以色列暗殺真主黨領(lǐng)導人的意愿,以及這位總理對奧巴馬總統(tǒng)的不快。
斯特拉福公司出售機密,但其客戶最終依靠的是其預測能力。地緣政治家們并不羞于做出這些預測。事實上,最近他們提供了如此之多的跨領(lǐng)域預測,以至于人們開始懷疑其發(fā)布這些預測時有多大把握。土耳其是否將如喬治·弗里德曼所預測的一般成為歐洲、亞洲和非洲的“支點”?抑或如卡普蘭所想,印度將成為“全球支點國家”?
如果存有經(jīng)得起考驗的記錄,就更容易認真對待地緣政治家們的言論。但我們?nèi)栽诘却龁讨?middot;弗里德曼在1991年寫的“即將到來的對日戰(zhàn)爭”,而對卡普蘭預測的任何評估都必須注意到他對伊拉克戰(zhàn)爭的支持,包括其加入秘密委員會向白宮鼓吹戰(zhàn)爭。值得稱贊的是,卡普蘭已經(jīng)承認了他的錯誤,他寫道,“當我和其他人支持伊拉克戰(zhàn)爭時,我們從未充分或準確地考慮過代價。”
現(xiàn)代麥金德的擁簇者是否充分或準確地考慮了所有相關(guān)因素,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得以驗證,但他們對當下的看法卻是足夠清晰。這主要是一種嘲笑性的保守主義,懷疑太陽下是否有如此多新事。對馬歇爾來說,巴爾干半島的“部落”永遠處于“古老的猜疑”之中,剛果民主共和國“仍然是一個籠罩在戰(zhàn)爭黑暗中的地方”,希臘人和土耳其人自特洛伊戰(zhàn)爭以來一直處于“相互對立”。卡普蘭也持有類似觀點。他寫道,俄羅斯一直是一個“缺乏安全感的、不斷擴張的陸地大國”,其人民在“整個歷史上“對高加索山脈抱有“恐懼和敬畏”。他贊許地引用了一位退休歷史學家的理論,即俄羅斯人在面對寒冷的冬天時,擁有更強的“承受能力”。
羅伯特·卡普蘭《地理的復仇》
學術(shù)地理學家Harm de Blij在評論卡普蘭《地理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一書時,發(fā)現(xiàn)這本書有時“令人備受折磨”,并寫道,學者們會驚訝地看到“長久以來被丟進垃圾箱”的粗暴的環(huán)境決定論竟獲得新生。卡普蘭承認,要從地緣政治角度思考問題,需要重新認識麥金德等“明顯不合時宜的思想家”,他們因與帝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聯(lián)系而受到玷污。然而,卡普蘭堅持認為,“誤用麥金德的思想”并不意味著麥金德是錯誤的。因此,我們的討論又回到了長久缺乏安全感、在對山脈的恐懼和敬畏中畏縮不前的俄羅斯人這里。
地緣政治學家們認為,即使是強大的領(lǐng)導人,也難以違抗地圖的宿命。2014 年烏克蘭的抗議活動推翻了對俄友好的前總統(tǒng)維克多·亞努科維奇后,馬歇爾寫道,普京“不得不吞并克里米亞”。盡管馬歇爾譴責俄羅斯的侵略,但其語氣與普京用來自我辯護的語氣相似。普京在2014年談到俄羅斯的對手時說:“他們不斷地試圖把我們掃進角落。如果你把彈簧一直壓縮到它的極限,它就會狠狠地折回來。”有人可能會主張,是普京的想法和態(tài)度,而非地圖,正在推動俄羅斯的好戰(zhàn)性,然而地緣政治學幾乎沒有為這種因素留出討論空間。馬歇爾在另一文本中寫道,“所有能做的就是對自然界的現(xiàn)實作出反應。”
如斯特拉福公司前副總裁彼得·澤漢所言,地緣政治世界觀的核心是對“地理的不可改變性”帶來的限制的理解。馬歇爾解釋說,重新劃定幾條邊界線,“伊凡所面對的地圖也是普京今天所面對的地圖。”由于地圖和圍繞地圖的計算都鮮有變化,明智的行動主要在于接受頑固的事實。
伊恩·莫里斯寫道:“地理是不公平的。”如果如其所主張,“地理即命運”,那么這就是一個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世界的秘訣。地緣政治家擅長詮釋為何事情不會改變,卻不太善于說明事情是如何發(fā)生的。
這可能解釋了地緣政治家們對歷史明顯的模糊性。正如馬歇爾所寫的那樣,德國的統(tǒng)一是因為“日耳曼國家最終厭倦了相互爭斗”嗎?越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是否如弗里德曼所說,“只是美國歷史上孤立的事件,沒有持久的重要性”?是否真如澤漢所辯稱的那樣,“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英國人從來不需要擔心軍隊悠閑無聊地經(jīng)過”?或者如卡普蘭所堅持的,“美國注定領(lǐng)導世界”?地緣政治家們的歷史描述介于“令人愉快的微風”和“在下一輛旅游大巴到來之前匆忙地讓學童們穿過城堡”之間。
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那些制作地圖并經(jīng)同行評議的研究者,也就是真正的地理學家的寫作方式。像地緣政治理論家一樣,地理學家相信場所的力量,但他們一直堅持認為場所是歷史性地被塑造而成的。法律、文化和經(jīng)濟就像構(gòu)造板塊一樣產(chǎn)生景觀,而這些景觀也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
地理學家指出,即使是地形,也不像地緣政治學家所認為的那樣不可改變。澤漢在斯特拉福公司擔任了十二年的副總裁,一直認為美國的巨大力量可以歸功于其“完美的地理”。定居者們來到新英格蘭,遇到了不符合標準的農(nóng)業(yè)條件,“小麥是個硬傷”;但幸運的是,他們被鼓舞著占有了西部的質(zhì)量更好的土地。這些富饒的農(nóng)田伴隨著“真正的交易”,廣泛的河流系統(tǒng)允許以“低到可笑”的成本進行內(nèi)部貿(mào)易。澤漢指出,這些特點使美國成為“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并世代延續(xù)。
但這種因素并非恒定不變的。小麥曾經(jīng)在新英格蘭普遍種植,盡管澤漢堅持說它是“硬傷”。是害蟲的到來與破壞性的耕作方式造成的土壤枯竭導致糧食產(chǎn)量下降。澤漢非常重視的自然河流也是一個變數(shù)。為了讓自然河流發(fā)揮作用,不得不用昂貴的人工運河系統(tǒng)作為補充,然后在幾十年內(nèi)被新技術(shù)所取代。今天,按價值計算,通過鐵路、航空甚至管道運輸?shù)拿绹浳镞h遠多于通過水路運輸?shù)呢浳铮ㄜ囘\輸?shù)呢浳飪r值是船只或船舶的45倍。
這是另一種說法,即我們并不總是接受我們所繼承的地形地貌。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樓哈利法塔誕生于迪拜,幾個世紀以來,迪拜一直是一個不被看好的、被沙漠和鹽田包圍的漁村。從地形來看它并無偉大之處。迪拜氣候十分炎熱,石油銷售雖然曾經(jīng)很可觀,但現(xiàn)在只占其經(jīng)濟的1%以下。若說迪拜的與眾不同之處,應該是其法律景觀,而非自然景觀。該酋長國不受單一律書的管轄,而是被分割成多個自由區(qū),如迪拜互聯(lián)網(wǎng)城、迪拜知識園和國際人道主義城等,旨在吸引各種外國資金。城市理論家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曾寫道,迪拜沙漠本質(zhì)上是“一塊巨大的電路板”,全球資本可以輕而易舉地與之相連。
迪拜的朱美拉棕櫚島。
將迪拜打造成商業(yè)中心意味著以實際行動將其重塑,這違背了任何關(guān)于“地圖即命運”的觀念。迪拜繁華的商業(yè)活動大多通過杰貝阿里港,這是中東地區(qū)最大的港口。擁有一個巨大的深水港似乎是地理上關(guān)鍵的天賜良機,但實際上迪拜付出巨額成本才從沙漠中開鑿出這個港口。迪拜的工程師們用挖出的沙子制造了一些島嶼,包括一個由上百個島嶼組成的群島,如同世界地圖般陳列著。綠色的公園和室內(nèi)滑雪場使這個挑戰(zhàn)自然的奇觀更加完美。
遺憾的是,改造迪拜是我們能做的最起碼的事情。全球變暖正在擾亂地貌,威脅將島嶼淹沒,將草原變成沙漠,將河流化為塵土。奇怪的是,地緣政治文章鮮少對這一點展開論述。弗里德曼在《未來100年》(The Next 100 Years)一書的結(jié)尾承認,“讀者們會注意到,我并沒有處理這個問題。”除了一些短小的評論與旁白,莫里斯的《地理即命運》、馬歇爾的《地理的囚徒》、卡普蘭的《地理的復仇》和澤漢的《意外的超級大國》(The Accidental Superpower)也未深挖這一問題。
喬治·弗里德曼 《未來100年》
地緣政治家不愿意考慮氣候危機,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兩種選擇,要么超越景觀,要么與之共存。要么全球化將使我們擺脫物理限制,要么我們將繼續(xù)受困其中。由于新的技術(shù)與制度顯然沒有抹除地域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回到地緣政治學。
但真的別無選擇嗎?可能性更大的,是全球化的瓦解非但未讓人類退回十九世紀,更是推動我們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險象迭生的未來。在那個未來,我們將深刻體驗到環(huán)境的約束,卻并非通過地緣政治家所預測的方式。恰恰相反,塑造人類行動的將是種種人造景觀,包括我們改造物理環(huán)境的途徑,而非自然景觀。如卡普蘭所寫,地理絕非“一成不變”,而是反復無常。法古之輿圖,難領(lǐng)未來航向。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