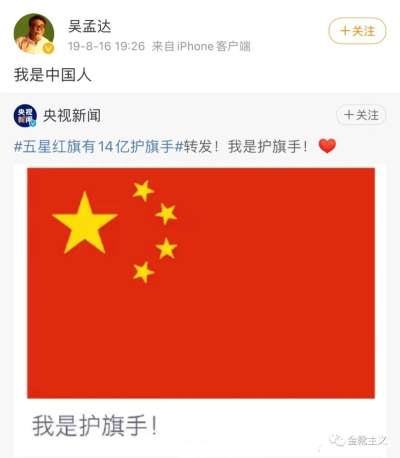簡單來說,就是歷史埋下的雷,今天的一言一行皆為歲月演進所致。
還是要從二十六年前的香港回歸說起。
1
在回歸之前,英國政府曾不向中方作任何通報,突然拋出過一個跨越1997年、耗資達1247億港元之巨的“機場及港口發展策略”,動用幾乎所有的財政儲備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政府舉債,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資本流向英國,意圖“掏空香港金融”。
而更早一些的1991年,英國先是把聯合國發布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改成了所謂《香港人權法》,提出許多人權方面的倡議,比如限制死刑、放寬國籍戶籍等;緊接著一年后,港英政府又宣布“解除社團限制”,完全放開港內港外的社團注冊,也宣布不再取締任何組織。
這就給大批NGO進入香港“備戰”提供了法理支持。
比如那個著名的“香港外國記者會”,拿著英國人在被驅逐前臨時更改的條例為依據,屢次邀請五獨分子來港演講、煽動獨派勢力對抗北京中央。
彭定康,這個末代港督正是在這個關鍵歷史時刻,由其政治摯友梅杰首相力薦走馬上任的。
這位在英國因誠信不佳而知名的政客,自稱“深知最大的試煉將來自政治競技場”,1992年上任伊始就在港英政府內部做了一個“嚴肅的形勢報告”,斷言:
北京政權不到1997年就會像歐洲的蘇聯、東德和波蘭那樣垮臺。
以此,彭定康動員政務官、公務員們跟著他一起“打亂仗”,放棄中英已經達成的所有協議、諒解的束縛,撈回十年前“英國在談判桌上想得到卻沒能得到的東西”。
1992年10月7日,上任僅三個月的彭定康發表了早在英國就打好腹稿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對香港面臨的1994年區域組織選舉和1995年立法局選舉提出完全另一套設計,掀起了后過渡期又一大折騰。
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魯平同志隨即指出,這個方案表面上仍然說要維持英國在香港多年來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但實際上是要急劇改變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機構的地位和權力。
這套方案在當時一度讓中英之間已達成的政權機構平穩過渡安排化為泡影。
彭定康先斬后奏公布政改方案后,不斷軟硬兼施要挾中方接受;中方自然堅決予以拒絕,直斥他背信棄義,是“千古罪人”。
但是,在彭定康借助首相支援和全力操控下,這套“政改方案”還是在港英立法局以一票微弱多數通過…事實上宣告了英國最后管治時期的香港政治體制已無法與未來中國香港特區基本法的規定相銜接。
1994年,中英雙方開始就渡期預算案編制問題交換意見,決定成立專家小組進行正式磋商。
財政預算案是現代政府理財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計劃和經濟政策的集中體現,對經濟民生影響重大。
按香港的慣例,每個財政年度從當年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
很顯然,1997/98 財政年度會跨越香港歷史性的回歸,其中前三個月為港英政府管治,后九個月將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管治。
這個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編制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完成,又由于財政政策、收支計劃的連續性,之前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必然對后一個年度的預算案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尚未產生前,由中國中央政府代表未來特區利益,與英方就 97/98、96/97 兩個過渡期財政年度的預算案編制進行合作,既是香港政權交接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香港財政政策平穩過渡的客觀需要,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精神。
而在實操過程中,英方對于這些重要原則看似表面上不持異議,實際上卻想獨自把握、以便配合其“光榮撤退”方案的實施。
因此,英方不僅想方設法阻撓中方參與預算案編制,還急功近利、不負責任地做大開支以粉飾殖民時期政績……
為了主導談判的方向,英方當時搶先公開向社會宣布將向中方“介紹”96/97 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編制過程,并就跨越回歸的 97/98年度預算案“咨詢”中方意見。
一口一個“介紹”,一口一個“咨詢”,先入為主地界定了中英雙方在未來專家小組中的角色。
彭定康于1994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以及英方在當年底向中方提交的書面意見均表達了上述觀點。
令人遺憾的是,中方代表內部竟然一度對此缺乏警惕,在1994 年底召開的兩次聯絡小組全體會議上居然都沒有對英方立場提出異議……
1997年的夏天,彭定康在離開香港前拋出了他最后一張重牌:草擬了一份五萬人的所謂“港英白名單”,單子上全是一幫“忠于英國統治”的香港上層精英,包括各類富商、政客、議員、教師、教授、媒體人……
他們所有人都收到了一個密碼,只要有了這個密碼,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的英國使領館都能帶著全家人火速入英國國籍。
當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并沒有走,而是選擇留在香港,繼續配合英國人保持香港各領域的殖民體系“不動搖”。
像陳方安生就是其中典型,她曾公然鼓吹:
香港回歸只是換個旗子,其他都沒變。
陳方安生確實沒有說錯,彭定康在滾蛋之前非常陰謀得把港府行政權分給了香港政務司,又將此前自己手下的“立法局”變更為獨立于港府存在的“立法會”,繼續保證英國對香港立法系統的殖民控制。
2
臨走前大肆分發“民主自由”的傳單,然而不禁試問: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個半世紀,什么時候講過“民主”?
在政治排序的圖譜上,香港人甚至還不如印度人,在自己的家園地盤上淪為“三等公民”。
一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中國共產黨制定了香港回歸日程后,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制的《基本法》,英國突然“如夢方醒”、在香港開始大搞所謂“代議政治,還政于民”……
一百五十年來,英國人從來有給過香港人一張選票嗎?
港督和港府主要官員,由倫敦任命,港府則既是三軍司令,又是立法局的主席,且有權否決法院所有的判案,是絕對的獨裁者;立法局,不過是港督的咨詢機構而非立法機構,局里的官守議員是港督委任的政府高官,非官守議員也是他委任的來自社會各界的代表……
一個半世紀的長史,被港獨分子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香港法院,其終審權一直掌握在倫敦的王室的咨詢機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手中。
這個有上千年歷史的機構是專門受理海外領地、王家屬地和英聯邦成員國家終審案件的。說白了,“殖民地案務專局”。
港英政府統治時期,香港每年有一二十宗案子要上報倫敦樞密院,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法律原則問題更是上訴焦點。
英國和香港地區雖同屬一個法系,但相距兩大洲,歷史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很不相同,加上樞密院的成員大多年事已高,對香港世態民情一知半解,做出的判決往往與香港上訴庭的判決很不相同。
饒是如此,終審權始終是在倫敦,而不是在香港。
在英國人看來,司法權力是他們統治香港最重要的一道楔子,它深深地插入香港社會的心臟,指揮著香港的國民教育、文化娛樂、媒體輿論……
直到數年前,香港名義上回歸已有二十余年,依舊會出現頭戴白發套的外籍法官杜大衛“赦免”港獨分子、“懲辦”港警的亂象——根據保釋制度,暴徒中的大部分人可以直接交錢回家,打砸搶燒的惡行可以連一天牢都不用坐。
甚至,直到2020年夏天更新的終審法院法官名單,都依舊“滿目狼藉”:首席法官一人,常任法官三人,非常任法官十八人——其中在三名常任法官中兩人為中國籍、一人為英國籍,十八名非常任法官中三人明確為中國籍、但其中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和英國雙重國籍,剩余十五人全部是純粹的外籍,分別來自英、澳和加拿大。
即,二十二人中只有兩個人是完完全全的中國人,其余全部為外國人(包括雙國籍)。
還記得那個著名的港庭終身法官包致金(Kemal Bokhary)嗎,任職期間在香港橫行霸道,侄女更是仰仗英方權勢在港無牌駕駛、暴力襲警、劣跡斑斑……
這也就不難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為何遲遲不能落地。
與之對應的是《基本法》第92條和82條,只對香港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存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的規定,但對其他法官的國籍沒有任何限制。
這就是歷史上用以描述1997年「香港回歸」的真相。
3
近三十年來,香港的一切都宛若大陸的某種臨摹“模板”,用許多人的話說:
中國的第一縷國際春風,正是由港風帶來的。
靡靡之音、燈紅酒綠之間,直至今日,以英國皇室成員、港督、殖民地官員、英軍軍官命名的街道,香港仍有八百多條。
連日本法西斯在1941年侵占香港后,“日督”磯谷廉介都知道發布“公示”將香港的所有英式地名改為日式名稱,而我們1997年正大光明地收復作為故土的香港,去殖民化工作卻似乎從未做到位。
埋雷,一直埋到暴動的2014和2019(事實上還有很多,如2010年“反高鐵”運動、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2015焚燒《基本法》事件……)。
逆向種族主義的恐怖分子其瘋狂,讓信仰一直以來搖擺不定、始終處在“我是誰,我的媽媽是誰,我從哪里來”的困惑之中的香港,一步步墮入歧途。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與中國政治母體之間始終存在嚴重的互信不足。
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作為外來權力管治的土地,香港孤懸于中國的政治體系之外仿佛成了一種默許的共識,造成日積月累之下同大陸主體政治秩序之間存有天然隔閡。
在長期的分離、分治狀態下,受到殖民操控的香港其政治文化、政治話語與政治精英都早已不屬于中國本土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政權,對于香港而言似乎皆屬政治上的“他者”,而香港在中國本土政權眼中亦是陷于南方一隅的化外孤城。
這種相互剝離,形成了香港社會同中國本土政治秩序之間彼此相安無事則易、而建立和維持互信則難的狀況。
從2014到2019,同一波年輕人,從幼稚走向野蠻,從跟風轉為仇恨。
所以今天時不時就會發生的一系列“歧視事件”,真的一點不奇怪。
四年前,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就通過發表不實言論不斷地抹黑和詆毀特區政府,更是在“修例風波”爆發后于2019年7月26日組織人員在香港機場舉行了一場反華游行。
要看到,法律層面扭轉歷史只需要一兩年(《國安法》早已落地),但是想在文化層面扭轉歷史,則需要突破三代人不止的思想桎梏,打破他們早已經與現實脫離的種族優越感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原因嘛,還是那句話:都是歷史埋的雷。
4
更讓人遺憾的是,曾經60年代我們對香港一度是占據文化高位和意識形態輸出地位的,只是一切都一去不復返了。
經過60年代洗禮的香港人多是愛國的,且他們拍攝的諸多影片也都表達著愛國情懷,絕無后來年輕一輩的媚外和自我矮化。
60年代中后期的六七暴動至今寫在香港歷史的光輝冊上,那是港英當局被迫撥政向善的轉折點,既是香港底層市民、香港左派的小小勝利,也是文革“南延”的一次正名。
回想60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緊張,存水量嚴重告急,正是毛主席力排眾議作出決定:
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們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應由我們舉辦,列入國家計劃。
于是,東江之水跨山而來,解決了香港幾十年一遇的大水荒。
再回想1894年時的香港大鼠疫,至今無法統計有多少香港人死在港英鬼子“潔凈局”的刺刀下。
有良心的香港人,都會記得,記得他們都曾屬于那個紅色的中國。
只不過,“有良心的香港人”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中還是否是市民主流,已經很難去估量。
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時(2012年),香港的國民教育(即愛國教育)方案竟然才姍姍來遲、磨磨蹭蹭地走上臺面。
即便如此,愛國主義運動在香港又面見了如何境遇?
2012年5月13日,香港反國民教育的“學民思潮”組織發動“513撤回國民教育課程大游行”;
7月,由香港部分家長組成的“民聲團體”,成立了所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要求港府撤回國民教育課程,此后又聯合“教協”等團體發動“全民行動,反對洗腦729大游行”;
結果是,2012年9月8日,時任特首梁振英被迫宣布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規定,改變為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辦國民教育科及其教學方式”……
這等于是將「愛國」這一現代國家之政治必須、又是國民樸素情感之凝聚的基礎性國家工程,交給了暗流涌動的“泛民”們,以及他們背后始終虎視眈眈的英美。
嚴格而言,1997年除了解放軍雄赳赳氣昂昂地進駐了香港(關于軍事用地的談判也用了足足七年),其他維度上都很難看到中央對香港的管理,尤其在經濟和文化層面。
不說香港人彼時是怎么俯視我們的,二十余年前就連我們自己都拿香港當天堂仰望,《讀者》《意林》等小布爾喬亞刊物上關于香港人高素質、香港城市環境優美、香港制度先進的小作文數量,一點不亞于對日本、德國、北歐、北美……
今天朗朗上口的“四個自信”,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
就連那位在90年代叛逃到美國的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職級相當于今天的中聯辦主任——的許家屯,竟然在黨內和大陸民間,彼時都有不少聲音對這位親近李嘉誠等香港寡頭與上層權貴的黨的叛徒,抱以“理解”。
一個在回歸前葬送了黨在香港的布局路線的政治叛徒,卻引起不了多大波瀾,這已然反映了當時大陸對香港的“燈塔式仰望”。
2001年2月14日,在時任總理的親自推動下,國務院任命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史美倫,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消息一出,全國震動: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從海外聘請的首位副部級官員。
十年后,作為英國殖民香港標志之一的香港大學,舉行建校百年慶典,從北京前往祝賀的領導在慶典上竟出人意料地用英語宣講……
今天回看,不失為一闕符號性的回聲。
市場經濟,開發開放,國際都市,地產先行,培育巨企,鼓勵造富……
還是那句話,“歷史埋的雷”,而埋雷者有何止英國殖民勢力與香港獨立勢力呢?
5
回看史冊,“一國兩制”政策構想,原本為統一臺灣而提出,而被首先運用到香港和澳門其實是歷史機緣巧合促成。
香港是現代中國的創傷性記憶,1842年清廷于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連同鴨脷洲和附近島嶼)永久割讓給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及其合法繼承人。
1860年,清廷再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敗于英法聯軍,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永久割讓給英國。
1898年,清廷再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據此租借“新界”(包括新九龍及逾二百個離島),為期九十九年。
這三份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承認的不平等條約,實際上形成了今天香港特別行政區所轄領域的大致范圍。
自70年代末開始,隨著新界地區租借期限的不斷逼近,在英國政府的動議和催促下,中英兩國政府才開始進行關于香港前途命運的外交接觸、商討和正式談判。
中英關于香港前途地位的談判,恰好與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思考臺灣統一問題的時間重疊,這使得領導集體開始考慮將剛提出不久的“一國兩制”構想,率先運用于香港回歸。
以“一國兩制”的方略來解決香港問題確實是一個政治層面的創舉,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這一問題是在非常倉促的情形下被提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議程的。
實際上,當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并與小平同志首次談及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剛剛結束對越南的大規模自衛反擊作戰不到十天,中央政府尚未對香港在1997后的地位和管治問題做出深入研究,遑論做出重要決定。
隨著中英關于香港前途命運問題的接觸和商談的深入,中國政府才逐步把香港回歸這個問題在內地百廢待舉的情況下“插隊”提上議事日程,并最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就香港在1997年回歸形成了初步決策。
起初,我們對于“一國兩制”框架下未來香港政治運行的設想,是十分“急凍式”的回歸。
即:快速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時分將香港既存的社會經濟、法律和政治制度基本不動地接收,保持大體不變,然后再因應時代的變化擇機予以解凍和變革。
80年代香港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最常聽到的六個字——“馬照跑、舞照跳”,就形象地表達了北京對于在回歸完成后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不同于中國內地的生活方式的設想與愿景。
80年代,北京甚至有官員表示香港回歸不過是“換面國旗、換個總督”般簡單,中央對港工作系統的負責官員也經常強調回歸后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華人公務員隊伍、精英階層地位、司法體系、營商環境等,均會同港英殖民地時期保持“高度連貫性”……
甚至,某位主政對港工作官員曾說出“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 是香港自治權范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一涉”之類極為寬厚的政治表態……
香港回歸后,中央政府還將港英時期派駐香港的隱蔽戰線力量幾乎全數撤回北京,原因就是:回歸之后香港都是自家人了,特區由港人掌握“完全放心”。
“急凍式”回歸,因而實際已超出了其作為一個較為原則性的、粗糙的、“摸著石頭過河”式的初步政治設計的本來面目。
這被不少香港居民有意無意當作是北京中央權力對自己做出的某種具體承諾和香港回歸的某種既定模式。
也使得部分香港市民后來對于“一國兩制”的理解,始終存在政治性偏差。
那么,對于未來,面對今天人均GDP25000美元的臺灣省,其經過七十年甘當帝國主義仆從的冗長崛起期、憑借地緣優勢而壯大的殖民地經濟規模事實上非常穩固的割據狀態,我們還要繼續沿用“歷史經驗”嗎?還要繼續埋雷嗎......
跋
1960年12月24日,聯合國通過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帶領四十余個亞洲國家提出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草案。
這個草案,將香港和澳門納入了名單之中。
正是這份《宣言》,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自決權”,使其可以“自由決定其前途,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
從歷史縱向維度而言,這份《宣言》成了此后蘇修進一步炮制所謂“有限主權論”、干預第三世界國家內政的預演。
其時,正是毛主席敏銳覺察到蘇聯和西方帝國主義集團有可能通過該法案干香港、澳門等地區形成事實“獨立”。
為了將中國的主權領土——香港與澳門從法案名單中永久刪除,在聯合國席位彼時仍被蔣介石政權非法把持的情況下,毛主席與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勢力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斗爭。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毛主席立刻指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盡早行動:港澳問題完全是為中國主權范圍內議題,不可以“殖民地”性質而論,應將港澳兩地剔除出名單。
1972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對港澳問題進行表決:支持刪除99票,反對5票,其余棄權。
香港和澳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底色,被毛主席以不容撼動的政治決心成功維護,也奠定了此后回歸祖國的水到渠成。
兩年后,1974年5月25日,年邁的毛主席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對香港問題做出了最后的交代。
中共中央檔案館保留的談話稿上準確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都成歷史了!你們剩下一個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也不談。到時候怎么辦,我們再商量吧。是年輕一代人的事情了!
苦盡孤心縱身付,山河悲風一曲吟。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