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這兩天在微信朋友圈很多轉發騰訊資本控股的「谷雨實驗室」所刊發的《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本呆迷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誤認。
一個朋友誤認為文中受訪者提到的「清湖勞務工圖書室」是由「清湖學堂」開辦的,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很抱歉,「清湖勞務工圖書室」是官辦的,并不是「清湖學堂」開辦的。
這圖書室從F廠小北門出來就可以看到,在村里非常醒目。而「清湖學堂」在村里的小巷子里,招牌小,非常難找。笨呆路癡,第一次去參加活動導航找不過去,問了來來往往很多人,都說沒聽過這個名字。
工時長,身體乏,各式手機娛樂占有休息時間,到底能有多少一線工人會留意到「清湖學堂」的活動呢?我不知。反正我有參加過幾次免費英文培訓班,外國老師讓自我介紹,大部分學員都是文員之類的,而非前線工人。
當然,如果文中受訪者是「清湖學堂」的「工友」,那就更好理解了。且不論這些反動哲學與The Governance of China到底有何區別,難道這類哲學與升官發財不是同一種意識形態的不同面向嗎?參加「清湖學堂」的朋友,很多人難道不是為了更好地晉升嗎?
哲學可以成為革命的武器,但它首先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文中受訪者的學哲學與升官發財,大概可以算作殊途同歸了。
要知道,「清湖學堂」不過是當地衙門的持牌合作方中的一個,但隨著「清湖學堂」早已被朝廷剿滅,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之中,它放佛被指認為了教化移民工人進行抵抗的牧師,成為想象的菲勒斯。
此外,我有留意到受訪者說很嫌棄對岸用語,諸如「軟體」之類。我也有同事告訴我,她沒緣由很討厭傳統儒字,即使自己可以讀懂。在這里,被剝削的身體生產了抵抗的無意識,而毋需「清湖學堂」們的教誨。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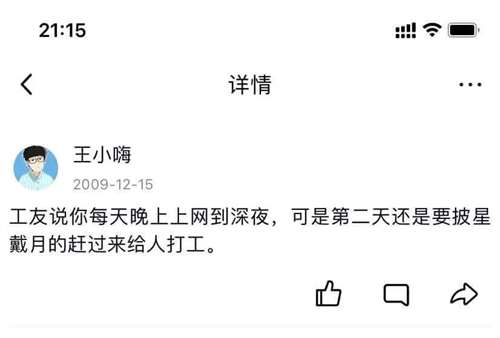
十幾年前,我進入家鄉一間小食品廠做工。每日清晨六點起床,媽媽早就給我準備好了早餐,我匆匆吃完,去趕公交。在車間,我面對巨大的機器,還有流水線,不知所措。帶我的小姐姐,教我怎么做工,怎么玩手機不被班長發現。
工閑時,我與前面工位的一位大哥聊老板與工廠的關系,他說老板死掉了,工廠可以照常運轉。下班后,天色早已漆黑,我拖著一身酸臭去等公交,帶我的小姐姐騎電瓶車路過,說要載我回家,我羞澀地說「謝謝,不用了。」
那時,我剛接觸馬克思主義,白天做工,晚上回家看徐禾的《政治經濟學概論》,越讀越興奮:原來資本家是這樣剝削工人的。深夜一兩點合上書后,我拿出mp3,聽著張廣天老師的歌,沉沉地失去意識。
后來,我又輾轉到了家鄉港口做保安。工作要求不許玩手機,我就拿著小紙條背單詞。休息時間,我和遠方的同志聊馬克思,聊毛主席,聊精神分析和哲學,聊我們的過去和未來。仿佛世界就在眼前展開,即便我只是一個辦公樓前的保安。
再后來,我去昆明念書。很多朋友都說我的故事很勵志,從保安到哲學系學生,簡直是資本主義的神話。可這樣的經歷并沒有讓我欣喜,反而讓我更加認識到資本主義所提供的改變可能是多么虛假,哲學系的老師有多無聊。
許多朋友都在微信朋友圈討論騰訊谷雨那篇文中的哲學愛好者,我并不覺得業余時間讀哲學有什么神奇,這不過和打游戲一樣,也是一個很平常的愛好。
每個真實都可以有許多敘事的可能。比如妳說因為日常生活沒有改變的可能,一個工人在游戲中開啟主體的行動性,從而開啟了改變的可能。坦率地說,這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說詞。
可問題在于,我們應該如何看到真實的實在,誰在創造財富,誰又在剝削。如果僅僅是業余時間讀哲學,我不覺得這和業余時間打游戲有什么區別。
相較大家更多地討論所謂「文化資本」與「階級凝視」,我個人認為,騰訊谷雨受訪者所表達想進入學院,專職做哲學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想法更為有趣。這種想法顯然是一種資本主義價值敘事的典范。
一個移工對周遭世界與生活產生了困惑,沒有去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而去讀學院里的經院哲學,這不僅得不到任何答案,對自身的處境也并無益處。這令讓人心酸。
從工人到哲學意識形態工作者,還是工人到有機知識分子,好像并沒有所謂的「左派」關心這個論題。
回到我自己,十多年來,我從工人到工人,經歷了發現新世界的欣喜,也有被背叛的幻滅。曾經的同志已然陌路,不過是一拍兩散。帝國的旗幟迎風飄揚,各自珍重,狗命要緊。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