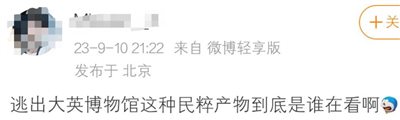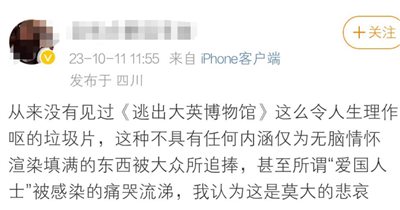前段時間,在某視頻網站上,一部低成本的自制視頻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引出一波“收視狂潮”,與之相關的話題也在許多社交網站上的一再引發大量的討論。從形式而言,《逃出大英博物館》短劇總時長只有17分04秒(本劇分成了三集),甚至無法與其他網劇正常的一集相比。但從其引發的效應而言,這部短劇卻遠遠超越時下動輒五六十集的劇集。
不出意外的是,當《逃出大英博物館》一再被“沉默”的大眾所肯定時,掌握了“話筒”的、被規訓的某些媒體以及自以為與這些媒體“所代表”的“精英性”的知識人自然會以一種姿態出來說怪話。這反映了一種確然存在于當下輿論場中的“話語權力”。而令人扼腕的是,大眾不止一次受到過這種“話語權力”壓迫,憤而抗爭的結果卻往往不盡人意。因此之于筆者而言,厘清這種“話語權力”的脈絡,還給大眾建構自身“話語權力”和消解對方“話語權力”的權利,就顯得非常必要。
在本文中,我們將會從某些的媒體的文章出發,經過BBC的文章,最后回到預定達到的目的地。希望讀者從這一趟旅程中,能夠掌握誕生于舊世界體制的話語的一些特征。
《南方周末》在9月5日刊登了一篇題為《混淆文物與工藝品,賺取愛國流量,真的好嗎?》的文章,而這篇文章刊登的同日的15:09分,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的第三集才剛剛在相關視頻網站上放出。易言之,這些媒體在面對《逃出大英博物館》一劇時,多少有點急不可耐,試圖在其形成效應時把其認為的這部短劇的短處“揭露”于讀者面前。
而在這篇文章出現后不久,以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平臺中,形成對這篇文章的“反擊”,并就這篇文章的種種訛謬之處作了指正。例如,這篇文章認為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在選取以中華纏枝紋薄胎玉壺為擬人形象時,混淆了工藝品和文物,但事實上這是短劇作者特地選取了一個現代工藝品,是有意為之,它的作用就是“回國送家書”。
又例如這篇文章以為中國加入了《關于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就“很難從法律上追索包括敦煌文物在內的大多數海外流散文物”,但事實上國際公約與國際法是兩回事,將公約充作法律,是典型的“胡說八道”。因此,這篇文章在事理上已經站不住腳。
但有趣一點在于,《南方周末》在文中使用的一些也被今天大眾所接受的東西,卻很少有人做過討論,也許這些才更有深究的價值。
【一】關于“文物保護”的強盜邏輯
例如文章中有這一段話:
“從今天的觀念來看,史克曼無疑做了一件偉大的事,他讓破碎的文物再次拼合,那我們需要向納爾遜-斯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聲索《文昭皇后禮佛圖》嗎?至于被普愛倫買走的《孝文帝禮佛圖》,我們知道普愛倫惡意引導別人破壞了文物,但我們在法律上如何向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聲索呢?畢竟他有當時的買賣合同。”
在引用這一段話時,筆者將部分文字加粗,以凸顯這篇文章的“邏輯”。
從這一段話中,我們能看到在援舉第一個例子時,文章用了“率先保護”的暗示,將文物的流失歸罪于母國當時的保護不力。亦即,由于母國的不重視導致了這類文物以所謂“異地保護”的形式而流失。
顯然,作者在這里訴諸了一個典型的“邏輯”:大前提是,文物是人類的遺產。小前提是,作為人類的遺產,人類就有資格保護。所以結論是,文物應當被人類保護。進一步推理,文物被誰保護,文物的所有權就在誰那里。
這個“邏輯”是典型的“滑坡推理”,或者我們可以用更為直白的話來稱呼——“強盜邏輯”(為了討論方便,下文將這個邏輯稱為“邏輯A”)。
在這個邏輯中,大家都知道“文物”是有標準的,但是往往會忽視“人類”也是有標準的。
當我們回溯包括“文物”在內的整個世界歷史的時候,我們會清晰地看到,與“文物”收藏地——博物館的誕生的“原罪”,也即與西方殖民活動相貫穿的“殖民主義”,而“人類”這個詞恰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地理大發現”使得在越洋航線上旅行的歐洲人看見了超越于歐洲以及近東、中東與遠東的人,為了區別同時也是為了將自身粘附于所謂“文明”之上,一種“當代人類學”誕生了。
所以,當對于這個“人類”的概念不加批判的吸收與使用時,我們會發現,我們使用的“人類”一詞與承源自西方話語的“人類”形成了同詞異指。
于是,當我們更為明晰的翻譯那個邏輯A時,我們會發現這句話的意涵是這樣的:大前提是,文物是[擁有文明的人群]的遺產。小前提是,作為[擁有文明的人群]的遺產,[擁有文明的人群]就有資格保護。所以結論是,文物應當被[擁有文明的人群]保護。
于是一個更為清晰的排他性出現了,“文明”作為了先決條件。那么何者為“文明”,何者為“非文明”(抑或是使用更廣泛的詞匯——‘落后’)?無疑,在這樣一個延續了殖民時代的話術中,這一條件成為了殖民主義的“準入證”。因此,當視角從此處明晰了之后,我們再看其滑坡推理的“文物被誰保護,文物的所有權就在誰那里”,就會感到其中蘊含的無恥與霸凌。更進一步說,當殖民主義尚未得到清算時,任何試圖為合理化殖民主義的結果的行動本身就是最大的殖民主義。
同樣的,在這段話援舉的第二個例子時,文章試圖用所謂法律抑或說合同,來限制一種被追索的可能。其言下之意是說,存在這樣的“合法”的契約關系,這些“合法”的契約關系保證了文物的所有權的“轉讓”,時過境遷之后,推翻這些的契約關系是困難重重的。這個邏輯(為討論方便,稱其為邏輯B),相較于邏輯A,顯然更為強詞奪理。
因為在邏輯B中,有一個“推翻”的結果被假設了,而相較于這種“推翻”,首先是那些“契約關系”被承認。問題在于,作為這樣一份通過以偷盜行為來作為“契約”成立的基礎的合同,“承認”難道不是對于法律尊嚴的最大的損害么?文章所謂的“合法”,除了合那個規避西方罪惡的法之外,到底合了什么法呢?從此可見,隱含于行文背后的“承認”,不過是那篇文章的一廂情愿,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強加人意。
【二】文物流失的“客觀結果”
當然,在《南方周末》的這篇文章中,最值得檢視的還不在此。在此文行文的后半部分,作者利用1930年斯坦因盜掘敦煌文物,因《古物法》的限制最終保存于中國卻在數年后不翼而飛的例子,以及“客觀上,中國文物流散促進了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了解”的說辭,為多年來盛行于輿論場上的,所謂“文物被盜掘了要比在本國破碎了好”的論調來背書。
這一論調同本文之前所舉的邏輯A是一致的。也即是,首先承認文物的“人類遺產”屬性。進而推導出為了維護“人類遺產”,相關方可以使用極端的手段來達到目的(為討論方便,稱其為邏輯C)。但這一邏輯C與邏輯A存在著一樣的問題,那就是其反復強調的“人類遺產”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無區別性”。
從大眾的情感與認知上而言,“遺產”是兼具了從物質到精神各種價值的東西,采用任何手段保護這一價值的具象,沒有任何的問題。但麻煩之處在于,這一邏輯本身是不能不加辨別地使用的。
因為文物這種“遺產”的歷史留存性必須在原歷史環境中才能夠得到完整的表達,太平洋群島上土著的東西,只有在群島上才具備了真正理解的可能,當脫離了這一個原歷史環境,文物只不過是從墻壁上剝落的一塊墻皮。拿著這塊墻皮的外來者,除了利用這塊墻皮進行充斥著浪漫的“異域空間”的想象之外,他所能做到一種正確理解少得可憐。特別是當文物進入博物館之后。
博物館的起源往往被認為是在公元前300年亞力山卓設立的“繆斯”(Musaeum),這個“繆斯”中收藏了亞歷山大大帝在亞非歐三大洲征戰時獲得珍寶。易言之,博物館最本質的特征,是一個私人的珍寶館。到了歐洲進入文藝復興時期之后,稍稍具有公共性的博物館方得以出現。所謂稍稍俱有,是指當時得以進入博物館的人往往是當時社會的中上層人士,底層人士被排除了參觀者的序列以外。在法國大革命之后,本來作為皇宮的盧浮宮變為盧浮博物館,允許來自各地的各種人士參觀。這時候,真正的公共博物館才出現,但是這時候的公共博物館提供給參觀者的,仍舊是一個進入想象的“異域空間”的途徑。而文物起到的作用,正是這個想象的“異域空間”的中介物的作用。
誠然,博物館在形式上似乎提供了文物一個較好的保存環境,使得文物的實在與具象不至于為時間磨損(但這對于大英博物館不成立,詳見螺旋真理在今年8月28日于其微博上發布的《再論大英博物館與文物返還》一文),但在更大意義上,博物館這個空間隱藏了、取消了或者說磨損了附著于的文物上的更大的文化內涵(這就是文物需要卡片介紹的一個更本質的原因),特別是那些非本土的文物,特別是那些通過被偷竊、被劫掠進入博物館的文物。——這些文物被其進入博物館的方式粘附上永久的、令人鄙視的炫耀的意義。
【三】來自殖民主義的規訓
復次,在邏輯C中,有一個“責任”及其內涵也需要分析。邏輯C的“責任”是說“作為人”而言,其維護這些“文物”是一種必須承擔的義務。這一說法非常冠冕堂皇,冠冕堂皇到甚至成了殖民者明火執仗的遮羞布。
但在分析邏輯A時,筆者就指出過,“人類”一詞的意涵是不同的,這個詞在歷史上曾是一個西方中心主義的詞匯。在此處,邏輯C的“作為人”同邏輯A的“人類”都具備了作為西方中心主義的詞匯的特征(可以試著比較“近東”“中東”“遠東”三個地理詞匯的預設原點所在)。
換言之,當“作為人”判斷這種“文物”在其母國將得不到維護時,所以“作為人”就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完全違反人類道德和當地法律在內)拿過來。這種完全錯誤的邏輯,除了是對強者的開脫之外,還是對于弱者的倒打一耙。
值得說明的是,以“文物被盜掘了要比在本國破碎了好”的論調既有明顯的“事后之見”,也是鮮明地胡攪蠻纏。一方面,在這個論調中,且不說“文物”需要被鑒定出來,即使是“好”字也蘊含了被價值審判的判斷。
舉例而言,一個清朝人在某天會失手打碎一只珍貴的碗,但是這一天他家要是被八國聯軍劫掠就可以使這只碗通過八國聯軍之手保存到今天,難道可以為這一只碗洗脫八國聯軍的罪惡嗎?更遑論,在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所標的的“大英博物館”中,多少文物是被毀掉了原來的保留地——“圓明園”后而流入的(令人痛心的是,更多的文物毀滅于這個流入過程中)。視“圓明園”的毀掉及其中“文物”的流失為歷史的必然,本身就是被西方殖民主義規訓出的認知。
另一方面,這個論調顯然是依托著所謂的“超越國族的世界公民”的背景而言的。也即,作為一個人,特別是一個知識人,首先應該自我承認的是他的世界公民身份,他不能受制于什么“狹隘的國家、民族”,而應該從全人類的視角出發去看待事物。這個預設背景在許多討論中往往被忽視,但卻是一個殖民主義慣用的“大帽子”。這必須加以解釋,為何這個看起來充滿了對人類命運的宏大關懷,卻更像一個難以忍受的火坑?
單刀直入地說,正是因為“世界公民”的“世界”,是延續了那個曾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輪番肆虐并還在肆虐的“世界”,成為“公民”除了被一個超越了母國的更大的權力組織所訓使外,本身更加不可能對這樣一個權力組織抗爭。
進一步,當這樣“公民”要對此加以抗爭之時,他必須依賴于一個小于“世界”的群體。小于“世界”即非“世界”,所謂的“世界公民”就是虛假的指稱。那么,自稱“世界公民”或者默認“世界公民”的理由最后導向的,不過是對于原先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締造且維持的這一世界無力的默認。
因此,“超越國族”的講法,同樣不過是順應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得出的把一切拱手讓人的自我閹割罷了。
在完成對《南方周末》這篇文章的分析之后,我們要更進一步進入BBC 的文章。因為與《南方周末》文章在事實方面的千瘡百孔不同,BBC顯然使用了一種“更為客觀”語調來敘述這個事。自然,執筆這篇文章的來自于Fan Wang 與 Derek Cai 兩位一眼從名字上就足以辨析清楚的華裔。
在這篇文章,兩位作者為英文讀者們先介紹了一波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的內容以及這出短劇的收視率,隨后點明該劇在各方面的評價,包括那些在抖音和微博上的熱評。最后將評論此劇是為對應與西方日益緊張的關系而被“推動的”“強大的中國認同感”產物。
不僅如此,為了增強這一段評論的可信度,兩位作者又引據了留學生抗議Dior“文化挪用”馬面裙的事情,并溯及了在短劇播出之前《環球時報》發起的“請大英博物館無償歸還中國文物”的話題。
在這篇文章中,兩位作者顯然延續了由政府操控民意的陳詞濫調,而且還延續了西方理解中國時采用的“沖擊-回應”模型。這些或明或暗的行文邏輯體現出一股的西方中心的傲慢味道,正如他們對待文物時更側重珍寶的意義一樣,這些人的視角完全視大眾之中普通個人的情感為虛偽之物。
易言之,他們完全不相信在中國社會中普通老百姓在公共事務里就可以與官方的立場一致,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通過官方對于公共事務的處理來寄托個人的意愿和情感。
在這種傲慢之下,他們將相信者稱為“蠢”或“壞”,更進一步地稱其為“又蠢又壞”。事實上,這些人獲得的除了一點虛幻的自我滿足感之外,更大程度上獲得的只不過一種自我欺騙。正因如此,BBC的這篇文章在表現出自身面對歷史洪流時的急不可耐之外,無疑更展露出一股自艾自憐的破落貴族氣。
另外,此文對于民族主義的指控也值得分析。因為此文對于“民族主義”的使用,延續的是一個經典定義。在大眾認知里,民族主義是狹隘的、頗為負面性的,并且在扭曲了或者說簡單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是一個想象出來的政治意義上的共同體”之后,民族主義幾乎被視作另一種奇妙的虛無之物。可惜的是,這里恐怕存在著種種的誤讀。
其一,由于中文詞匯的一詞多義的特征外加特定的歷史現實,印在身份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民族”在詞面上耦合了。從“民族主義”的起點出發,也即從其nationalism的詞源分析,在中文語境中,“民族主義”更準確的稱呼是“國族主義”(下文討論時,將采用此詞)。那么在此基礎上解釋同一個國族之下的諸多民族的現實,自然就能看到其多元一體的寬泛性(應當注意,這種寬泛性是針對于內部而言的)。
其二,之于國族主義而言,盡管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借用其早年間在東南亞做人類學研究獲得材料來厘析國族主義的起源,但不可否認的是,安德森的厘析本身并未否定國族主義是存在積極作用的。放大國族主義的負面性,并將此手段融入到一個殖民者對于被殖民者的指責之中,除了惡意之外所能看見的只有讓被殖民安穩做好“奴隸”的企圖。
其三,一旦當我們回溯到安德森的文本之時,我們看到的安德森寫作的動力之一即在批判性地支持對于聯合王國(UK)的指摘(當然還有對美國的指摘)。吊詭的是,這些指摘一再被那些飽受歐美的折磨的國土上的知識分子的忽視。只能說自歐美新自由主義風行以來,全球南方是反復接受了以此核心的“文化”的規訓。
以上三點所言及的誤讀,都指向了當下一種“話語”的共通謬誤,也即通過“斷章取義”式的論據,采用看起來更為“宏大”的背景抑或是關懷,消解掉抗爭的意義,乃至于洗白殖民主義的歷史罪惡。在BBC和《南方周末》的文章中,都展現了這個能夠令人產生生理性不適的行文邏輯。
【五】余論
通過歷史考索,我們能夠發現這種話語的產生與西方殖民世界的歷史千絲萬縷,與從殖民時代誕生出的國際體系藕斷絲連。因此,在當下很多話題的討論中,我們都可以在輿論場中看到殖民主義是如何一次次地逃開被清理,一次次地改頭換面、堂而皇之的被論述的現實。
這種舊“話語權力”的誕生與消亡都會與現實形勢產生脫節,也即有非常嚴重的滯后性。但這并不代表對其奮起抗爭是無意義的飛蛾撲火。筆者認為,只有深化以抗爭作為的對話的方式,厘清對方種種論述中那些不易為人察覺的、帶了面紗的所謂超越國族的、俱有世界公民性質的言論背后的對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更為本質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漠視,才能真正誕生屬于大眾自身的話語權力。
歷史滾滾向前,遲早要將這個世界推到重塑的那一個坐標上。短劇《逃出大英博物館》的出現,是邁向那一個坐標的美好先聲。筆者相信,即使目前現實還有非常多的困難亟待解決,還有非常多的人在隨意唱衰,在不久的未來,類似于《逃出大英博物館》這種傳達大眾“話語”的影音文字作品還是會如春筍般涌現,那種深植于舊世界體制脈絡的“話語”還是會如同被碾過的齏粉一樣隨風消散。
歷史在它的推動者這邊,在屬于遭受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更為本質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深重苦難的人民這邊。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