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對利潤的盲目追逐導致大氣污染、水污染、核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問題,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生存。大范圍的生態運動在歐美乃至全世界不斷高漲,形成了包括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環保主義者在內的規模龐大的綠色陣營。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派將馬克思主義與全球生態運動相結合,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為了解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派對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生態危機及其應對措施的看法,《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的記者于2023年3月對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進行了專訪。
在這篇訪談中,福斯特不僅介紹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來龍去脈、不同派別之間的差異,更從我們當下的生態危機談起,分析了危機背后的帝國主義格局。
概括地來說,福斯特的觀點是: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是我們最基本的關系。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需要與自然不斷“對話”,這是我們自己存在的基礎。馬克思強調了人類與自然世界的共同進化關系,也強調了自然的人性化和人性的自然化的生態必要性。所以,工人階級的斗爭不僅局限于工作場所的罷工和斗爭,也存在于工人階級物質生活的各個領域,其中也包括環境(人造的和自然的)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
福斯特還提出了環境無產階級的概念,將環境問題與經濟問題、無產者、農民和原住民結合在一起。無產階級的環保意識正在覺醒,這將決定人類對全球危機的反應能力。而這場斗爭已經開始了。
受訪者 |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者
采訪者|賈可卿,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當代理論思潮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采訪、整理并翻譯本文.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福斯特是美國俄勒岡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每月評論》期刊主編。他學術視野開闊,研究視角獨到,并且勤于著述,對整個國外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其代表性著作(含合著)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2000)《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2002)《生態革命:與地球和平相處》(2009)《生態斷裂:資本主義對地球的戰爭》(2010)《馬克思與地球:一種反批判》(2016)《自然的回歸:社會主義與生態》(2020)《人類世的資本主義:生態毀滅還是生態革命》(2022)等。此外,他還在《每月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相關文章。
一
馬克思主義生態學具有重要價值
賈可卿
福斯特教授,您好!您能不能介紹一下當前世界范圍內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研究的大致狀況?比如在您看來,有哪些代表性學者和代表性刊物?
福斯特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許多杰出的環保主義者,如泰德·本頓(Ted Benton)、安德烈·高茲(André Gorz)、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和喬爾·科威爾(Joel Kovel),都是新左派的傳統代表人物。但他們對馬克思和整個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非常不滿,認為馬克思等是所謂的“普羅米修斯”般的人物(代表極端工業主義和生產主義的立場),并且是“反生態的”。因此,他們的理論主旨是將傳統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和階級的立場與本質上主要是自然倫理的綠色理論進行折衷結合。在某些情況下,這也涉及將馬克思與其他人物結合起來的嘗試,如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被錯誤地視為一個環保主義者)或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他們被認為提供了一種更具社會民主精神的政治經濟學,有時被描述為比馬克思的分析更加環保。本頓認為,馬克思(與馬爾薩斯相反)未能認識到環境的局限性。對于詹姆斯·奧康納和瓊·馬丁內斯·阿利耶(Joan Martinez Alier)來說,馬克思“拒絕了”烏克蘭馬克思主義者謝爾蓋·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提出的生態經濟學——盡管后來的研究證明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就喬爾·科威爾而言,馬克思的“主要失敗”在于否認自然的內在價值。這些環保主義者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當時對蘇聯解體的反應,以及試圖將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傳統劃清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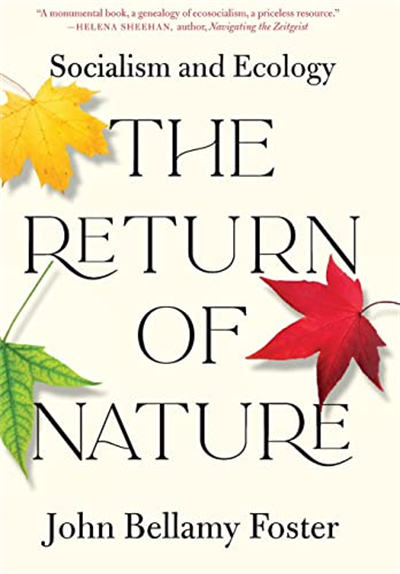
《自然的回歸:社會主義與生態學》(The Return of Nature: Socialism and Ecology)從馬克思和達爾文逝世到上世紀60年代,追溯了有關環境的辯證思維的持續線索。這是一部關于社會主義和生態學共同演進的細致研究,引用了大量的資料,包括恩格斯、"左派達爾文主義者"雷·蘭克斯特(Ray Lankester)和浪漫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這些觀點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者的挑戰。這些學者發展了馬克思生態理論的傳統,主要是植根于對馬克思本人的生態批判思想的發掘。其核心是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概念化闡述,即代謝斷裂理論及其與經濟價值理論的關系。在重建馬克思生態理論的過程中,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和我發揮了主導作用,比如伯克特的《馬克思與自然》和我的《馬克思的生態學》。
在過去的20年里,我們不僅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認識有了極大的擴展,而且還擴展到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破壞的批判,這體現在以下這些人的著作中:齋藤幸平(Kohei Saito)、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 Magdoff)、安德列斯·馬爾姆(Andreas Malm)、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理查德·約克(Richard York)、伊恩·安格斯(Ian Angus)、漢娜·霍爾曼(Hannah Holleman)、德爾·韋斯頓(Del Weston)、埃蒙·斯萊特(Eamonn Slater)、斯蒂法諾·朗戈(Stefano Longo)、麗貝卡·克勞森(Rebecca Clausen)、布萊恩·納波利塔諾(Brian Napoletano)、尼古拉斯·格雷厄姆(Nicholas Graham)、卡米拉·羅伊爾(Camilla Royle)、毛里西奧·貝當古(Mauricio Betancourt)、馬丁·恩普森(Martin Empson)、杰森·希克爾(Jason Hickel)、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很多沒有提到的作者。
阿里爾·薩利(Ariel Salleh)提出了代謝價值分析,將代謝斷裂分析與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相結合。杰森·W. 摩爾(Jason W. Moore)提出了一種世界生態學方法,這種方法源于代謝斷裂分析,但最終走向了后人類主義。薩爾瓦多·恩格爾-迪·毛羅(Salvatore Engel-Di Mauro)寫過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和環境的文章。
在英語世界之外,法國的邁克爾·洛伊(Michael L?wy)、比利時的丹尼爾·塔努羅(Daniel Tanuro)、日本的齋藤幸平和佐佐木隆治(Ryuji Sasaki)、西班牙的馬丁內斯-阿利耶爾(Martinez-Alier)和卡洛斯·索里亞諾(Carlos Soriano)、巴西的里卡多·多布羅沃爾斯基(Ricardo Dobrovolski)、烏拉圭的愛德華多·古迪納斯(Eduardo Gudynas)和南非的維什瓦斯·薩特加爾(Vishwas Satgar)都做了重要的工作。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現在已經傳播到全世界,并影響了社會運動——比如巴西的無地工人運動,以至于很難全部追蹤到。我也注意到中國學者在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與許多思想家建立了聯系,盡管我無法總結那里的發展態勢。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者最熟悉的一部著作是陳學明的《生態危機與資本邏輯》(2017)。
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重要性不斷得到人們的重視。安德列斯·馬爾姆的《化石資本》(2016)、齋藤幸平的《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2017)和我的《自然的回歸》(2020),獲得了著名的伊薩克與塔馬拉·多伊徹紀念獎(Isaac and Tamara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就期刊而言,很少有主要關注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期刊。在這方面,由詹姆斯·奧康納創立,現在由薩爾瓦多·恩格爾-迪·毛羅編輯的《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他定期發表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重要文章的期刊包括《每月評論》(本人為編輯)、《歷史唯物主義》(馬爾姆是編委)以及《國際社會主義》(尤其是羅伊爾擔任編輯時)。但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文章出現在大多數社會主義期刊和學術出版物上。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網站是由伊恩·安格斯編輯的“氣候與資本主義”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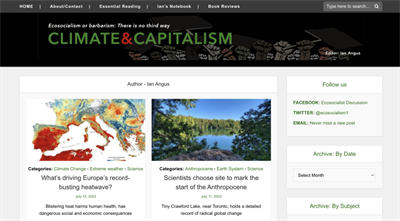
《氣候與資本主義》(Climate & Capitalism)是一本生態社會主義期刊,反映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 圖片來源:網站截圖climateandcapitalism.com
賈可卿
依您的看法,人類與地球的關系是我們最基本的物質關系,因為地球構成了生命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地球這個共同體中,您如何看待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您更傾向于人類中心主義還是生態中心主義的主張?非人類物種是否具有獨立于人類的內在價值,或者它們僅僅具有工具性價值?
福斯特
我們與地球的關系是我們最基本的關系,是人類生存和一般生命的基礎。這是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也是我們的出發點。因此,拒絕以人類豁免主義為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很重要的——這種人類中心主義聲稱,人類追求的目標可以獨立于我們所生存的自然物質世界。這種觀點是不科學的、不合倫理的、非生態的。我們必須認識到:正如馬克思所主張的那樣,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需要與自然進行持續的“對話”。這是我們自己存在的基礎。因此,與自然和地球建立共同進化和可持續的關系至關重要。在這個意義上,生態中心主義意味著否認人類和人類社會與馬克思所說的“自然的普遍新陳代謝”的根本分離。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必須陷入某些非理性的觀點,這些觀點有時與生態中心主義有關。例如,根據所謂的“新唯物主義”(實際上是生命力論的復興,流行于美國學術左翼的一些分支),馬克思被認為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因為他不承認存在的一切——一塊石頭、一團煤、一片云、一個微生物、一朵花、一塊巧克力、一組塑料恐龍——都是與人類存在于同一層面上的“非人類的人”(non-human person)。這是蒂莫西·莫頓(Timothy Morton)和簡·貝尼特(Jane Bennett)等人提出的實際主張。莫頓說,由于拒絕把在生產過程中被消耗殆盡的煤炭看作“非人類的人”,馬克思所受到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指控被證實。顯然,沿著這些極端的生命力論(“新唯物主義”)路線走下去會陷入荒謬。
的確,馬克思有時被像蒂莫西·莫頓這樣的思想家批評為“人類中心主義”,僅僅因為他只關注人類物種的異化——就好像他在對階級社會的批判中,在闡述人的存在及人與自然的異化時,否認了其他非人類物種的存在。然而,事實是,馬克思強烈批評笛卡爾式的人與動物的機械分離論,并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辯護,強調人類與自然世界的共同進化關系。他還強調了非人類動物物種與人類在智力上的密切關系,并批評了資本主義生產中出現的對非人類動物的虐待。馬克思在他的整個著作中,強調了自然的人性化和人性的自然化的生態必要性,也就是說,一種取代自然異化和勞動異化的生態結合。
一些環保主義者,如喬爾·科威爾,指責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未能將自然的內在價值納入這種生態結合中。在這里,我們遇到了問題,因為雖然我們可以承認其他實體/存在及其存在的權利,但我們所說的價值觀是基于人類的資質,是我們自己作出的區分。當我們試圖將自然的內在價值與我們自己的判斷分開時,定義內在價值往往只是在兜圈子。馬克思通過他的自然物質的使用價值這一概念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種關于人類和生產的唯物主義觀點,其中包括自然物質的質量和必需性方面。他還指出,我們與自然的聯系不僅僅是通過我們的生產,而且還通過我們對美的認知,也就是審美。
我在與保羅·伯克特合著的《馬克思與地球》一書的導言中提到了馬克思的生態美學及其與自然內在價值的關系。正是在美學中,我們非常感性地與作為整體的自然聯系起來。我認為,習近平最為出色的見解之一,就是在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以“美麗中國”的提法來強化生態文明的概念。也就是說,我們與自然的審美關系以及自然的內在價值被視為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單獨強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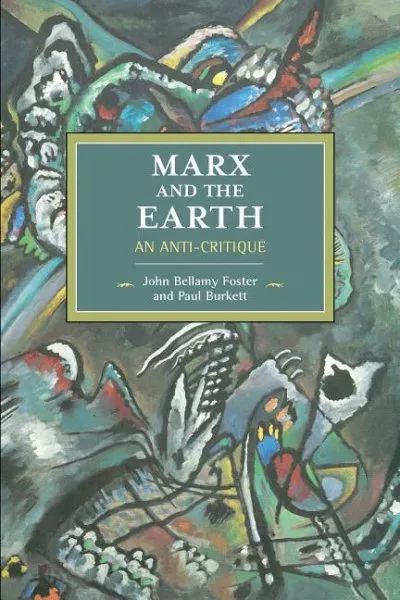
福斯特和伯克特對馬克思思想的生態基礎提出了革命性的理解,證明馬克思關于自然普遍新陳代謝、社會新陳代謝和代謝斷裂的概念預示了現代系統生態學的大部分內容 | 圖片來源:abebooks.com
賈可卿
您以大量的事實恢復了馬克思作為生態學家的本來面目,特別是提出了代謝斷裂理論。今天,馬克思主義生態學已成為社會主義生態學發展的基礎。您說過: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沒有任何意義,除非它與唯物主義的自然觀相聯系。您能否稍微詳細地解釋一下這個觀點?
福斯特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們對歷史和社會分析的貢獻稱為“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這被認為是與“唯物主義的自然觀”相對應的。自然的唯物主義觀念是所有唯物主義哲學的根本基礎,這在西方傳統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馬克思當然是古代唯物主義方面的專家,他的博士論文(包括為準備論文而寫的7本伊壁鳩魯筆記)就是關于伊壁鳩魯(Epicurus)的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自然的唯物主義概念,特別是體現于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Lucretius)的自然的唯物主義概念,是17世紀歐洲科學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礎,這場革命與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皮埃爾·加桑迪(Pierre Gassendi)和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思想家有關。
因此,馬克思在介紹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時,把重點置于人類社會實踐——這是在與唯物主義的自然觀相一致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唯物主義自然觀,歷史唯物主義就失去了一切真實的基礎。因此,自然科學的概念出現在整個《資本論》中。理解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辯證關系,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學和整個馬克思主義都是至關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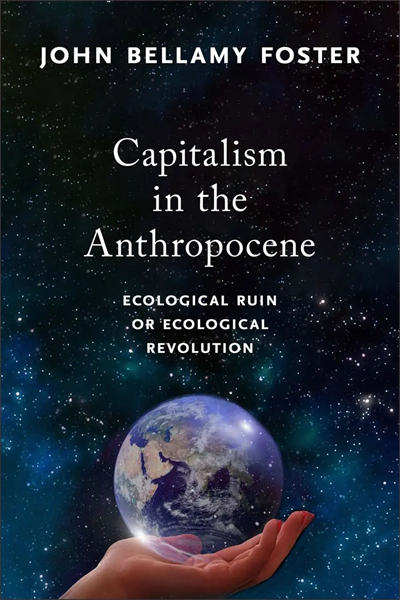
《人類世的資本主義:生態毀滅還是生態革命》這本書中說,人類世的特點是生物循環中的“人為裂痕”。地球系統,標志著一個改變的現實,人類活動現在是影響整個地球的主要地質力量,同時給世界人口帶來了生存危機 | 圖片來源:monthly review
二
生態危機推動資本主義走向終結
賈可卿
您經常在著作中提到“自然資本”這個概念。它與“生態資本”具有相同的含義嗎?在您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批判中,這一概念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福斯特
我在為《每月評論》撰寫的兩篇關于“自然金融化”的文章,即《作為積累模式的自然:資本主義和地球的金融化》(2022年3月)、《保護自然:抵制地球的金融化》(2022年4月)中,對“自然資本”概念進行了歷史的說明。在這些文章中,我解釋了自然資本的概念最初是如何在19世紀早期被激進的反資本主義者用來指代自然資源的使用價值的,這其中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觀點。這種用法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生態經濟學家E. F. 舒馬赫(E. F. Schumacher)和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然而,近幾十年來,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將這一概念轉變為其對立面,將其從基于使用價值的概念轉變為基于交換價值的概念,從而與資本主義經濟完全融合。

馬來西亞婆羅洲島沙巴州美景。2021年10月28 日,馬來西亞婆羅洲島沙巴州的領導人在當地原住民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新加坡空殼公司 Hoch Standard 簽署了一項協議,賦予該公司在200萬公頃的森林生態系統上管理和營銷“自然資本、生態系統服務”的權利,持續一百到兩百年 | 圖片來源:摘自《保護自然:抵制地球的金融化》monthlyreview.org
自然資本從一個反對自然資源商品化的批判性概念,被顛倒為它的對立面。整個自然界被降格為資本主義市場的要素。自然資本成為這樣一種基礎性概念,它擴展了生態系統功能的現有范疇,從而推動了自然資源的金融化。在這方面,從交換價值的角度來看,“生態資本”一詞只是“自然資本”的替代品。為了在分析中弄懂這種轉變的意義,以及為什么有必要與這些傾向作斗爭,我建議閱讀上面提到的文章,尤其是《保護自然》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當馬克思開始使用“自然資本”一詞時,他認識到這個概念在資本主義下有可能被扭曲,因此轉而在《資本論》中強調“地球物質”和“地球資本”之間的區別)。
賈可卿
生態問題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全球范圍內的廣泛認同,而階級斗爭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今天,您是否認為生態危機和生態斗爭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階級斗爭?也許這兩者最好能夠結合起來,但這兩個方面似乎并不總是一致的。
福斯特
我看待這些事情的方式與左派的標準觀點有些不同,與經典的歷史唯物主義更密切相關。您這里所說的傳統觀點,是把階級斗爭等同于狹義的經濟斗爭,從而把經濟斗爭和生態斗爭看成是有很大區別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現實,但一定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處理階級問題的方式。
在許多方面,建立整個歷史唯物主義范式的著作是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部著作首先引入了工業革命的概念,承認了生產的階級基礎和剝削現象,還引入了失業和未充分就業的產業后備軍的概念。這是恩格斯在1843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的部分成果,這本書影響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和哲學手稿》的寫作。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也是一部開創性的流行病學著作,它研究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流行病的起因,認為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促進了“社會謀殺”。恩格斯并沒有從工廠工人的剝削和工作場所的條件開始分析,盡管這占據了該書的一部分內容。他更傾向于從資本主義城市開始分析,包括住房條件、空氣和水污染、各種疾病的傳播以及工人階級高得多的死亡率等。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工作是生態的,甚至超過了經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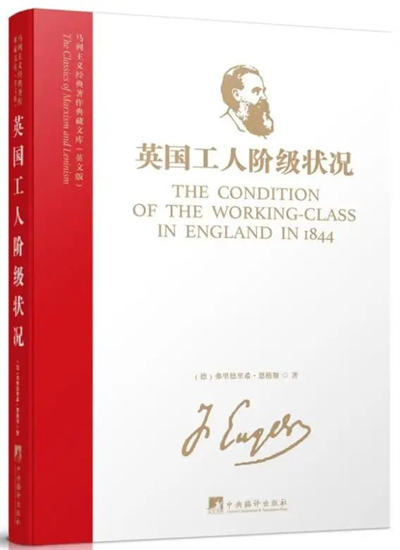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恩格斯1844年9月-1845年3月在英國居住期間寫成的。他研究了英國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說明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特殊作用。他確信,一旦英國喪失了壟斷地位,“社會主義將重新在英國出現” | 圖片來源:中圖網
19世紀早期的工人斗爭是工人階級整個生活條件的產物,而不僅僅是工廠條件的產物,即使他們罷工的威懾力是其階級權力的基礎。恩格斯寫這本書的時候,所謂的“塞式暴動”剛剛在英格蘭西北部發生,就在他居住的曼徹斯特附近。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工人階級的斗爭并不局限于工人在工作場所內的罷工和斗爭,而且也明顯地存在于工人階級物質生活的整個領域。歷史唯物主義常常不得不被簡化為我們可以稱之為歷史經濟主義的東西,而忽略了更廣泛的生活領域。不僅忽略了更大的環境,而且忽略了家庭中的社會再生產條件。
我還認為,只有當階級斗爭擴展到它存在的整個物質基礎時,包括工作場所、環境(包括人造的和自然的)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它才是真正的革命。這也適用于農民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認這一點),盡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不同的階級關系。在這里很明顯,與對工作本身的控制一樣,對土地或自然的控制也一直是個問題。
我相信,我們時代危機的特點是,在這些物質斗爭再次激烈時,圍繞工作和生態環境的階級斗爭也將日益成為一種物質的斗爭。

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大多來自過去的自耕農、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此之前,他們基本上過著田園生活,按照農業生產的節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業革命發生后,大規模圈地運動、大機器生產打破了農業社會的寧靜,往昔的男耕女織生活難以為繼,工人的生活開始發生很大改變 | 圖文來源:中國新聞網
賈可卿
您認為,今天生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環境無產階級。這一階級與傳統的無產階級有哪些不同?您還認為北方國家工人階級的斗爭意識不像南方國家的工人階級那樣強烈,因為他們是全球帝國主義體系的間接受益者。但南方無產階級也可能受益于這一體系帶來的就業、收入等機會。在現實中,他們是否表現出了比北方國家無產階級更強的革命性?
福斯特
環境無產階級的概念實際上是一種理論嘗試:既要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經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概念,也要發展一種適合我們時代的無產階級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人類依賴于他們生存的物質條件和他們在這種條件下發展人類能力的斗爭。但這些物質條件不僅局限于經濟方面,而且還包括生態/環境方面,因此更加包羅萬象。工作場所依然是工人階級權力的中心,但今天的階級斗爭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工作場所的斗爭,還涉及整個環境的斗爭。把物質生存的經濟條件和環境條件分開是越來越難了。如果今天全球南方的人口缺乏食物或水,這主要是由經濟因素還是生態因素造成的呢?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受到經濟的和生態危機與災難的雙重作用,這些問題將越來越頻繁地相互交織。
經濟上的無產階級常常被工會的邏輯和爭取工資、福利的斗爭所束縛。環境無產階級,僅僅是就無產階級物質存在的全部復雜性而言的一種說法,它既涉及工作關系,也涉及全部物質生活條件。這種統一的立場必然更具有革命性,更能抓住時代的問題。如伊斯特萬·梅薩羅斯(István Mészáros)所主張的,真正的革命斗爭需要對社會代謝再生產的整個體系進行改造,但目前這個體系被資本以一種異化的方式主導著。
因此,談論環境無產階級就是談論一個更廣泛的無產階級,把環境問題和經濟問題,把無產者、農民和原住民結合在一起。這還意味著要解決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產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對婦女的極端壓迫。我們已經看到,無產階級環保意識的覺醒正在世界更廣泛地出現,特別是在問題更為嚴重的全球南方,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正在發展的地方。無產階級環保意識的發展將決定人類對已經來臨的全球危機時代作出反應的能力。這種斗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經開始發生了。
就全球南方工人更具革命性的問題而言,這是毫無疑問的。處于資本主義體系邊緣的工人們正面臨著帝國主義的尖銳鋒刃。我們有整個20世紀和21世紀頭20年的時間來見證全球南方各大洲的革命斗爭。革命一直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持續特征,即使在全球北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地帶基本上沒有發生。當然,并非所有這些革命都取得了成功。在任何情況下,它們都面臨著反革命勢力的挑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反革命勢力主要是由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支持的美國。然而,全球南方的無產階級/農民一直在引領著革命的道路,人們因此看到了今天最激進的環境無產階級的斗爭。就對整個歷史發展的理解而言,我最喜歡的書之一是L. S. 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盡管這本書現在已經顯得過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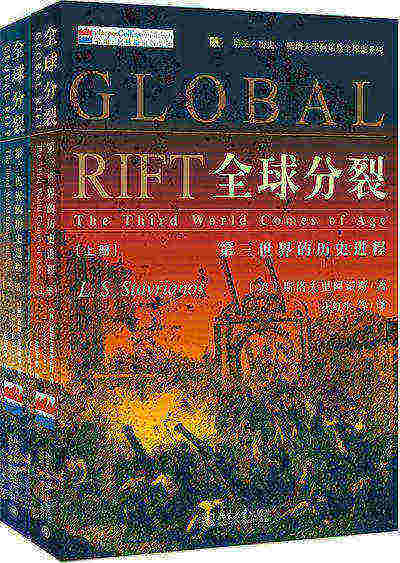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上下冊)》是《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觀代表作 | 圖片來源:亞馬遜
賈可卿
資本主義由于其利潤邏輯,最終只能走上滅亡的道路。您甚至說:“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變得比想象世界末日更容易,事實上,前者可能會排除后者。”但這是不是有些太樂觀了?雖然如您所說,世界陷入了災難資本主義時代,表現為全球生態危機、全球流行病危機、無休止的世界經濟危機等,但資本主義的力量在今天似乎仍然很強大。
福斯特
我之前說過,我們現在正在遠離“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霸權,即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20年前批判性地闡述的概念:“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資本主義末日更容易”。我在2020年3月新冠肺炎大流行開始時首次指出,詹姆遜所說的這種情況現在正在逆轉。在這里,我顛倒了詹姆遜的著名論斷。我說:“突然之間,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比想象世界末日更容易。”我的意思是,面對我們這個時代出現的危機和災難——如經濟停滯和金融化(包括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世界各地法西斯運動的復活以及新冷戰的開始,世界各地的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資本主義已經失敗。看似穩定的社會秩序的普遍崩潰,越來越多地被看作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而不僅僅是反烏托邦(dystopian,指更糟糕的世界——編者注)或世界末日的來臨。
馬克思所說的體現于資本主義異化社會的“悲劇性缺陷”意識,再一次在世界各地人們的觀念中凸顯出來,導致人們日益強烈地要求克服現有的社會關系和生產方式。這并不是過于樂觀,因為它正在我們周圍發生,即使與資本主義斗爭的最終結果遠不確定。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新書名為《對資本主義感到憤怒是可以的》。這與20年前詹姆遜的說法相比,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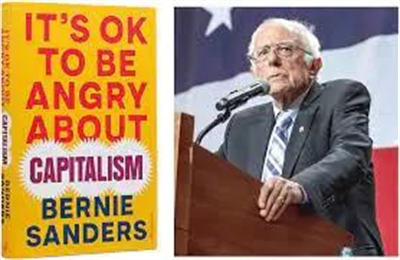
81歲的兩屆美國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在新書《對資本主義感到憤怒是可以的》中指出,美國90%的財富由1%的人口所擁有,并對“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評 | 圖文來源:歐洲時報
賈可卿
根據您的研究和了解,近些年的全球生態運動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帝國主義行徑是否有所遏制?全球北方欠全球南方的“生態債務”是否有所減輕?其中的阻礙因素是什么?
福斯特
如今的全球環保運動發展非常迅速,在抵抗和削弱資本主義勢力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很難說全球北方欠全球南方的生態債務已經減少,因為即使在全球生態危機的背景下,生態帝國主義仍在繼續擴張。
為了了解問題的嚴重程度,我們可以看看在全球碳預算方面全球北方對全球南方的欠帳有多少。科學家已經建立了一個全球碳預算,其目標是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保持在350ppm。一旦確定了碳預算,就可以確定每個國家在人均基礎上的公平碳排放份額。正如杰森·希克爾2020年9月在《柳葉刀:星球健康》雜志上發表的一項重要研究所證明的那樣,如果我們從各國的公平份額中減去它們的實際排放量,我們就可以確定哪些國家在歷史上產生了過量或過剩排放。根據2014年的數據,希克爾能夠確定的是,世界上所有進入大氣的過量二氧化碳排放中,有40%要歸咎于美國,92%要歸咎于全球北方的富裕國家。與此同時,中國和印度的超額排放均為零。全球北方國家的過度排放以氣候債務的形式對全球南方國家構成了巨大的生態債務。

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期間,Action Aid組織提出“富裕國家償還氣候債務”的口號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當然,這還不包括全球北方在過去5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里對全球南方產生的所有方面的生態債務。而且,富裕國家不但不幫助窮國,反而在全面擴張它們的生態帝國主義。漢娜·霍爾曼、布雷特·克拉克和我在2019年7—8月發表于《每月評論》的《人類世的帝國主義》一文中提到了這一點。
三
爭取全球社會主義的生態未來
賈可卿
中國雖是現今世界年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但中國的歷史碳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都遠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盡管如此,中國明確表示要走一條生態文明的道路,并制定了碳達峰和碳中和的路線圖。您也認為,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努力是革命性的。依您的了解,中國在應對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方面,有哪些需要注重的地方?
福斯特
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方法與全球北方/西方的任何方法都完全不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是要改變整個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結構,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向生態友好型轉變,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這種努力正在取得驚人的成果。例如,根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數據,2000年至2017年,中國為全球貢獻了1/4的新增森林面積。中國制定的“十四五”規劃(2021年-2025年)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作為優先事項,并力爭在“十五五”規劃(2026年-2030年)期間即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科技和生產的領導者。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煤炭。盡管燃煤電廠在中國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已經從70%下降到56%左右,但中國在過去兩年增加了煤炭開采,并一直在建設新的燃煤電廠。中國的煤炭消費總量創下了新紀錄,盡管過去10年煤炭消費相對持平。一些人將這解讀為中國在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上的退步。然而,現實遠比這復雜得多,因為中國政府正尋求在能源穩定、能源安全與降低污染和碳排放之間取得平衡。
一些地區的電力短缺和對能源安全的新擔憂,促使政府讓煤炭發揮新的作用。在政府看來,這與長期逐步減少煤炭消費和最終淘汰未減排的煤炭產能(缺乏碳捕獲和封存)是一致的。煤炭發電被視為支撐全國電網的關鍵,盡管中國正在迅速轉向替代性能源。燃煤電廠一旦建成,可以在正常情況下以較低的產能運行,而在需要穩定能源生產時,可以提高產能利用率。因此,重點是將煤炭用作儲備能力。通過這種方式,中國燃煤電廠數量的增加實際上可以支持棄離煤炭的轉變。新電廠還將取代以前效率較低的燃煤電廠(主要影響是減少污染)。由于中國計劃在下一個五年規劃(2026年至2030年)期間達到碳排放峰值,因此有必要采取堅決的措施,在這十年中實現煤炭排放的穩定和減少。
中國持續依賴煤炭的一個重要因素與能源安全有關,而不僅僅是經濟本身。煤炭是中國唯一豐富的化石燃料。隨著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發起新冷戰,并在拜登政府時期繼續推進和加劇,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變得更為嚴峻。在這方面,中國非常清楚帝國主義的整個歷史。西方列強在利用“炮艦”干涉中國并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一個世紀中,對中國實施各種制裁,直到中國革命成功才結束。
重要的是要記住,盡管中國是當今大氣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國,但它對整體氣候問題的國家責任遠小于全球北方國家,后者才是人均碳債務的主要責任方。正如希克爾所指出的,按截至2015年的數據,中國的歷史超額排放量為零(按人均計算),而美國占世界總量的40%。
賈可卿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對生態文明的重視與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沒有什么關系,而主要是來源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天人合一”的思想。您似乎并不這樣認為。在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背景中,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作用是怎樣的?
福斯特
我在《生態文明,生態革命》一文中談到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最初是與一些中國學者的談話,發表在《每月評論》2022年第10期上。在那次談話中,我反駁了杰里米·倫特(Jeremy Lent)的觀點,他認為,生態文明完全源于中國的傳統價值觀,與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無關。對此,我指出,生態文明的概念起源于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最后幾十年,并在當時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者所接受,只是在最近30年里在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因此,試圖將生態文明與馬克思主義分離從歷史上看是不正確的。
然而,我也認為,生態文明的概念是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一部分在中國發展起來的。它受益于中國本土的革命傳統,也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化。這種觀點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生態學和中國文化傳統簡單地分開甚至對立起來,而是反映了它們在許多方面的密切關系,其中包括生態方面的考慮。
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偉大的科學家、西方著名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影響。李約瑟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書的主要作者。我在《自然的回歸》一書中提到過李約瑟。西蒙·溫徹斯特(Simon Winchester)為他寫了一本有趣的傳記,名為《愛中國的人》。杰里米·倫特認為西方文化和科學從一開始就是完全支配和剝奪自然的,與之不同,李約瑟強調:西方的科學人文主義和有機自然主義是在古代伊壁鳩魯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對馬克思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伊壁鳩魯主義和中國的道家思想有某種相似之處。他寫道,“盧克萊修(伊壁鳩魯思想的繼承者——譯者注),(在這方面)和道家有著同樣的語言”。道家的“無為”或不作為的概念不意味著被動,而是指避免“違背自然”的行為。道家的核心思想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也就是創造了東西卻不占有,做出了功績卻不自恃功勞,養育了東西卻不主宰它的命運。所有這些都與辯證唯物主義有著天然的親近感。李約瑟在《四海之內》中說,“有機自然主義是中國的永恒哲學”。因此,中國的思想家們可能會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看作他們“自己的哲學與現代科學相結合,并最終回家了”。
我自己的思想深受P. J. 拉斯卡(P. J. Laska)《〈道德經〉的原始智慧:新的翻譯和評論》的影響。在書中我們讀到:
統治者們的克扣太多了,
糧倉空空如也,
田野叢生著雜草。
在宮廷里,
他們穿著設計精美的華服,
攜帶武器,
貪婪地胡吃海喝,
并且占據了過量的財富。
這就是所謂“強盜的夸耀”:
這絕對不能稱為正道!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并非不了解東方哲學。他對佛教有相當大的興趣。偉大的印度馬克思主義學者普拉迪普·巴克西(Pradip Baksi)探討了馬克思對佛教虛無概念的興趣。

杰克遜合作社(Cooperation Jackson)是倡導可持續社區發展、經濟民主和社區所有權的新興組織 | 圖片來源:housmans.com
賈可卿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存在為人類可持續發展而進行的實踐斗爭。您在著作里提到美國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遜合作社(Cooperation Jackson)正在從事一個革命性項目,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未來的一部分。能不能介紹一下這個組織的活動或者其他類似的組織?
福斯特
在2002年7月-8月《每月評論》關于《社會主義與生態化生存》的特刊中,我們關注的問題是:在氣候變化導致環境破壞加速的情況下,社區如何在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以求得生存。在關于這個問題的介紹中,布雷特·克拉克和我提到了一個這樣的社區組織:杰克遜合作社。
杰克遜合作社不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或資本為可持續發展而斗爭的一種方式,而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的合作社聯盟。它由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領導并適應這些群體的需求,是在這個國家和工人階級中受種族壓迫最嚴重的人群中產生的。他們強調可持續發展、社會正義以及向環境保護和集體需求的合理過渡,最初是源于西班牙蒙德拉貢(Mondragon)實驗的啟發。
我們認為,杰克遜合作社是資本主義社會毛孔中代表著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的“前線社區”的眾多組織之一;代表著無產階級走出野獸肚腹般的環境的方向。雖然目前規模不大,但這些運動構成了革命的希望和行動的島嶼,預示著另一種可能的未來。
賈可卿
您在一系列著作中描述了核冬天的可怕場景。如果真的出現熱核戰爭,全球氣溫可能會急劇下降,對地球上的生命造成滅絕性后果。俄烏沖突以來,世界將注意力轉向核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也就是從碳滅絕轉移到核滅絕。您如何看待核戰爭的可能性?
福斯特
這不是一個“從碳滅絕到核滅絕”的問題,而是我們面臨的兩種密切相關的人類滅絕的問題。加速的氣候變化或全球變暖,是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中,導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結果。全球熱核交換反應以相反的方向運行,通過向環境釋放核爆炸的煙塵而產生核冬天,這幾乎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蘇聯和美國的氣候科學家差不多同時了解了這兩個過程。今天,我們正面臨著兩種可能的滅絕現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氣候變化造成的世界環境不穩定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全球對能源資源的競爭,加劇了核超級大國之間的沖突,從而有可能出現核冬天。
當烏克蘭危機在2022年升溫時,我清楚地意識到,在這場沖突中,對整個人類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代理人戰爭正在將核超級大國推向全球熱核反應的邊緣。然而,即便是左派也沒有清楚地認識到這其中的真正危險,因為大多數人在1991年蘇聯解體后就不再關注核戰爭計劃,并長期相信“相互確保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簡寫為MAD)是一種絕對威懾。
偉大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20世紀80年代歐洲核裁軍運動的領導人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曾寫過一篇有關核戰爭(和環境破壞)的危險的文章:《關于滅絕主義的注釋》。受他的啟發,我在2022年5月的《每月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21世紀生態與和平運動的“滅絕主義注釋”》。
這篇文章圍繞兩個主題展開:
(1)21世紀氣候科學研究進一步證實了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關于核冬天的分析。如果由于熱核反應造成100個城市發生大規模火災,會導致大量煙塵進入大氣,太陽輻射將被阻塞,全球平均氣溫將會下降,達到在幾年內殺死地球上幾乎所有人類的程度。
(2)蘇聯解體后,美國關于核武器發展的辯論導致了“最大主義者”對“極簡主義者”的勝利。這形成了對反制武器的一致追求,旨在為美國提供“核優勢”或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通過在另一方的核武器發射前將其斬首,并運用反彈道導彈系統將其剩余核武器清除——即使是對于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主要核大國。

隨著冷戰的結束和世界發展日新月異,當今世界很少有人會考慮“核冬天”的問題 | 圖片來源:搜狐
2007年,美國外交和軍事機構宣布,美國即將實現全球“核優勢地位”。這意味著美國的戰略核姿態不再受到“相互確保毀滅”概念的限制,而是越來越多地傾向于核優勢地位或首次打擊能力——這是一種危險的幻想,但它越來越多地推動了華盛頓的政策,并導致近年來美國軍事攻擊性的增強,特別是在美國霸權地位下降的背景下。例如,美國認為中國的核潛艇編隊在美國的首次打擊中無法生存,因為中國還不能充分降低潛艇的噪音水平以避免被發現(盡管近年來在這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俄羅斯和中國的導彈發射井也越來越容易受到更精確的導彈瞄準,甚至是非核導彈的攻擊。所有這些都鼓勵了長期受到“相互確保毀滅”限制的美國的好戰性,將世界危險地推向核戰爭。美國試圖努力減緩其霸權的衰落——特別是由于中國的崛起,進而實現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的(不可能的)目標。自不必說,俄羅斯和中國一直在采取行動,如發展高超音速導彈。由于所有這一切,世界和平運動的復興是一項緊迫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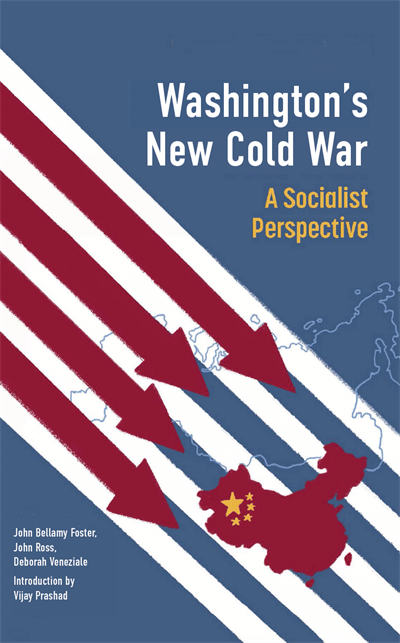
《華盛頓的新冷戰:社會主義視角》認為,美國最新的一系列軍事冒險行為的目標仍然與以往一樣:維護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 | 圖文來源:Monthly Review
賈可卿
我們注意到,您最近與其他學者合作出版了一本新書《華盛頓的新冷戰:社會主義者的視角》。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其中的主要內容嗎?
福斯特
那本書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和三大洲社會研究所聯合出版,由三篇論文組成:上面提到的我寫的《21世紀生態與和平運動的“滅絕主義注釋”》,以及兩篇關于新冷戰的文章。這兩篇文章都是我們首先在中國的《觀察》發表,然后在每月評論網上發表的:一篇是羅思義(John Ross)的《是什么推動美國日益增加軍事侵略》,另一篇是黛比·韋內齊亞勒(Debbie Veneziale)的《誰在領導美國走向戰爭》。維賈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為這本書寫了序言。
書中的文章描述了美國在引發新冷戰中的角色。根據美國國會檔案辦公室的數據,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對其他國家進行的軍事干預/戰爭超過了其此前的整個歷史。它擴大了北約,現在幾乎包圍了所有原華約國家和原蘇聯地區的領土。這種擴張導致了現在的烏克蘭危機。與此同時,華盛頓宣布中國是其頭號安全威脅,因為中國的增長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或以美國(以及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日本的“三位一體”)為基礎的全球權力體系構成了挑戰。
美國一直就臺灣問題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國際公認的——美國也承認——中國的一部分,但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采用了不同的制度。根據一個中國的政策,北京的長期目標是實現臺灣海峽兩岸人民的統一,但這被美國扭曲成北京將要發動“侵略”的證據和潛在戰爭的原因。拜登政府打算將“駐臺”美軍增加4倍。美國目前在中國周圍有400個軍事基地——這通常被視為針對中國的一個巨大套索。但中國的立場是: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美國無權干涉。
在美國經濟霸權衰落的背景下,華盛頓堅持單極世界理念,擴充軍事集團以對付中國和俄羅斯,拒絕以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為代表的多極化發展。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正在被武器化,被用以制裁俄羅斯和中國,以及所有其他世界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的國家,而美歐日“三位一體”繼續尋求在全球南方三大洲行使其帝國主義的統治權力。因此,世界正處于危及人類生存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中國的回應是在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這是迄今為止對世界整體安全(包括所有國家的安全利益)作出的最全面的承諾。在西方,這種安全承諾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可以追溯到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論永久和平》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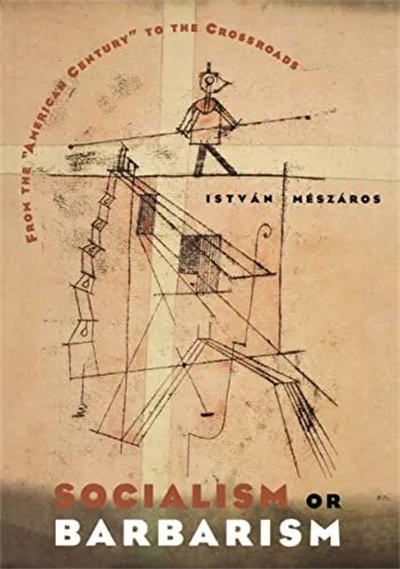
伊斯特萬·梅薩羅斯的《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從“美國世紀”到十字路口》| 圖片來源:Abebooks
這是一個大抉擇的時代。世界要么朝著社會主義和世界和平的方向前進,要么朝著資本主義(包括法西斯主義)和滅絕主義前進。最值得贊揚的是伊斯特萬·梅薩羅斯,他在2001年的《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從“美國世紀”到十字路口》中強調了這一點。在那里,他寫道:“如果我必須修改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關于我們現在所面臨危險的戲劇性話語,我會給‘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加上如下修辭:‘野蠻已算我們幸運’。因為人類滅絕是資本之危險發展歷程的終極伴生物”,而現在我們正面對的“可能是帝國主義的最危險階段”。
(文章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4期)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