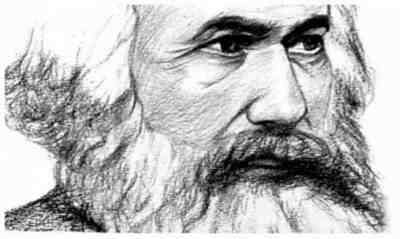無論西馬是馬克思還是鹿克思,這一點其實并不重要。因為西馬的主張者及其擁躉,是學術分析的路子,解釋權的邏輯閉環對他們而言是毫無必要。對于尚未掌握政權的在野者而言,他們的使命就是不斷提出執政者難以接納的提議,然后通過被否決來實現自身的神圣性。
在傳統的蘇馬環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為政治服務,兩相對比,西馬和新馬確實在一定程度回歸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分析,實事求是地看待問題。但是,隨著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西馬”更像是普通的社會哲學學術研究,不再提出激進變革社會的方案和嵌入歷史風波了。
英國新左派的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中,提出了“新左派”的概念,這與斯大林上臺后西方特色的“西馬”是相吻合的概念,或者準確說,這兩個概念具有親緣關系,是相伴而生的姊妹。這是他們對考茨基、普列漢諾夫、伯恩斯坦、列寧、盧森堡、葛蘭西等先輩的重新發現,乃至對一致的自然主義或人文主義進行了反叛,亦即社會主義不只是建構秩序,更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也非是自然反映論的旁征博引,更是一種創造新世界的趨向。
然而,西馬被視為正確的科學社會主義,甚至可能比之蘇馬更為危險。從“西馬”的起源來看,其主張一開始便是用于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否定的理論工作上的。就在1955年,那位“知覺現象學”的哲學家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歷險》首次提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針對“列寧主義”的開創性進行批判,并且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對馬克思本身做了切割,分化出了辯證的、經過觀念論訓練的馬克思和“自然主義”的馬克思。歸根結底,梅洛龐蒂是要用現象學的方式去揚棄辯證法(即使他的這種批判也歸于一種歷史的辯證運動),目的是要摧枯拉朽地打倒馬克思主義。
綜觀看待,西馬是一種和“戰斗唯物主義”相對立的意識形態,也是一個整個西方與蘇東相對抗的地域象征,屬于是不以馬克思主義自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造成巨大思想沖擊的思潮(蘇之砒霜,美之舒爽)。
不過,西馬推究到極致,也終歸是正治領域的斗爭,即使遠遠那么定睛一瞧,那么慈眉善目。可歷史總會告知世人,左良玉也是會慈眉善目地說,“老鄉,借你的人頭一用”。譬如,葛蘭西會講“向人類的外部去尋找現實和實在,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學地理解實在。……沒有人,宇宙還有什么意義”。這些話在當時的語境里,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可一旦變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語錄,就難說會不會對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產生不良影響了。畢竟20世紀末期,有位叫做戈爾巴喬夫的“地圖頭”,他也喜歡說這些人啊、人類文明啊之類的口頭禪。于是,歷史就出現了極為詭異的一幕——“沒有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
1877年,伯恩施坦也是四處宣傳這種與上文所述相類似的觀念,號稱要用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觀點來代替社會主義的思想。甚至,他還要求放棄階級斗爭,取消革命,鼓吹“全民黨”(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的“全面”的黨),可謂是修正主義的面目暴露無遺。西馬相對比,更為聰明了一些,他們要利用社會科學和哲學的權威來做事。如果出了差錯,那么這口黑鍋得甩到教育體系和社會研究方面,西馬繼續裝作無辜的旁觀者。
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端起碗大快朵頤、放下碗就罵娘的西馬叛徒。確切講,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進過窄門,又談何變成猶大呢?著名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法蘭克福的“大孝子”)哈貝馬斯就曾指出,馬克思主義的規范性基礎是不明確的。什么是規范性呢?其實沒有什么高深的內容,就是講你應該如何如何做事,這也就是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所講的“應然性”。所以,哈貝馬斯的意思是大家都沒想拋頭顱灑熱血,不過就是像生物學家做玻片一樣,做做研究,最多妄圖青史留名而已。學術混子都能研究馬克思,那可不就是缺乏規范性嘛。
可如此表述,也不究竟。因為社會科學是一門涉及方方面面的精細學問,除了要有“規范性”的理論,還要有“實證性”的理論,也就是要對做事的進程進行描述。規范主義與實證主義,是一對互相成就的矛盾,不可能隨意地全盤打倒。換言之,西馬的理論特性就是一種實證分析,無論他怎么在“馬克思主義是哲學還是科學的問題”這個“科爾施問題”面前標榜自己,中世紀負責經院哲學的那批人肯定也會說:“這味我熟”。
又譬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雖然提出了許多激進的主張,但當激進的學生找上門來,他人卻玩起了奇妙的躲貓貓。至于阿爾都塞學派的阿爾都塞,如果在所謂的大革命到來前不要瘋癲,就更為絕妙了。
再看看其他的西馬又如何。哲學家薩特把列寧顛倒過來的黑格爾哲學再度顛倒回來(列寧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顛倒成唯物主義),也就是再度投入歷史唯心主義的懷抱,“不間斷的精神運動”的提法無疑是對“無意識”的淺顯分析。他認為辯證運動意味著主體自身一分為二,從自身樹立起對立面來認識自己,這無疑是對斗爭的曲解。他只是通過自欺,樹立了一個永遠存在且永遠達不到的存在方式。換言之,比起為了人民群眾的福祉,薩特更在乎自己的學說如何邏輯閉環。
本雅明對馬克思的解釋則比薩特更為極端,他幾乎將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重塑,他那種“人必然在欲望與塵世當中沉淪”的情調貫徹始終,他的“革命”是彌賽亞主義試圖創建的一種新型時間,即彌賽亞時間,悖于現代啟蒙理性所依賴的線性時間,這是實現與未實現之間的空白區間。本雅明的歷史唯物主義轉向了一個永遠的危機時刻,但又絕非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可也徹底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性(主觀能動的),顯得只是與基督徒相似地被《保羅書》的起源性真理事件的綁定。
這種西方馬克思主義只是在大學里作為一種學說和思潮而存在著,出版的大都是一些純理論和文化方面的著作,少有斗爭性指向明顯的表述。總歸不值得迷信這些主張,畢竟,有信無證,雖不落惡果。可也是終不得正果。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