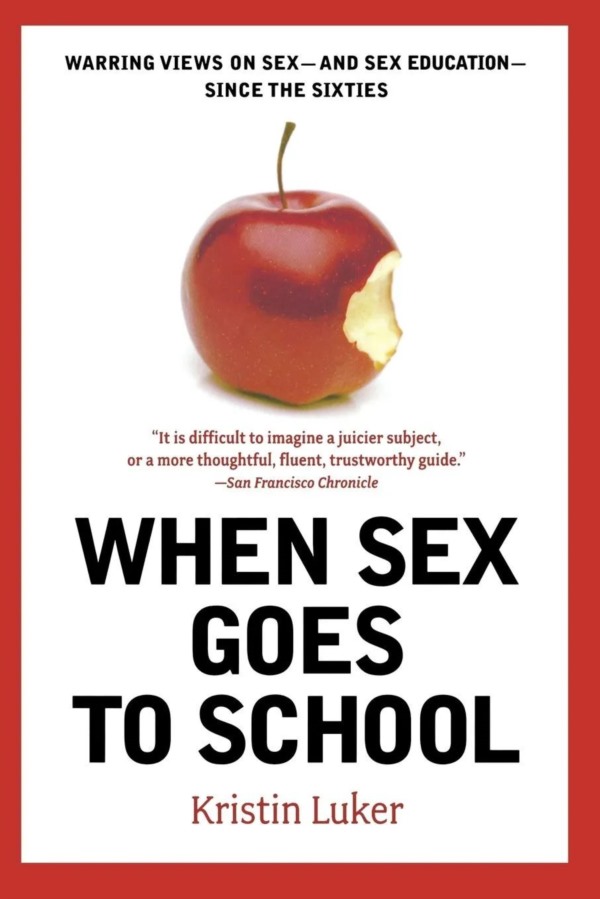[譯者按]
斜下的夕陽點燃著怒火,倉促的應變時間和癱瘓的公共交通未能阻扼無盡潮涌的人海。6 月 24 日下午 5 點半,筆者所在的波士頓市古老的市中心已充斥人群和條幅,以抗議當天上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決議。支持墮胎權利的活動者嫻熟地封鎖街道,引導人群,高喊「我的身體我做主 (My body my choice) 」、「無問教會,無問國家,女性自決 (Not the church, not the state, women will decide their fate) 」口號,間或有戰鼓擊節,風琴合鳴。而不同組織展板的迥異色彩,抗議者條幅措辭選取的微妙差異,以及人群中不時發出的異議和糾正,也揭示著這場運動的多元性。八點,人群才在籠罩的夜幕下開始散去,而這將是一場未來可預見的巨大運動動員的序曲。
困惑,而非憤怒,是筆者作為墮胎權利毫無歉疚的支持者的第一反應。為何已有近五十年之久的對墮胎權的憲法保障仍會一夕傾覆?反墮胎運動的動機和動員能力究竟來自哪里?而女性主義在一場敗局后又將如何再組織?這些問題無論是對墮胎權和其它女性權益的支持者,還是對社會問題的研究者來說都有其意味,而回顧相關問題的歷史和研究文獻則將不無裨益。
本文從《美國女性社會運動的行動主義牛津手冊》 (The Oxford Handbook of U.S.Women's Social Movement Activism) 譯出,以饗讀者。原文著于 2017 年,自無法涵蓋近年來的法律變化和新的研究成果。且原文美國政治法律術語和組織名稱紛繁,筆者限于學力,難免有較多錯漏,還望讀者指正。
[摘要]
本章探討美國的女性主義者爭取墮胎和生育權利的歷史,并分析這些議題為何能持續動員相反運動的參與者。符號政治 (Symbolic politics) 是沖突長期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墮胎與生育權利則關乎對性別和性存在的關切;運動 / 反運動的動態變化也有助于保持沖突的活力:當一方贏得戰果,另一方則獲得動員的促力,彼此開始新一輪的爭斗;女性主義的策略和框架也一直在適應政治和文化環境的變化,隨著不同群體(如年輕女性、有色人種女性)參與組織,她們為爭取墮胎和生育權利的斗爭貢獻了新的框架和策略。
關鍵詞:墮胎、生育權利、女性主義、反運動、性別、性存在
長期以來,在美國和許多國家,墮胎與生育權利一直是女性主義的關鍵議題。許多在「第二波」女性運動中活躍的女性即圍繞墮胎以及生育控制進行動員,而對這些權利的威脅則仍激勵著許多年輕的女性主義繼續參與當代的運動。本章將探討兩個主要問題:首先,墮胎和生育權利議題為何能持續動員參與者?其次,女性主義者如何有效地改變其戰略——包括沖突目的、戰術選擇和議題框架,以回應對生育權利的新挑戰?即使本章的重點是生育權利運動,我們也研究了反墮胎運動和更廣泛的反女權運動,因為這些反女權運動影響了女權運動的動員能力和戰略抉擇。鑒于墮胎具有深刻的個人重要性和象征意義,我們也研究了墮胎議題對身處沖突兩端女性的激勵作用。對于如何解釋某一議題的動員能力和戰略抉擇,我們將介紹部分關鍵的理論觀點,其中包括符號政治。這一概念經常被用于研究墮胎議題、社會運動動員的原因、策略抉擇、運動/反運動的動態變化,這些均對理解圍繞墮胎的沖突至關重要。
我們首先介紹美國圍繞墮胎和生育開展的女性運動的歷史,并重點關注動員和戰略隨時間的演變;然后,我們研究為何墮胎對雙方而言都仍是個重大的議題;最后,我們評估墮胎和生育作為一個動員議題的持續重要性,以及女性運動調整其戰略的能力。
一、美國圍繞墮胎與生育的女性運動
1早期努力
19世紀出版物《Le Rire》的一幅插圖,一個女人在丈夫準備上床時祈禱免于意外懷孕。(圖源: Historia/REX/Shutterstock)
長期以來,女性對身體自我控制的權利一直是女性主義的基本原則,但運動的需求和策略、以及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則隨著時間推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最初在美國各州,遵照英國普通法, 女性能感覺到胎動的階段前的墮胎都是許可的。19 世紀,試圖實現職業化的醫生與反淫穢運動 (anti-obscenity) 運動的活動家聯合起來,將實施墮胎者逐出醫療領域。由于尚無墮胎權利運動,至 1900 年,墮胎在所有州均被定為非法 (Mohr 1978; Reagan 1997)。19 世紀的女性主義者確實開始主張「自愿母職」的權利,但她們并不贊成避孕和墮胎。在女性缺乏經濟獨立的時期,她們需要男性在婚姻中的承諾,因為已婚女性的財產和收入都要依靠丈夫。高等的教育機會和高薪工作對婦女來說并不開放,也無法獲得。在獲得選舉權之前,女性沒有政治代表,因此也沒有能力修訂使她們不得不依賴丈夫的法律。正如琳達·戈登 (Linda Gordan 2007) 所解釋的那樣,當時的女性主義者不贊成避孕,因為她們擔心使用避孕藥具會導致婚外性行為,而這將導致男性而非女性獲得更大的自由。因此,她們主張女性有權拒絕與丈夫發生性關系,也反對婚內強奸合法化。只有在經歷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如城市化和工業化導致女性參與勞動市場之后,女性運動才擴展了她們對生育權利的看法。
隨著女性在 20 世紀越來越多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她們開始組織起來,支持避孕和墮胎。瑪格麗特•桑格 (Margaret Sanger) 創造了「節育 (birth control) 」一詞,并在1916年開設了第一家節育診所,倡導避孕,但反對墮胎。許多節育倡導者的動機是希望改善女性的經濟狀況,包括社會主義者,他們認為節育可以幫助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能夠限制自己的家庭規模。部分人還支持爭取女性的性平等,而另一部分人則擔心性放縱以及與母職相關的女性地位的下降 (Gordon 2007)。艾瑪·古德曼 (Emma Goldman) 和瑪格麗特•桑格等女性主義者則認為,節育將使女性從強迫母職中解放出來,并使她們能享受性生活 (Reagan 1997: 36)。到了1960年代。女性主義者在支持節育、墮胎和女性的性自由方面已團結一致。她們倡導女性能獲得避孕和墮胎,并將它們視為更廣泛的女性健康運動的一部分,建立其新的女性健康診所,旨在使女性能夠對她們的身體和生育做出決定 (Morgen 2002;Ruzek 1978)。
2圍繞墮胎之戰
伴隨著女性主義者和計劃生育倡導者的支持,1960 年代出現了一場墮胎合法化的運動,該運動的各種策略受到 1960 年代其它運動和部分選民的立法游說和訴訟經驗的影響 (Staggenborg 1991)。墮胎運動 (abortion movement)——其中「運動」一詞是墮胎合法化前產生的叫法,得到了一些全國性組織的支持:全國女性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簡稱 NOW)在1967年支持廢除反墮胎法,全國廢除反墮胎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Repeal of Abortion Laws,簡稱NARAL)則在1969年成立。然而這些組織當時并不強大,該運動依靠的更多是基層的草根活動家。女性解放主義者則通過演講和其他公共集會,促力改變社會對墮胎的認識。鑒于人們需要安全、可負擔和富有同情的可選項,盡管有面臨刑事指控的風險,女性解放主義者仍在采取許多直接行動策略 (direct-action tactics),如提供墮胎轉介,有時還直接提供墮胎服務 (Kaplan 1995)。墮胎運動的參與者還包括「親選擇」的宗教活動家,如神職人員咨詢服務 (Clergy Consultation Service)。這是一個在1967-1973年期間在許多州運作的墮胎轉介服務,由天主教修女和神父、基督教牧師和猶太教拉比組成(Carmen和Moody 1973)。許多見識了非法墮胎惡果的醫生,也參與了幫助女性墮胎,并在立法后仍不顧風險提供墮胎服務 (Joffe 1995)。活動者還通過現成的渠道,包括州立法機構和法院,向州立法機構提出廢除反墮胎法案的提請。1970 年,由于活動者的游說努力,紐約州和其它三個州改革了各自的墮胎法,但立法進展仍很緩慢。墮胎運動在進行立法游說的同時還追尋法律戰略。1973 年,在運動的積極分子提起了許多案件,并在羅訴韋德案 (Roe v. Wade) 中提交了許多支持墮胎合法的「法庭之友」 (Amicuscuriae) 文書后,最高法院最終將墮胎合法化 (Faux 1988)。
1973年4月,反對者和支持者在新澤西州特倫頓的州政府大樓外,在最高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作出裁決幾個月后。
反墮胎運動是針對 1960 年代的墮胎權運動而出現的,墮胎合法化使許多反墮胎者感到憤怒,反墮胎運動又隨之開始活躍起來。即使支持墮胎的運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在羅訴韋德案后,它還變得更為組織化,因為反墮胎者迫使墮胎運動在新的賽場上捍衛新贏得的墮胎權 (Staggenborg 1991)。在墮胎合法化后,反墮胎運動將墮胎沖突的焦點從各州轉移到國會,立即開始推動憲法修正案以禁止墮胎,如果無法做到,則通過聯邦立法來禁止墮胎和禁止聯邦為貧困女性墮胎提供醫療資助。為了應對這些威脅,墮胎權利團體發展了更正式的組織結構使他們能參與國會的游說策略 (Staggenborg,1988)。NARAL 改名成全國墮胎權利行動聯盟 (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并開始在華盛頓雇用專員;墮胎權利宗教聯盟(Religious Coalition for Abortion Rights,簡稱 RCAR),則在全國范圍內通過州級的分支機構組織了「親選擇」(pro-choice) 的宗教團體。墮胎權利的聯盟也得到了全國性的加強,因為計劃生育協會 (Planned Parenthood) 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ACLU) 等組織都對該運動給予了支持。
1976 年,反墮胎運動贏得了第一個重大勝利,國會通過了《聯邦醫療補助撥款法》(Medicaid appropriations act) 的海德修正案 (Hyde Amendment),禁止聯邦資助墮胎。這當然鼓舞了反墮胎者,但它也導致了支持墮胎運動的擴展。海德修正案的通過和 1970 年代末新右派可見的組織活動為墮胎權利運動提供了強大的促力——正如羅訴韋德案刺激了反墮胎運動一樣。在組織的角度講,運動和反運動的悖論是,一方的勝利有助于動員對立的一方。運動和反運動都繼續發展演化,并采取新的策略來應對其反對派的進展(Meyer和Staggenborg 1996)。
在國會輸掉關于海德修正案的關鍵戰役后,許多女性主義者在基層圍繞墮胎和生殖權利問題組織起來。墮胎診所是一個主要的沖突場所,因為女性主義者努力保護它們免受反墮胎者的攻擊 (Blanchard 1994;Ginsburg 1989;Simonds 1996)。1978 年, 全國性組織「生育權利全國網絡」(Reproductive Rights National Network,簡稱 R2N2)成立,旨在聯結在地生育權利團體。這些團體是針對新右派的崛起而組織的,他們認為新右派不但威脅墮胎權,也威脅整個女性主義。除了保障墮胎合法,生育權利團體還希望擴展「親選擇」運動的框架和目標:她們主張女性有權獲得許多條件,包括醫療保健、兒童看護和就業保障,以使是否生育成為女性真正的自我選擇 (Staggenborg 1991)。因此,這些針對墮胎權利的新威脅,激起的義憤正激發著生育權利運動,而這一運動則是更廣泛的女性健康運動的延續。
運動 / 反運動的動態演變持續塑造著墮胎相關沖突,每當一方贏得戰果,另一方就會動員作為回應。作為一個政府權力分立的聯邦制國家,美國將可能在墮胎等議題上面臨對立運動之間的長期沖突(Meyer 和 Staggenborg 1996: 1637; O'Connor 1996)。哈夫曼 (Halfmann 2011) 闡明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正是政治制度的不同使美國的墮胎相關沖突比英國和加拿大更為激烈。在美國,有許多不同的戰場可以爭斗,包括包括立法機關和不同級別的法院。因此,關于墮胎的沖突似乎能夠無限期地持續下去。1983 年,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重新肯定了羅訴韋德案,反墮胎立法在國會被擊敗。這些挫敗使反墮胎者尋求新的策略,包括直接行動。1989 年,最高法院對韋伯斯特訴生殖健康服務案 (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進行裁決,允許對墮胎服務進行一些重要的限制,成為反墮胎運動的一項戰果,并激怒「親選擇」的活動者。1992 年,最高法院在賓夕法尼亞州東南部計劃生育協會訴凱西案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 中允許對墮胎服務施加更多限制,但它未能如墮胎反對者所希望的那樣推翻羅訴韋德案。這一決定在州一級開辟了新的戰場,因為反墮胎者有機會對墮胎服務實施新的限制。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大部分圍繞墮胎的斗爭是在街頭進行的,因為反墮胎者試圖封鎖墮胎診所,而墮胎權利活動者則采取了旨在保護診所及其主顧的策略 (Wilson 2013)。所謂的「營救活動」(Operation Rescue),即 1980 年代末開始的對北美墮胎診所的大規模封鎖,也許是反墮胎街頭行動的最引人注目的形式,這反過來又刺激了墮胎支持者的基層行動作為回應(見 Ginsburg 1993;Johnson 1997;Williams 和 Blackburn 1996)。墮胎權利團體爭取頒令和法律,以保護診所不受反墮胎抗議者的影響。他們隨之采取自己的法律策略,以言論自由權為由挑戰對墮胎的法律限制。新的法律判例仍不斷擴展有關墮胎的運動/反運動間的沖突 (Wilson 2013)。1994 年,聯邦層面通過了《自由進入診所法》(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 Entrances,簡稱 FACE),使墮胎診所被封鎖的情況急劇減少 (Wilson 2013: 105)。對地方法規的法律挑戰也一直在持續。2014 年,最高法院以憲法第一修正案為由推翻了 2007 年馬薩諸塞州的一項法律,該法律原本在墮胎診所周圍設立了 35 英尺的緩沖區(Liptak 和 Schwartz 2014)。由于反墮胎運動的這項戰果,墮胎診所所在地的街頭爭斗可能會再次加劇。
圍繞墮胎之爭也在各州的立法機構中繼續進行,法庭上出現了更多的爭斗。德克薩斯州和其它州曾試圖要求墮胎診所達到醫院式的手術標準 (hospital-style standards for surgery),從而迫使許多診所關閉。2014 年秋,聯邦法官允許德克薩斯州的限制墮胎措施生效,關閉了該州 80% 的診所,大大減少了墮胎的可能。最高法院后來阻止了這項法律,允許一些診所重新開業 (Eckholm 2015)。2016 年,墮胎權利運動贏得了一場重大勝利,最高法院推翻了德克薩斯州的法律,認為它對婦女的墮胎權造成了 「過度的負擔 (undue burden)」,而「造成過度的負擔」則在 1992 年的凱西案裁決中被禁止 (Liptak 2016)。這項裁決為全國各地通過的其他限制墮胎的法律帶來了潛在的挑戰,具體來說,該項裁決禁止了對墮胎診所提出必要條件,如要求具有醫院級別的設施,這些必要條件帶來了更大的成本,卻沒有保護女性的健康。此外,該裁決也可能支持挑戰其它限制墮胎的法規,例如對醫療墮胎的限制 (Eckholm 2016)。
紀錄片《大法官金斯伯格RBG》劇照
在 2016 年的最高法院的裁決之前,各州立法機構通過的限制墮胎法規數量一直在急劇上升,使女性更難獲得墮胎。在 2001 年至 2010 年期間,州級通過了 189 項限制墮胎法規(Boonstra 和 Nash 2014),而在 2011 年和 2014 年之間則急劇增加到 231 項 (Guttmacher Institute, January 5, 2015)。這些反墮胎的措施包括延長等待期、規定年齡限制、禁止聯邦醫療補助支付、限制保險范圍、父母知情同意、強制性超聲波檢測以及醫生必須向病人宣讀文本,而被宣讀的文本不準確地將墮胎與乳腺癌、心理疾病或自殺進行關聯 (Pollitt 2014: 24)。2015 年,亞利桑那州長首次簽署了一項法律,要求醫生告知客戶她們會經歷藥物流產的副作用 (Rojas 2015)。在俄亥俄州,立法者批準將資金用于「危機懷孕中心 (crisis pregnancy centers)」,這一中心勸說女性不要墮胎,而這些資金原本則計劃用于援助貧困家庭(Pollitt 2014: 24)。堪薩斯州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法律,限制最為常見的孕中期(四個月到六個月)的墮胎措施(Eckholm 和 Robles 2015)。2015 年夏,一個反墮胎組織開始在網上發布經過編輯的視頻,指責計劃生育協會從出售胎兒組織中獲利,在國會的共和黨人則作出響應,提案取消對計劃生育協會的聯邦資助的法案,而這些資助本大多用于一般性的健康保健服務 (Calmes 2015)。
3瞄準弱勢群體
對墮胎權多策并用的攻擊,既旨在限制墮胎的提供者,也旨在定罪墮胎的主顧,且往往針對弱勢群體,如青少年、低收入女性和有色人種女性。由于羅訴韋德案的裁決中主張憲法賦予的人格權不包括胎兒,為了反制,反墮胎團體試圖在限制墮胎立法中插入關于人格權的用語。2010 年, 反墮胎組織美國人格權協會 (Personhood USA) 在科羅拉多州表決了第一個 「人格權修正案 (personhood amendment)」。盡管這一嘗試宣告失敗,且反向動員了許多墮胎的支持者,但反墮胎運動的倡導者一直在其它州推行這一策略。三十八個州都有關于殺害胎兒的法規(盡管有些州禁止法律懲罰女性),在大約十五個州,懷孕期間使用毒品和酒精被視為「虐待兒童」(Reitman 2015)。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說明懷孕越來越容易被定罪,2015 年,印第安納州的一名女性普維·帕特爾 (Purvi Patel) 被判因使用藥物墮胎犯有殺害和疏忽的重罪,盡管她的體內沒有發現任何藥物,且她聲稱自己流產并處理了胎兒,但帕特爾仍被判處 20 年監禁 (Bazelon 2015),這一定罪后來在上訴中被推翻。
2004年 4月25日,超過一百萬人參與 "March for Women’s Lives "
墮胎和其它生育權利仍然是女性的重大動員議題,因為年輕女性總會和老一代的女性主義者并肩保衛這些權利。2004 年 4 月 25 日,超過一百萬名墮胎權利支持者聚集在華盛頓特區,參加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游行之一——「為女性生命而游行 (March for Women’s Lives)」。在德克薩斯州,對獲取墮胎服務的威脅引發了另一波大規模的動員活動。在最高法院發布禁令暫停反墮胎法案之前,2013 年夏天,溫迪·戴維斯 (Wendy Davis) 參議員對該法案進行了長達 11 個小時冗長辯論 (filibuster),使全國公眾關注德克薩斯州成千上萬的墮胎權利倡導者的工作。YouTube 頻道直播的參議院會議有超過 10 萬名觀看者,推特上有 40萬條推文,甚至奧巴馬總統也參與其中(Kelly 2013; Tumulty 和 Smith 2013)。數以百計的墮胎權利支持者擠滿了德克薩斯州的國會大廈,他們身穿橙色襯衫,而人數眾多的反對者則選擇藍色襯衫來表示反對,因為在色輪上藍色正與橙色相對。這從視覺上象征著圍繞墮胎權的斗爭仍是多么的極化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July 4, 2013)。
4爭取更廣泛生育戰爭的努力
除了墮胎之外,女性更廣泛的生育健康護理也愈多遭到攻擊,反墮胎者已與其他反對奧巴馬總統《可負擔醫療法 (Affordable Care Act)》右翼勢力合流。2012 年,藝術和工藝品連鎖店好必來(Hobby Lobby)就《可負擔醫療法案》中要求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險涵蓋緊急避孕藥具的規定提起訴訟。2014 年,最高法院裁定,好必來和類似的公司可基于宗教偏好而選擇豁免于該法案 (Bravin 2014)。雖然宗教自由的論點在此案中獲得了成功,但反對資助避孕藥具的人群卻對女性的性自由發動了攻擊。例如 2012 年,當法律系學生桑德拉·弗魯克 (Sandra Fluke) 呼吁喬治敦大學在學校健康保險計劃中為學生覆蓋避孕費用,她被右翼脫口秀主持人拉什·林博 (Rush Limbaugh) 指控為「蕩婦」和「妓女」。克里斯蒂娜·佩奇 (Cristina Page 2006: 74–75) 認為,反墮胎運動也是一場反節育的運動,并應注意到該運動與婚前守貞教育 (abstinence-only) 項目之間的聯系。
Sandra Fluke & Rush Limbaugh(圖源:NBC/Getty Images)
女性爭取控制生育運動的范圍也不斷擴大。在有色人種女性的領導下,運動正努力地轉移為以「生育公正」(reproductive justice) 為框架,并與其他斗爭建立明確的交叉聯系,將生育公正與更廣泛的人權議程聯系起來。盡管有色人種女性參與了二十世紀初的節育運動 (Ross 1992) 和第二波女權運動中爭取墮胎的斗爭,但在呼吁更廣泛的女性生育護理概念方面卻和運動存在著內在張力 (Price 2010; Silliman et al. 2004)。1970 年代,由非裔美國女性領導的倡導團體在她們爭取生育權利的斗爭中強調了濫用絕育的問題 (Price 2010) 。同時,一個明確地關聯女性權利與人權的跨國運動正在獲得勢頭。這種框架引起了許多有色人種女性的共鳴,呼應了擺脫個體主義方法論并強調問題之間相互聯系的愿望 (Luna 2009)。1994 年,在開羅舉行的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國際會議后的一個「親選擇」會議上,黑人女性首次創造力了「生育公正」一詞 (Price 2010;Ross 2006)。隨著推廣生育公正這一概念,有色人種女性在2004 年的為「女性生命而游行」中實現了「框架轉變 (frame shift)」(Luna 2010)。正如普萊斯 (Price 2010:43) 的解釋,「生育公正這一框架承認將生育健康權利與其它社會公正問題聯系起來的重要性,如貧困、經濟不公、福利改革、住房、囚犯權利、環境正義、移民政策、毒品政策和暴力」。雖然 1970 年代末的早期生育權利運動也呼吁擴大墮胎權的框架,并應對與階級和種族有關的問題,后來的運動則具體區分了「生育權利」與「生育公正」兩個概念,前者側重于隱私權和生育選擇權,后者則是更廣泛的人權框架的一部分 (Luna 2010:556)。
許多拉丁裔、非裔、原住民和亞裔的美國女性認為建立在「選擇」概念上的框架具有局限性,因為它暗示女性已在物質的層面有足夠的優待,從而具有各種選擇。雖然某項具體的法律權利作為具體的運動目標來說是有益的,但對于被邊緣化的女性來說則遠非足矣,因為她們受到機會缺乏和經濟限制的影響過大 (Hooton 2005;Luna 2009)。在 20 世紀 80 和 90 年代,有色人種女性創建了自己的生育健康組織,既應對優生法規 (eugenics laws) 和政府批準的絕育活動,也應對她們在白人主導的支持選擇運動中所經歷的疏離。那些白人主導的運動只關注墮胎,而忽視了生育對一部分女性來說是激勵性的,對另一些女性來說才是阻礙性的現實 (Luna 2009;Price 2010)。她們呼吁關注控制人口的各種形式,包括福利改革、限制移民和絕育濫用,以尋求應對她們社群更廣泛的需求 (Silliman et al. 2004).
生育公正運動的一個有組織的例子是姐妹之歌 (SisterSong),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有色人種女性的生育權利聯盟,成立于 1997 年,由 80 多個組織組成 (Price 2010)。朝向生育公正框架的轉變愈發可見,這為被邊緣化的女性創造了一個修辭的 (rhetorical) 余地,使她們能致力建立一個集體性的身份,并超越對墮胎議題的單一關注。這使生育議題與艾滋、殘障權利、反貧困政策轉變、移民改革和環境正義的工作之間有了聯系。活動家們希望這一轉變能使更多的有色人種女性認同運動的信息,并更多地參與到爭取生育自由的斗爭中 (Price 2010) 。
二、對墮胎和生育作為動員研究問題的解釋
分析者研究了圍繞墮胎和生育權利議題持續進行動員的各項過程。墮胎的涵義 (meaning) 和激勵框架 (motivating frames) ——無論是合法墮胎的反對者抑或支持者所使用的——是當前沖突中的一大重要因素;而對立運動的戰略互動 (strategic interactions), 包括框架、戰術和開展,也對當前的沖突至關重要。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們將首先研究其中涉及的符號政治,其次則研究戰略互動,以及女性主義者為應對針對生育權利的新威脅而如何調整其戰略。
1符號政治
為了解釋為何關于墮胎的沖突持續存在,許多分析者都指出了墮胎所具有的符號意義。這即是說,墮胎是有爭議的,并非僅是因為墮胎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有道德上的分歧,還因為墮胎象征著更廣泛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在《墮胎與母職政治》(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一書中,克里斯汀·盧克 (Kristin Luker 1984) 發現,墮胎之爭與對母職涵義的不同看法有關。她研究了加州的活動者,反墮胎者往往是決心成為妻子和母親這一傳統角色的女性,盧克認為,保持這一角色的地位對她們有好處,因為她們在就業市場可用于競爭的資源較少;相較而言,墮胎權的支持者往往是受過教育的職業女性,她們并非拒絕母職,但僅將其視為生活的一部分。這一分析表明,墮胎之爭是不同社會地位群體成員之間的沖突 (Gusfield 1963),不同群體成員不僅是對墮胎持相反意見,也是在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往后的作品《當性進入校園》(When Sex Goes to School) 中,盧克(2006)報告了「性自由派 (sexual liberals)」和「性保守派 (sexual conservatives)」之間在學校性教育上的持續分歧。她發現,圍繞性教育的沖突標志著美國社會中關于愉悅、責任和婚姻角色的更廣泛的分歧 (2006: 107)。毫不奇怪地,性保守派反對婚外性行為,將其與 60 年代的性革命關聯起來,且大多數人反對墮胎合法。
其他分析者也將有關墮胎和性行為的斗爭與 60 年代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變化聯系在一起。斯蒂芬·馬克松 (Stephen Markson) 認為,與性別和性存在有關的文化演變,被與同性戀和女性運動關聯,且對那些忠于傳統價值觀的人來說是一種威脅。對他們來說,「游戲規則」已經發生變化,而墮胎則是這些變化的象征 (Markson 1982: 25)。同樣,在對 80 年代初北卡羅來納州新右派的研究中,安東尼奧伯沙爾 (Anthony Oberschall) 發現,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的反主流文化,包括性解放、吸毒、張揚自我的權威、以及新的性別角色,「冒犯并激怒了美國文化傳統主義者的情感」(Oberschall 1993: 339)。作為具有共同價值觀和信仰的宗教團體的成員,保守派基督教徒擔憂這些外部變化會威脅他們按基督教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社會化青年兒童的能力。其中墮胎尤其具有威脅性,因為它關聯于性行為以及面臨外界影響時掌控自己孩子的難度。因此,墮胎象征著對保守派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更廣泛的威脅。
其它研究則認為,在墮胎之爭中,不同群體間并沒有較大的極化現象。在對加拿大反墮胎活動者的研究中,庫尼奧 (Cuneo 1989) 發現盧克將墮胎沖突解釋為兩個女性群體之間的沖突過于簡單化。他指出,在美國和加拿大,男性和 30 歲以下的未婚女性都大量參與了反墮胎運動。而在對多倫多的反墮胎活動者的研究中,庫尼奧發現「親生命」的活動者在意識形態上比盧克所設想的有更多的多樣性,他還指出反墮胎運動內部也在在框架和意識形態方面存在沖突。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蒙森 (Munson 2009) 也發現,「親生命」的活動者內部有著迥異的信仰,運動內部也存在張力,活動者們會使用多種不同框架,對如何理解墮胎問題也沒有達成共識。在 2012 年關于墮胎和母職政治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的研討會上,謝爾茲 (Shields 2012) 指出,自盧克進行研究的年代以來,性別角色已發生變化,「親生命」的人已經不那么傳統,在關于性別的意識形態上已更接近「親選擇」的人。謝爾茲認為,關于墮胎的沖突已不再象征關于性別和母職意見的分歧,而是關于胎兒的權利與女性的權利。費爾德曼和韋茨 (Freedman and Weitz 2012:40) 則指出,60%進行墮胎的女性已經有了孩子,且其中許多是低收入女性,她們墮胎不是為了拖延母職,而是為了對自己的生活進行管理。她們指出,關于女性是否應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辯論已不復存在。作為勞動力的永久組成部分,大部分女性都需要在家庭之外工作。然而,一般公眾和「親生命」運動內部人士的態度仍存在差異。根據佩吉 (Page 2006) 對「親生命」運動的網站和其它通訊的研究,支持「親生命」運動的人士仍然忠于傳統的性別和家庭觀點。
隨著時間推移,墮胎沖突的性質明顯地發生了變化,性別和家庭角色也在進行演變。然而,性別議題仍是持續進行的圍繞墮胎斗爭的核心,正如前文已詳述的最近新聞事件所表明的那樣。波利特 (Pollitt 2014:31) 認為,反墮胎運動并非僅是關乎胎兒的生命權,而且「也是對女性日益增長的自由和權力的抗議,包括她們在性方面的自由和權力」。她認為,關于墮胎的討論往往聚焦在對女性性存在的判斷上,如共和黨政治家進行的那些與強奸幸存者有關的廣泛宣傳,如托德·阿金 (Todd Akin) 斷言在所謂「合法」的強奸中不會發生懷孕 (2014:105)。佩奇 (2006) 還發現,反墮胎者反對性自由,且運動中的許多人既反對墮胎也反對避孕。即使女性在家庭外的工作已經變得普遍且廣泛接受,但她們作為性行為參與者的獨立性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而這則影響了關于墮胎和節育的辯論。
2戰略互動
運動 / 反運動的動態演變,對于女性主義者圍繞墮胎和生育權利的持續動員來說也至關重要。正如所見,對立的運動在不同的戰場——立法機構、法院和街頭——此消彼長,互相較勁。墮胎運動在推動墮胎合法化的時期是積極進攻的,但隨后不得不策略性地回應其反運動的出擊,而反運動則是在羅訴韋德案判決的威脅下獲得動力。墮胎運動則繼續以各種方式從戰略上適應其反對者和不斷變化的政治環境(參見 McCammon 2012),在組織和戰術上,NARAL 等墮胎權利團體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以游說國會和參與訴訟,同時也發展基層分支機構,在州一級游說, 并反制反墮胎者的街頭戰術 (Staggenborg 1988,199; Wilson 2013)。盡管墮胎運動的許多戰略是針對反運動的出擊而制定的,它仍采取了許多積極主動的策略,并持續增添不同的選民。
除了努力挫敗各項限制墮胎的立法,活動者們也在游說各州通過支持生育權利的立法,以擴大女性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這項運動將生育權利與更廣泛的經濟和政治議程聯系起來,使女性能夠更多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從而獲得更廣泛的支持,推進攻守同盟型 (coalition-driven) 的立法平臺。這一立法包裹 (legislative packages) 計劃,包括提高墮胎服務的可達度、將這一目標與產育護理和經濟可負擔的兒童護理等特性進行聯系、同工同酬、更好地獲得家庭計生服務、和努力防止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和歧視 (Culp-Ressler 2014)。
2012 年,在賓夕法尼亞州,一個非營利女性法律倡導團體,與醫療保健提供者、生育公正活動者和「親選擇」立場的立法者合作,提起了賓夕法尼亞州女性健康議程 (Pennsylvania Agenda for Women's Health),這即是個立法包裹,旨在應對妨礙女性福祉的一系列障礙(見http://pa4womenshealth.org)。2013 年,國會議員提出了《2013 年女性健康保護法》(Women's Health Protection Act of 2013),旨在防止各州對墮胎進行非醫學必要的限制,以保護墮胎權利 (Culp-Ressler 2014)。
生育公正活動者的另一項主動戰略,則是為與墮胎有關的實際支持服務建設基礎設施。這包括由全國墮胎基金網絡(National Network for Abortion Funds,見 www.fundabortionnow.or )等團體為女性籌集墮胎資金,為女性提供并協調診所的往返交通,并提供其它支持服務,如幫助女性在獲得墮胎手術的過程中處理她們工作、家庭方面的雜事。與部分醫療專家的聯盟則使活動者能夠進一步采取攻勢。「親選擇」的倡導者也一直把目標放在醫生身上,這些醫生對越來越多的墮胎限制以及為看護客戶必須跨越無數障礙的的親身經歷感到憤怒。這為阻撓法律創造了更多的動力(Chen 等,2015)。這種戰略方針反映了醫務人員和「親選擇」活動家之間不斷變化的關系,這一聯盟并不穩定,有時則是矛盾的。因為醫生變得更加政治化,而活動者則變得更加專業化(Joffe 等,2004)。
在運動框架方面,墮胎權利運動不斷改變其框架,以應對其反對者和不斷變化的政治氣候, 而反墮胎運動也同為如此。由于相互競爭的存在,雙方都在努力通過大眾傳媒傳遞信息(Ferree 等,2002;Rohlinger 2002,2006,2015a)。在墮胎合法化之前,支持墮胎的改革者引述了非法墮胎的恐怖,敘述那些無疑需要合法墮胎的極端情形,以及作為非法墮胎受害者的年輕女性的故事 (Condit 1990)。在公共話語受到影響后,20 世紀 60 年代的運動——且尤其是女性運動里,支持墮胎的論點開始集中關注女性權利和控制自己身體的能力。認為女性應該平等、自由的想法被結合為一,產生了對「選擇的權利 (Right to Choice)」的呼求 (Condit 1990: 67)。在墮胎合法化后,「親選擇」的框架被廣泛使用,以回應其反對者的所謂「親生命」框架。這一框架非常成功,因為它迎合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自我選擇」,且使墮胎合法的支持者是在支持選擇自由,而不是直接「親墮胎 (pro-abortion)」。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墮胎權利運動通過抗議政府對女性生活的干預來抗擊其反對派,而塞爾坦 (Saletan 2003) 認為,這一策略有其代價,因為這一更保守的框架將使貧困女性的墮胎資金等議題邊緣化。
長期以來,女性主義內部對「親選擇」這一言辭爭論不休,一部分人主張,由于避免使用「墮胎」一詞,這種言辭助長了將墮胎描述為「駭人之事」(Ferree 2003: 330),而其她人則認為「親選擇」這個詞是指稱那些「支持女性有權自己決定是結束妊娠還是懷胎到足月的人」(Pollitt 2014: 14) 的有益方式;一些女性主義者則認為,需要有意識地重拾墮胎的積極意義,將其視為一個安全、實際的決定,且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是必要的。她們認為,運動往往關注極端的情況下墮胎的必要性,如強奸和亂倫,盡管這一措施為運動贏得了盟友,但這種防御性的戰略只獲得了表面性的支持 (Pollitt 2014)。
由于需要抵御對墮胎越來越多的限制,主流墮胎權利運動似乎已開始采用表示歉意的策略 (apologetic strategy),但墮胎權利的提倡者也一直努力試圖影響文化,并以不含歉意的方式描述墮胎的情況。諸如2014 年《平淡無奇的孩子》(Obvious Child) 等流行電影,和印有「我墮過胎」的 T 恤衫等服飾,都在努力消除墮胎的恥辱感。社交媒體也有助于抵制「墮胎是可恥的秘密」這一信息,例如,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那些自白式的關于墮胎的個人敘述引起了全國關注,「三分之一運動」(1 in 3 Campaign, 指的是據一項統計每三個女性中就有一個經歷墮胎)的倡導者為女性提供在線平臺來分享她們的故事,以促進墮胎經歷正常化。社交媒體的去中心化和迷因 (meme) 的病毒式擴散能力,使圍繞墮胎的對話有了前所未有的參與度。然而,數字技術也可能對墮胎權利活動者的戰略選擇造成限制,畢竟從前她們對信息有更多的控制能力。
運動和反運動的框架策略也在互動中相互演變。麥卡弗里和科耶斯 (McCaffrey and Keyes 2000) 研究了紐約州的全國女性組織 NOW 在墮胎議題上的框架實踐變化,并表明該組織使用了各種言辭策略來回擊其反對者,包括謗議 (vilification) ,揭露反對者的框架,以及為運動的框架辯護。麥卡弗里和科耶斯認為這些框架策略有助于對支持者的持續動員。伊斯塔科伏 (Esacove 2004) 研究「半分娩墮胎 (partial birth abortion) 」的框架變化,揭示議題框架如何通過與對立運動互動而演變。對立雙方的活動者有時還將沉默作為一項戰略反擊,來回應實事和對手的舉動,并影響信息傳達。例如,在反墮胎活動者謀殺佛羅里達州一家墮胎診所的醫療提供者后,反墮胎活動者通過直接譴責暴力,得以維持公眾支持。但十年后,當媒體狂熱地追念他被處決一事,全國生命權委員會(National Right to Life Committee,是一個反墮胎的組織)避開了進入媒體辯論,從而在一場戰術多樣化的運動中有效保持了其內部的凝聚力 (Rohlinger 2015a) 。盡管墮胎權利運動奮力對抗反墮胎運動的框架成分,但反墮胎者成功地使公共話語向他們轉變,并最終成功贏得了一些對晚期墮胎的禁止令 (Gerrity 2010) 。
盡管墮胎者成功地部分影響了這一議題的公共話語,但女性運動的成功也使他們的言辭發生了變化。正如施萊伯 (Schreiber 2008) 在《糾正女性主義》 (Righting Feminism) 中所言,保守派的女性組織被迫修改她們的言辭,以承認女性運動的成功和文化環境的變化,如公眾對女性在家庭以外進行工作的壓倒性接受。因此,反對墮胎的團體,如「北米憂國婦女團 (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 」,將其反對意見歸結為她們所聲稱的墮胎對女性造成的身心傷害(2008:97)。此外,反墮胎者還挪用了女性主義的策略和言辭。例如,蘇珊·B·安東尼的名單 (Susan B. Anthony List) 是一個反墮胎組織,照搬了女性主義的組織艾米莉的名單 (Emily’s List) 的名字,挪用著名女權領袖的名義為反墮胎候選人籌集資金,并「告誡政治家以聽起來幫助性而非懲罰性的方式談論孕婦」 (Sanneh 2014: 39) 。
除了相互回應,對立的運動也表現了對不斷變化的政治氣候的戰略適應。在一種政治環境下有效的框架,也可能隨環境變化而不再有效。在 2012 年選舉年,包括密蘇里州的托德·阿金在內的許多共和黨候選人,「對強奸和墮胎發表了政治上不幸的評論」,從而為女性主義者創造了機會,將他們指控為「對女性宣戰」 (Rohlinger 2015b: 70) 。然而,隨著發表這些過激言論的候選人的消亡,以及反墮胎者學會使用更有效的所謂「宗教自由」框架,這一指控「對女性開戰 (war on women) 」的框架最終變得無效 (Rohlinger 2015b: 71) 。而其它的女性主義的框架,如「生育公正」,則可能更持久,因為它們扎根于有色人種女性等群體的長期經歷。
然而,在女性運動中也存在著關于框架爭議的張力,不僅對「選擇」框架的有用性存在爭論, 而在倡導使用新框架的團體內部也存在分歧。一些有色人種女性認為,生育公正框架的政治、經濟目的還不夠深入,并呼吁「親選擇」運動對資本主義和監禁制度采取更強硬的立場 (Smith 2005) ;還有人認為,原本建立在憲法上的墮胎權與生育公正的進路相抵觸,因為前者以隱私權作為其基本的意識形態,而最小化國家干預和更多公眾支持之間卻有著緊張關系 (Hooton 2005;West 2009) 。然而,如果運動內部的張力使得對戰略和戰術有更多的批評性評估,卻也可能是積極的 (McCammon 2012) 。
普萊斯(2010)呼吁更多關注生育公正運動所產生的集體認同,以便更好地評估運動的影響、參與以及戰術選擇。對建立集體身份問題的關注,使我們好奇「生育公正」運動是究竟從屬于「親選擇」運動,還是彼此獨立,甚至背道而馳。生育公正的框架也引起了更年輕一代女性的共鳴,過去幾十年中她們接觸了女性主義者和酷兒理論家對壓迫、以及不斷變化且日益模糊的身份界限的交叉性分析 (intersectional analyses) ,而這些想法已經融入了流行文化的骨架。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如果要實現更廣泛的生育公正議題的目的,這一框架將與真正具有交叉性的女性主義進路密不可分 (Hooton 2005) 。
三、總結
紀錄片《推翻羅伊訴韋德案》
在本章中,我們探討了兩個關鍵問題。首先,為和墮胎和其它生育相關議題能持續動員互相對立的運動,并帶來無盡的沖突?其次,隨著時間推移,運動的策略又如何轉變?為了弄清這些議題為何能持續動員活動者,我們需要了解它們對活動者所具有的的意義,以及運動 / 反運動間的動態作用。對于女性主義者來說,墮胎和控制生育是女性平等以及性自由的基礎之一。雖然自墮胎沖突的早期以來,女性的社會角色和家庭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但這一議題仍與性別和性存在密切相關。反墮胎者關心女性的性存在,對墮胎權利的支持則關乎對性別平等和性自由的女性主義追求。而相反運動造成的威脅也使圍繞墮胎沖突能持續下去,因為當一方贏得戰果,另一方就會獲得動員的動力。
女性運動持續在調整其戰略,部分原因是它一直在被迫回應其反運動的戰術,但女性運動有時也能采取主動攻勢。年輕女性和有色人種女性對運動的持續動員、戰術創新和成果來說尤為關鍵。而新的框架和戰術正是隨著新的支持者進入運動而發展。例如,年輕女性創新性地使用了社交媒體,而有色人種女性則提出了生育公正的框架。部分墮胎的支持者也持續質疑現有的進路,舉例來說,如果生育公正框架要繼續擴展,且與多樣性的經驗對話,它就可能需要面對殘障議題 (Piepmeier 2013) 和跨性別權利 (Chanda 2015) 等問題。女性主義內部的選民多樣性,將使其可能應對社會、政治和生態等不同領域的性別不平等,而最終實現墮胎成為女性真正的自我選擇。
關于墮胎和生育權利的未來研究,應仔細審視那些使女性主義團體能在戰略上適應不斷變化的政治和文化環境的因素 (McCammon 2012) ,這涉及到運動中組織結構和網絡,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戰略決策。特別來說,有必要追蹤運動的組織形態如何隨時間推移而在其支持者和反對者的影響下改變,從而對早期的研究進行更新。我們需要知道,運動的動員結構發生了哪些變化,它們是否還能吸引新的選民?隨著年輕女性主義者和有色人種女性建立自己的組織,女性運動的框架和策略又將如何變化?而反運動的組織、戰略的新發展又如何影響了女權運動的組織?這些都需要進行新的研究,包括比較性的研究 (見 Halfmann 2011) ,以追蹤隨近年來的政治、文化和科技發展帶來的運動框架和集體行動的變化。社交媒體顯著地對戰略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學界需要更多關注社交媒體的性質和作用,以及墮胎之爭中對立運動的其它組織和戰術的特點。
參考文獻
Bazelon, Emily. 2015. “Purvi Patel Could Be Just the Beginning.” New York Times, April 1. http://www.nytimes.com/2015/04/01/magazine/purvi-patel-could-be-just-the- beginning.html?_r=0.
Blanchard, Dallas A. 1994. The Anti-Abortion Movement and 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From Polite to Fiery Protest. New York: Twayne.
Boonstra, Heather D., and Elizabeth Nash. 2014. “A Surge of State Abortion Restrictions Puts Providers—and the Women They Serve—in the Crosshairs.” Guttmacher Policy Review 17(1). http://www.guttmacher.org/pubs/gpr/17/1/gpr170109.html.
Bravin, Jess. 2014. “Supreme Court Exempts Some Companies from Health Care Law on Religious Ground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 pp. A1, A6.
Calmes, Jackie. 2015. “Reacting to Videos, Planned Parenthood Fights to Regain Initiativ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p. A1.
Carmen, Arlene, and Howard Moody. 1973. Abortion Counseling and Social Change. Valley Forge,PA: Judson Press.
Chanda, Sagnika. 2015. “State Interventions in Transgender Parenthood and Pregnancy.”Presented at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Health and Access Conference, Pittsburgh, PA.
Chen, Beatrice, Catherine Chappell, Audrey Lance, Jane McShea, and Marta C. Kolthoff. 2015.“Access to Abortion in the U.S.: Implications of Targeted Regulation of Abortion Providers.”Presented at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Health and Access Conference, Pittsburgh, PA.
Condit, Celeste Michelle. 1990. Decoding Abortion Rhetoric: Communicating Social Change.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ulp-Ressler, Tara. 2014. “Why 2014 Could Be a Huge Turning Point for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