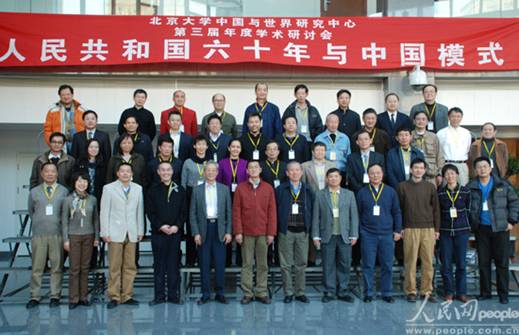本黨,聚沙成塔的魔術師
——司馬南在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年度學術研討會上演說中國模式
按語:
今天是本黨中共成立88周年紀念日。
迄今本人黨齡已逾28年。
有心寫一篇長一點的文章,整理思路時發現好多事情還來不及作深入思考,加之這一段俗務纏身,時間特別緊,拿不出像樣一點的東西。恰巧,瑪雅博士發來本人2008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學“人民共和國60年與中國模式”研討會上的一篇發言的記錄稿,中間涉及到對本黨地位與作用的認識。本人講話固為淺薄,亦不揣冒昧,但是,即席發言,有聲有響,較為靈動,校改之后首發于此。敬請本黨同志批評指正,同時俺也不忌諱那些立志把推翻共產黨當事業干的好漢們繼續來此潑污,北京龍須溝的老百姓常說,褒貶都是買家。
下圖三排左六黑衣蓄須者即為本人,圖后短文為人民網當日報道
|
潘維(一排左四)、李強(二排左八)、胡鞍鋼(一排左三)、溫鐵軍(一排左一)、房寧(后排右二)、賀雪峰(三排左八)、石之瑜(三排左十)、司馬南(三排左六)等與會學者合影。 |
人民網北京12月21日電 (記者 唐述權)12月20日-21日,由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辦的“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關新園舉行。在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上,共有52位來自海內外的著名學者圍繞“中國模式”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出席會議的學者有主辦方北大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汪暉,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房寧,社科院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張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丁寧寧,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主任王紹光,獨立學者司馬南等。對于召開此次研討會的目的,潘維教授表示:“中華民族在‘人民共和國’期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走出了一條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一個‘中國模式’已經呼之欲出了。為促進‘中國模式’的總結概括,也為促成國際學界‘中國學派’的興起,我們組織了此次研討會。” 會議共分七場,就以下五大類議題展開辯論:中國獨特的社會模式,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中國獨特的政治模式,中國獨特的思想方法,前四種模式之間的有機聯系。會議論文從縱向把握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有關史實,從橫向比較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道路,論述了所探討的具體領域與抽象的“中國模式”之間的關聯。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將負責會議論文的正式結集出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辦于2005年7月,是北京大學下屬的、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代管的學術研究機構,為研究中國與世界面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提供平臺。
司馬南演講記錄稿
參加今天這個研討會,潘維先生打招呼,囑我寫一篇論文,當時未加思索就答應了。后來潘維的學生正式通知變得鄭重起來:“對遞交給會議的論文,有具體要求,必須符合嚴格的學術規范……”,我一聽就傻了。
咱不會按照“嚴格的學術規范”寫論文啊。
所以矮人家半截,未提交規范學術論文出席研討會,心虛著呢。
轉念一想,干嘛心虛呀。據說穆罕默德、耶穌基督、孔夫子、毛澤東也都不“按照嚴格的學術規范”來寫文章,反倒是研究默罕默德、研究耶穌基督、研究孔夫子、研究毛澤東的人,都必須按照“嚴格的學術規范”寫文章。
我的發言是隨想式的、靈動的、跳躍的,不符合“嚴格學術規范”的。
因為本人的不規范的發言,本次學術研討會或許增加一種色彩:除了學者式的中國模式總結外,百姓某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中國模式研討會因此而更具開放性、豐富性、兼容性與社會影響力,列位學者便愈發象學者。
如果一個人只有二十歲,喋喋不休大講“人生經驗”,好玩是一定的,也很可能招人討厭,在座的李昌平教授也許會說,太嫩了,簡直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一個剛及而立之年的年輕人超常自信地講到,“積三十年經歷,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后接“一、二、三、四、五……”,在座的王紹光教授也許會說,唉,我們年過半百的人還沒發言呢!
可是如果一個六十歲的老人感嘆道,“這輩子啊,我數著石頭,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一個甲子、一個輪回,一生回首,人們大概有必要靜下來聽他說點什么了,六十“耳順”啊,積六十年的經驗,這里邊必定會有些值得總結的經驗和教訓。劉曉慶很年輕的時候,都可以寫“我的路”,共和國六十年,為什么不可以坦然地自信地講一講中國模式?誠然,對于人的一生而言,六十年至少意味著大半輩子,對于共和國而言,不過是一日之中剛剛開啟的霞光滿天的希望黎明。
謙虛是美德,我們可以謙虛地僅僅以“我們的路”、“我們的經驗”、“我們的體會”來概括中國模式,但是,將成功的東西理論化、系統化、集成化,徑直以中國模式概述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須知,中國模式,在今天已經不是破題了。潘維先生早就在力倡中國模式。他是不是首倡,我不知道,但是力倡同樣有功。將大家從全球各地召集到北大聚而研討中國模式,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功在社會,善在社會,利在社會。
哈哈,潘維教授在那里不會被我這話嚇一跳吧?
不經意間創造歷史的人常常意識不到自己的作用。
先講一個觀點,模式是中國模式,模式只能是中國模式。
我們未必不愿意西方模式,譬如美國模式吧。正如一些浪漫的自由主義者想象的那樣,三權一分,聯邦制一搞,總統一選,于是中國就有了美國那樣高的GDP,中國老百姓就過上了美國富人那樣的好日子,我們家在西海岸就有了別墅……這樣當然很好,但是真的可能嗎?
中國能夠做到人均占有資源是世界平均的30倍嗎?我們能象美國那樣想打誰就打誰,不斷通過戰爭的手段和不流血的政權顛覆的手段,來隨心所欲改變世界利益格局為我所用嗎?我們能在全世界各地敲骨吸髓汲取資源,讓自己的財富充分涌流,華爾街高管年薪幾千萬,汽車廠工人每小時工資72美元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既有秩序的制定者、受益者人家不肯相讓啊。你委曲求全地見人就拱手作揖聲言和平崛起,百分百地按照人家的體系人家的規則與人家做生意,兩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人家還NMD你、封鎖你、詆毀你、妖魔化你,對你實行“顏色革命”,實行“文化毒化”呢,即使人家無條件地平等地善意地對待我們,美國模式在中國也照例行不通。不說別的,假如中國人均家庭轎車象美國人一樣,這個地球恐怕首先承受不了。所以,不論我們愿意不愿意,不論我們主觀動機怎么樣,中國的發展模式必須是中國的,也只能是中國的。
當年咱不是沒試過西方模式。就政治模式而言,北洋試過吧?民國試過吧?試得怎么樣呢?試得河南老鄉袁世凱干了83天皇帝徹底歇菜,試得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遍地哀鴻,試得蔣委員長將黨與國玩弄于股掌之間,試得軍統、中統真統天下戴笠式人物成為江湖大佬后墜機身亡,試得局面一塌糊涂國家稀里嘩啦。
最后六十年,接受國民黨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接著試,先照本宣科念著馬克思列寧的經來試,后實事求是念著毛澤東鄧小平的新經來試,試來試去,春華秋實,試出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之見,今天固然可以論證中國模式之有無的問題,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很像一個單位兩塊牌子,一個老頭兩個名字。中國模式乃為既有之物,乃為客觀存在,乃為別于西方模式、他國模式的中國人自己把玩在手行之有效的價值體系、文化體系、工具體系。
第二個觀點,中國模式是逼上梁山的結果,是生生逼出來的。
遙想當年,區區兩萬洋兵,洋槍一架,中國的馬隊,驍勇彪悍的的清兵,就是瞄準器下一個一個的活動靶子。洋人恣意的屠戮游戲結束,中國政府出面,四億五千萬國人,按照每個人頭一兩白銀賠款給獵殺中國人的劊子手。四億五千萬人呀,兩萬洋兵。英國人藉此而攫取的財富,足以支持完成全社會保險體系的建設。一說到這些,哪個中國人能不心痛?后來更嚴酷,日本人打進來,野蠻肢解中國,屠戮三千萬中國人,我們迫而救亡保種,中國人發出最后的吼聲。
本來,沒有鴉片和洋槍洋炮轟開中華古老的國門,中國也會緩慢地發展到到資本主義。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但是,后來中國緩慢自然的社會發展進程被打破了,歷史改變了方向,中國人選擇了社會主義,認定了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并且矢志不移。這個局面的形成,要感謝那些列強們,是他們把中國逼到了今天路上來的。那么難的時候都走過來了,足以證明中華民族是5000年的不死鳥,死而后生,九死一生,浴火重生。
回過頭,數數曾經經歷過的那些日子,看看那些浸透著死難同胞血跡的腳下的道路。我們無法用優雅的心態,自由地想象中國模式合乎邏輯的推演過程。事實上,我們堅守的的主義與創造的模式,都不是設計出來的,生更不是哪個人設計出來的,而是被動適應各種臨界變化的結果,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是“生存法則勝過一切”的必然選擇,是無比復雜的自組織系統的隨機演化結果。曾經的創傷和屈辱,曾經熱臉貼人家冷屁股,曾經的被出賣被欺負,曾經的咬碎了牙齒和血吞下……所有的一切,把我們逼上了一條叫社會主義的道路。憧憬、初試、小成、瓶頸、湍流、痛苦……遍嘗九九八十一難,始有了今天國家獨立、社會安定、人民吃飽飯,年輕人唱歌跳舞做游戲,軍隊扣著核武按鈕揚眉吐氣有尊嚴的生活。
第三個觀點,中國模式是試出來的,摸出來的。
路風先生昨天講過,說沒想到啊,特意外地,糧食就夠吃了;特意外地,鄉鎮企業就異軍突起了;特意外地,特區就成功了;特意外地,中國企業竟然獲得自主研發能力了……。這些意外,講的都是“歪打正著”,正中下懷。
路風先生沒有講,我們也曾經“正打歪著”,適得其反。
還記得1988年自上而下鬧物價改革么?物價當時敏感的很,社會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物價改革關口要不要過?怎么才能過?過得去過不去?趙紫陽大人的說法是,過也得過,不過也得過,長痛不如短痛。那時,兄弟我正在一家報館作小頭目,每天為社評操心。絞盡腦汁撰寫評論的時候,一樣跟著上面的口徑照葫蘆畫瓢,也咬牙切齒地喊“過也得過,不過也得過”。我們的報紙是《中國商報》,物價改革,本報正管。結果怎么樣?那一輪物價改革關沒過去,搶購風潮席卷全國,人們不滿之聲嘈嘈然分貝驟然升級,累及下一年,1989,引發動亂,差點連老本都賠個干凈。
只講“歪打正著”,過關斬將,顯而易見的好處是鼓舞士氣,用樂觀主義情緒調整氛圍,但是這不符合歷史的真實,無從得到探知真正有效的經驗模式,而專心地總結一些“走麥城”,包括“大意失荊州”,包括“胡亂三板斧”,正視我們曾經“正打歪著”的歷史,包括使個大勁放個小屁的經歷,反倒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試錯,這東西聽起來好像不是那么堂皇,不像是從一個理念出發,惠澤方海般地累積紅利進而完勝那么體面,和中國模式好像關系也不大。其實,試錯,真真大規律也。無論是甲殼、多足小蟲還是哺乳類動物,或是長臂猿、類人猿,直至人類,都是要在試錯的基礎上獲取進步,試試錯錯,試試錯錯,試試……OK,對了。試錯是個大規律,我們是“積小成而得大成,去小錯而避大過”,因為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沒有告訴我們,今天具體應該怎么辦。小平同志的戰術要求概之以“摸”,戰略要求概之以“貓”,好在目標已經明確,一路摸下來就是了。中國模式就是這樣試出來的,摸出來的。故而,中國模式或可易名為“中國摸式”。
第四個觀點,中國模式,核心是讓人民滿意。
改革開放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即抓問題,從問題出發。
抓問題,是一種意識;抓問題,也是一種能力。從問題出發,去解決真問題,而不是從本本出發,從觀念出發去制造偽問題,解決偽問題。
如果從本本出發,從觀念出發,無論哪個本本、哪種觀念,都沒有中國模式的位置。但是按照“讓人民滿意”的標準來抓問題,中國模式必然凸現出來。
現在有一種人,喜歡拐彎抹角地編造借口,忽悠我們不必去在意人民滿意與否,強調必須讓洋人滿意。
讓人民滿意,還是讓洋人滿意?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選擇。讓人民滿意,是中國模式的應有之意;只讓洋人滿意,不屬于中國模式。讓洋人滿意,千方百計取悅于洋人,甚至認為洋人之所以不滿意,罪在我們,罪在吾族,這樣一條路我們不能走,也走不通,那是通往地獄的死路。
這個論證并不復雜,北方鄰國20年前開始走一條從觀念出發,旨在讓洋人滿意的道路,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中國西山會議,北大某公有此類鸚鵡細語,某憲章中,漢子們更加直截了當了),國家解體了,人心散掉了,國際地位失去了,自家兄弟相殘,至今槍炮聲不斷……洋人滿意了沒有呢?沒有啊。北約仍在東擴,不斷蠶食其地盤,顏色革命此起彼伏。幸有普京這樣清醒的政治家,該國小幅震蕩盤整格局,還將持續。
在總結中國模式時,從觀念出發,而非從問題出發的“政治浪漫主義”最為有害,這種“政治浪漫主義”刻意要國人相信奇跡——世界上有西方大國比中國人民自己更關心中國人民的幸福,他們會象諾爾曼·白求恩那樣無私地幫助中國人民。
必須指出,國門開,生意來,所謂生意,本質上是互通有無,互惠互利,今天叫雙贏,就是相互需要得到滿足。僅單一方面滿意,另一方吃虧的買賣,不符合生意原則。北京天意小商品批發市場的攤主都明白的生意原則有三:一為個體獨立,二為彼此平等,三為交易自由。取消自己的獨立性,自貶為附庸走狗的行為不要顏面且愚蠢至極,人民的利益與洋人的利益存有永遠無法克服的“不兼容”,洋人首先是美國人,從來不是中國人民的上帝,中國人民沒有上帝。
歷史上,確有部分黑人被調教得很成功,他們把自己侍奉白人視同為侍奉上帝,但后來終于發現,代表上帝的白人除了屠殺黑人以外,能給黑人的最好出路,只有作奴隸。
第五個觀點,中國模式的本質是“山寨中國”。
昨晚討論,我首發此言,冒叫一聲,本以為會遭到呼嘯板磚,想不到列位學人如此寬容。
山寨,原意為有柵欄等簡易防守功能的山莊,后泛指窮地方、窮人聚居的地方。
舊詩曰“有財居大宅,無財住山寨。大宅真才少,山寨盡是才”。
廣東人近年把不受政府管制的地方,包括盜版、克隆、仿制或者行業政策邊緣地帶的民間產業,叫作山寨,于是,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成了山寨的新含義。今年(2008),山寨文化突然大面積蔓延,對精英文化的挑戰成了山寨新意。
如果我們避開克隆盜版一類知識產權問題(避開,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很體面,也不意味著這個問題碰不得,發達國家為了對后進國家設障,以維護并不公正的世界體系,進而保護本國利益是這個問題的實質),從“山寨原意”角度看中國模式,大家會發現,“山寨中國”與今天我們討論的中國模式,何其相似乃爾。
一曰窮人扎大堆;二曰充滿創造性;三曰挑戰既有體系;四曰自我設防——山寨中國,把社會發展建立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不卑不亢地與“大宅富戶”交往,依靠人民的聰明才智,篤信發展硬道理,堅守根本利益底線,低成本地又好又快地擴充自己的實力,在現有的條件下,因地制宜,靈活機動,齊心協力奔好日子。
我只能這么干啊。
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富人要活,窮人也要活;你有尊嚴,我也有尊嚴;你有需求,我也有需求。于是乎,在山寨里,我就過起了這樣勤奮紅火的日子,在山寨外就有了越來越多的深層交往。原來,我寨子不如你;現在,我正在拉近與你的距離;將來,我寨子里的日子不會比你差哪去。這是信念,亦是動力,亦復為模式。歸根結底,這是事實。
這個問題,就像毛澤東當年在井岡山,毛主席不服氣啊,那幫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的人動則頤指氣使,壟斷了真理的發布權、解釋權、還奪去了毛的指揮權。毛老人家就不信這個邪,“山溝里為什么就不能出馬列主義”?
同理,山寨模式為什么不可以是中國模式?
山寨模式為什么不可以與美國白宮模式平分秋色?
山寨模式為什么不可以與英國白金漢宮模式平起平坐?
自言中國模式是山寨中國,并無貶義,對此躲躲閃閃恐怕生出什么副作用的諸公,何不想想美國的例子?如果美國學者不健忘,不自恃清高,應當有能力,有勇氣承認,白宮比之英國的白金漢宮,也疑似山寨啊。
量量尺寸,看看級別,查查出身,驗驗血統,美國白宮文化與山寨文化何異?
故而,山寨中國,沒有什么不好,不怕別人看不起,就怕自己沒有信心。
就山寨中國而言,人家從看不起,到看得起,從敵視我們、全面封鎖我們,到與我們打乒乓、做生意,從“接觸性遏制”,到“中國威脅論”,從“利益攸關方”,到今天更多的溢美之詞,洋人眼里中國形象的全部變化演進過程,總共不過六十年。
中國模式有目共睹的成績,促使我們靜下心來,慢慢總結其中的規律,譬如,后三十年經濟加速發展的一個規律性的東西大家業已形成共識,那就是打開山門啦,改革開放啦,我們大家都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所以,打開山門是強國之路,這個基本結論,反對的人一定不多。但是到了2008年的今天,只講“打開山門”已經不夠了,片面地一味地強調殺出血路來“解放思想”,甚至“解放”到連“山門意識”都放棄掉,連“國家意識”都更換掉,連愛國主義都被妖魔化成了“極端民族主義”,那就未免太不靠譜了。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對開門,對為什么開門,對開門干什么,對開門注意什么等等重大問題,有過許多諄諄告誡,不知為什么,有人拉開門之后,很快地就將小平同志的這些話忘到了腦后,甚至連門里門外都搞不清了。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先生以“國家第一”作為演講題目,他的很多話如果換個國名,我是很聽得進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不能改掉。改掉了民族意識、國家意識,當然就沒有了國家利益,沒有了國家利益,民族復興從何談起?民族復興不講,還有什么中國模式?講中國模式又有什么意義?
身在山寨,卻魂不守舍,心根本不在那里,整日嘮嘮叨叨嫌山寨這也不合人家的規矩,那也不合城里人的規矩——“城里的韭菜不是這樣切的”。這種人言說山寨中國,不配,不配。
第六個觀點,山寨中國的機制,本黨聚沙成塔。
過去的中國,積貧積弱一盤散沙,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處于前工業社會,非現代社會,因此無法形成強有力的組織力量。這六十年,不一樣啦,事實上六十年前的幾十年,就已經大大地不同了。為什么呢?就因為有了一個全新的組織。
小平同志在講民主的時候,講了一句馬克思列寧,更不要說盧梭,伏爾泰,托克維爾,誰都沒有講過的話——“最大的民主,就是調動積極性”。此話簡直妙極了,透射出偉人的大智慧:從問題出發,直奔主題,看重結果,一語中的。比之那些懶婆娘裹腳一樣奇長無比,從觀念出發本本出發,對民主問題舍本逐末,玩弄形式的民主高論,不知道要高多少倍。(昨天會上紹光兄引用過這句話)。
鄧小平說,“最大的民主,就是調動積極性”。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是本黨魔術師般地將人民發動起來,一盤散沙式的民眾,因為“支部建在連上”而獲得空前的戰斗力,因為“利為民所謀”而聚沙成塔。眾志成城,螞蟻搬家,都可以用來形容中共的魔術師效應。無論戰爭、建設、改革,莫不如此。六十年里,若離了本黨這一條,中國模式從何談起?
我注意到一種傾向,有學者似乎有意避諱談中共作用話題,據說是因為太接近意識形態。余以為,共產黨意識形態具有如此非凡的組織力和動員力,恰恰說明在中國模式研究中,這是繞不開、躲不過、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把意識形態現象(中共作用豈止于意識形態?)作為客觀研究對象,與甘愿放棄獨立思考,寄居在僵硬意識形態窠臼之中,明顯是兩回事。那些拿了人家的錢,被人家洗了腦,操著人家的話語,屁股坐在人家的板凳上,回頭對中國唾沫四濺的人,才是真正應該鄙視的。
中共無異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但他的志趣與行動力又是超越意識形態,并不拘泥于意識形態的,其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國文化特色,其意識形態本身也在與時俱進。為中國人民謀福祉,即毛主席說的“為人民服務”,今天強調的“以人為本”,從來都是中共的理念。人們可以對自己不喜歡的中共的行為提出任何批評,但是中共在創建中國模式過程中不可替代的砥柱中流作用,明擺在那里,贏得了連對手都不得不承認。
中國共產黨,美國共和黨,日本自民黨,印度國大黨,英國工黨……同一個“黨”字,涵義大不同也,此黨非彼黨也。他國的“黨爭之黨”,“部分人之黨”,“意在分得一杯羹之黨”與中國共產黨基因不同,起根上就不是一回事。不僅所代表的群體不同,利益訴求不同,要干的事不同,能耐、紀律、扎根民眾引導民眾服務民眾的執政能力也大不同。
沒有這樣一個黨,中國模式不可想象,聚沙成塔絕無可能。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尚看不到任何組織有能力取而代之。
(未完,明天再續)2009-7-1
本黨,體制自信根據何在?
——司馬南在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年度學術研討會上演說中國模式
(接續昨天)
第一,集權為民是正道
歷史上存在過的幾種基本的權力模式,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山寨中國今天哪個模式都不是。恕我大膽,中國是獨特的“黨主立憲”、“集權為民”(“集權為民”的說法,河清先生一直在堅持)。 “黨主”“集權”的理念強調尊嚴、能力、責任“三位一體”,無例外地悉心服務全體人民。這個意思,官方的準確表述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
有人對此諱莫如深,怕有人聽到不高興;也有的人死活聽不懂,不認為這三條能統一起來;還有的人把這三條與美國政治模式一對照,立碼翻臉,翻臉的理由是不合洋人規矩。
一切均合洋人的規矩,也就沒有了中國模式。
須知洋人的規矩,也并不一律。英國非“三權分立”,美國非“多黨制”。
應當承認,實現三者的統一,確非易事。列寧有一個天才的創造,今天的人們已經不怎么提了。這個創造就叫民主集中制。集中制,當然不是民主制,民主制也不是集中制。天才地將兩個矛盾的東西捏合在一塊兒,機制的復雜性,使得應對和解決復雜問題成為可能。
當商量事情的時候,百無禁忌,但說無妨,知無不言,百家爭鳴,充分民主釋放出人民的聰明才智,為正確決策提供可能。當決定了要干事的時候,一旦形成決議,必須號令一致,政策統一,行動統一,任何人在行動中不得有任何反對的表示,這叫集中。毛主席認為民主集中制可以造成“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個人心情舒暢又有統一意志”的局面。作為黨內的規矩,建國前期的時候,中共黨內就這樣實行之,后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里,這個黨內的規矩又變成了全國人大,乃至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及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規矩。
第二,“人民革命”的倫理正當性
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有人會迅速抓住司馬南的說法,攻其不周延不邏輯。最為強悍的理由恐怕會是如何處理“假如集權無道”問題。其實,關于這個問題,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反反復復講過“人民會起來革命”,他老人家晚年念念不忘的“反修防修”也集中包含著同一意思。革命、造反,天下大亂,于是“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澤東語)。“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條也做不到,政不養民,不以人為本,少數人窮奢極欲,人民的不到社會變革的好處,人民造反是必然的。毛主席的說法,對“人民革命”的倫理正當性,重新給予了肯定,這是“為人民服務”這一最高理念的逆向表述,是“人民最高主權”、“人民最高主權不可分割”的毛氏版本。
新中國六十年里,對這個問題的探索從沒有停止過。“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是一種積極探索,“文革”是更大范圍內、整體意義上、試圖一攬子解決問題的一種積極探索。當然這種探索的代價大得驚人,某些結果令人心痛。但是,我們能因為探索出現失誤,連探索本身也一概否定嗎?沒有對探索失誤的“文革”的深刻總結,怎么會有后來的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撥亂反正?怎么會有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實踐?
毛主席當年告訴黃炎培,我們找到了“跳出周期律”的辦法,就是人民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我理解,現代中國法治背景下,“程序化造反”、“制度性造反”就是人民起來監督政府的具體行動,即在制度框架之下解決問題——包括最高領導權力和平交接,包括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等。這一大類正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制度辦法,是解決政府懶惰問題的基本手段,是人民民主的具體體現。
面對巨大體量國情復雜的現實社會,中國沒有簡單化地采取“以票為綱”競爭性票決方式處理問題,這種作法,被海內外一些勢力詬病為“不民主”“獨裁專制”,這種他們眼里的“不民主”和所謂“專制”的東西,正是中國模式應當特別加以總結的部分。嗡嗡嗡的叫聲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自己欠缺“文化自信”與“體制自信”(王紹光語)。我理解,體制自信的核心意思,就包括了堅持我們自己認為有效的、與中國發展相適應的、與洋人模式不盡相同的人民民主政治模式、權力模式。
第三,在西方批評家的挑剔目光下
60年,僅僅60年,中國人民過上了從沒有過的富裕的生活、中國人民見證了人民意愿之下的民主政治,中國人民有了與自己國家的地位和國力相應的大國民風范與民族意識。60年里,有人打我們,反被我們打敗了,至少打了個平手,打了個麻桿打狼——兩頭害怕;60年里,有人封鎖我們,想困死我們,我們部分地沖破了封鎖線,封鎖我們的人,反過來向我們借錢花;60年里,有人不停地妖魔化我們,尤其是妖魔化共產黨,但是,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共聚沙成塔的執政能力,不得不承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貧困的中國人今天過上了富裕、體面、有尊嚴的生活,不得不承認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是公認的世界經濟復蘇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不得不承認在這為期60年的世界各國無人缺席的漫長的馬拉松比賽中,被他們天天妖魔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居于令人驕傲和妒忌的位置,好過所謂民主的亞洲櫥窗,好過所謂人權的樣板國家,好過按芝加哥學派理論精心設計施工的轉型國家,尤其是好過實行“去共產黨化”一步到位休克死的前“第一世界”。
君不見,盡管西方批評家的挑剔目光不曾改變,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批評越來越集中于那幾個自己也不很有信心的名詞上,也就是說他們越來越集中于所謂理念,除了搗騰那幾個概念含含糊糊指責本黨不符合他們的所謂標準之外,對新鮮的多變的復雜的中國社會現實,尤其是經濟一體機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經濟發展現實,他們多采取滑稽的兩面態度:剛剛軟磨硬泡要你買他的國債,買他的飛機,買他的大型成套設備,轉眼工夫一變臉,就指責起中國的人權、自由、民主方面有問題,一點不害臊地把自己臉上的標簽當成 “普世價值”。
……
就說這么多了。
我帶來了一幅大字送給大會。
寄語“中國模式研討會”: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本固邦寧,民為邦本,
惠澤方海,峻節如山,
高文華國,穆行安人,
正德厚生,曰仁曰信,
圣王有道,乃質乃文,
唯此為大,喚我國魂”。
給大家稍作點解釋:討論中國模式,我們不能不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今天總結六十年,六十年背后是五千年。今天的人,橫看西方、學習西方都是必要的,但是豎看自己的歷史,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向古人學習也是必要的。學習人類一切優秀的東西,為中國模式的創建完善盡心竭力方為正道。這幅字具體內容的出處,從《尚書》到《周禮》,再到《中庸》,外加先王的句子,余下的是我自己瞎編的。送給大會主席潘維先生,謁勝忭賀,權作紀念。
任劍濤:司馬南先生的發言無比激情,中氣十足,而且具有煽動力,給人以新鮮感。我突然想到,如果中國模式需要一個民間的煽動領袖,那一定是非司馬兄莫屬。
司馬南:您不是第一個說我很適合“街頭政治秀”的臺灣模式、泰國模式、烏克蘭模式。
任劍濤:我們這一節最后一位發言人是新法家網站中英文版總編輯翟玉忠先生,有請。
翟玉忠:司馬,我告訴你,今天早上報紙上打擊山寨手機,“山寨中國”要受打擊的。
司馬南:昨天晚上我說了,好的山寨文化,原意的山寨文化才是我們要的,不好的我們剔除掉,不要了。
第四,普世價值,在爭什么?
河清:司馬南,你應該講一講關于普世價值,你寫的關于普世價值的文章引發了國內理論界的大討論……
司馬南:河清先生問關于普世價值的問題,我簡單地回應幾句。
幾年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國內某些媒體,大講普世價值,某些活躍的知識分子,也在以各種方式宣講普世價值。
開始,我并沒留意。及今年汶川地震發生《南方周末》的本報編輯部文章《汶川震痛,震出一個新中國》發表,我仔細研究一番才發現,他們言說的所謂普世價值,并非修辭之用的美麗辭藻,而是一種政治標準文化標準,開始若隱若現好似冰山一角,其實很有深意與來頭。
今年5月27日,我以“抗震救災是為普世價值嗎?”為題,寫了關于普世價值的第一篇文章,首發于新浪博客。我質問《南方周末》的評論家,“鬧了半天,十幾萬官兵的浴血奮戰,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援,那嘩嘩的眼淚,那井噴式的捐助,十三億人抗震救災的所有努力,居然不是中華民族古已有之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使然,不是政黨和軍隊“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不是“以人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觀的表達,也不是樸素的“愛的奉獻”,不是善良天性,不是悲憫之心……而是為了什么“兌現國家自己對于普世價值的承諾”,南報高論,豈非咄咄怪事?”“沒有普世價值,難道中國人民就不抗震救災了嗎?”
南方周末的編輯部文章并非只將地震與普世價值相聯系,文章點明了普世價值的主題:“只要國家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只要有這樣的底線共識,就會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國與全世界和解的倫理基礎。整個世界就都會向我們伸出援手,整個人類就都會跟我們休戚與共。我們就會與世界一起走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康莊大道。”
該報言下之意:吾國此前并非“以蒼生為念”,沒有“以國民生命權利為本”,這樣一個“底線”,及格分數線,吾國竟未達到!因為吾國連這個“底線”都沒有達到,所以,在國內,少數族群鬧分裂跟國家較勁,未能實現“民族和解”;在國外,某些國家跟中國較勁,未能實現“世界和解”。中國想實現“民族和解”與“世界和解”嗎?照照自己吧,由于你自身的原因,所以今天和解還沒門兒——沒有“倫理基礎”。
我順著《南方周末》意思,做了一點歸謬處理:
——啊,好家伙,鬧藏獨的人沒完沒了,原來責任不在分離主義勢力啊,不在有人出錢出力出軍師背后挑唆啊,某報意思,這是吾國責任,是吾國沒做到“以蒼生為念”“生命權利為本”,導致沒有“底線共識”;
——陳水扁之流搞“兩國論”,搞“入聯公投”,搞“去中國化”,也沒啥過錯,是吾國責任,導致沒達成“底線共識;
——今年五月,巴黎街頭舊金山街頭有人舉著雪山獅子旗發狠搶火炬,也不是人家的錯,也是吾國責任,導致與洋人沒達成“底線共識;
——“輪子神功”雇人敲鑼打鼓紐約街頭阻止華人為地震災區捐款,照理也不是輪子神漢有錯,而是吾國責任,導致沒達成“底線共識”;
——某國炸我使館,撞我飛機,刁難我遠洋貨船,詭稱我威脅他國,指控我人權不堪,以間諜罪陷華裔科學家于不義,收留一切反華垃圾人物,千萬枚導彈瞄準吾國,更是吾國責任……
吾國責任如此之多,大大出乎意料,不知世上還有什么責任不是吾國責任?
第五,政治氣功大師作法
無獨有偶,南方另外一家報紙,也是不遺余力鼓吹普世價值的。其社論《國家榮譽制度當奠基于人類普世價值》講到:“這種價值是必要的。就像諾貝爾和平獎,無論這個獎項頒給誰,它都會堅持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守衛人類和平的道義責任。”——那么頒給達賴喇嘛呢?提名東突分子熱比婭呢?是否普世價值依舊?倘社論回答依舊,社論立場在哪里?此種立場會“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嗎?會“促進人類和平”嗎?
當時本人對于普世價值問題的認識并不深刻,博文最后我表達了兩層意思:
第一,“普世價值”這玩意兒,不同人群、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下,均有不同的解讀,“真理從來都是具體的”(列寧語)。那種放之四海而皆準,并且由胳膊粗、力氣大、背景深的大佬及其小兄弟、代理人找上門來推行的“普世價值”,您最好離他遠點,久入鮑肆,不聞其臭!
第二,某報用“坐商形式”來兜售“普世價值”,不太合適。筆者早年畢業于商學院,略通為商之道。開辟市場必須抓典型,今曰“案例教學”,推廣“普世價值”的成功案例,近年莫過伊拉克國。過些日子,沒準兒伊朗也會被強行“普世”。所以,文章中,我誠懇建議《南方周末》諸公到伊拉克那一帶宣傳“普世價值”,一定特帶勁兒。最好帶上前幾天駐伊美軍用古蘭經當靶子實彈射擊彈無虛發的照片,伊拉克人民無論是什葉派,還是遜尼派,都會被你們感動,會熱烈歡迎你們的……
哈哈,我知道,博客里這種文章是打嘴仗用的,對于說服對方根本沒有用。
偏見再加上利益,兩股繩擰成一股,糾正起來,幾無可能。
但是,百萬之眾從這張報紙獲取信息閱讀評論,這張被一些人譽為“最敢講真話”的報紙的評論,其實他們的評論中經常在講假話忽悠讀者。這種“政治神功”的外氣發放,比之當年裝神弄鬼為特征的“異能神功”對社會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一鼓作氣,連寫了幾十篇文章,也到一些大學里研究機構做了相關的演講。
第六,美國《時代》周刊不藏藏掖掖
有人說得對,這場爭論其實學術含量并不高。
到底又沒有普世價值?什么是普世價值?怎樣認定普世價值?哪來的、誰的普世價值?共同人性是不是普世價值?這些問題當然都可以討論,司馬南并不是籠而統之地反對什么普世價值。某人說“愛是普世價值”;某人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普世價值;某人說“仁”是普世價值……都有一定的道理,本人無意也無趣置喙。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講過,語言具有深層結構,表面上人們看到的所表達的是一層意思,其實內里邊,所隱含的表達的是另外一層意思。阿慶嫂明白,這就是所謂“聽話聽聲,鑼鼓聽音”。
有人說“民主”是普世價值,“自由”是普世價值,“人權”是普世價值,“憲政”是普世價值……如此抽象地講普世價值也無妨,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擺出決戰的架勢針鋒相對。如果一定要我做出一點回應,我會建議:列位評論家,請問:何如將自由、人權、民主議題具體化?
比如民主,就抽象理念而言,你吼著說它是普世價值,我安然做我的俯臥撐;
你說它是最重要的生活倫理,我干脆自己出去打醬油。
但是,你說它是政治制度,并特指美國的政治制度,強制性地要中國必須向美國的政治標準、政治結構模式看齊,如果不看齊,就是不民主,你未免有點欺負人了;
當某報以“天下最敢說話”的架勢,將美國的政治制度描繪成是普世價值,并且每天以評論方式“敲打中國”、“格式化中國”“羞辱中國”,在道義上將中國置于不義地位的時候,當然就由不得你信口雌黃啦。
《南方周末》慣以隆禮厚金請某類學者戴著所謂“分析性學術概念”面具,上演“普世價值倮戲”,可是他們的鑼聲鼓聲不過三圈,就下意識變成了舶來的意識形態的宣傳,其評論員文章情感與信念的表達,常常建立在他們一貫的專門詛咒“黑暗專制”大語境之下。這與學術有什么關系?與“分析性學術”有什么關系?“分析性學術”沒有“分析”,“學術”又在哪里?
所以,當他們的評論員文章起勁地忽悠“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就是為了“踐行普世價值”的時候,讀者一點懸念都沒有地清楚他們的主張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按照他們的主張去踐行所謂“普世價值”,當然就沒有本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也便沒有了我們討論的中國模式。
可見,宣揚普世價值并不是什么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有著鮮明的政治目的“話語攝心計劃”,無非是用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按照西方的戰略意圖改造中國”,以期改變中國發展的方向道路。倘按他們的主張,我們今天的研討會完全沒有必要召開,因為早已經“文明終結”啦,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么中國模式。
我看不慣那些普世價值傳銷的文章發表之后,招來了一大堆國外的媒體記者叩門。BBC的記者采訪我,記者調門很高很兇,我反問他:英國的政治模式和美國的政治模式不一樣,英國是不是就沒有踐行普世價值呢?他支支吾吾好半天說不出來。
在這個并不復雜顯而易見的問題上,我們隊伍中的某些人沒有了主心骨,在人家“普世價值傳銷”攻勢下,已經魂不附體了。潘維先生講過,政治領導集團當中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出現判斷失誤,這是我們最擔心,最需要警惕的。
最近,一些人學捷克,鬧顯章運動,我著文表示反感。
昨天最新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一篇講中國的政治形勢的文章,專門提到司馬南博客:“中國專欄作家司馬南在自己的博客里,把《零八顯章》指稱為‘顏色革命宣言’”——《時代周刊》這句話說得不錯,這的確是我真實意愿的表達。不過,他們的“顏色革命宣言”不是第一次講了,借著這個機會也就再講一遍而已,沒啥新鮮的。
美國《時代》周刊關注司馬南博客,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普世價值作為《零八顯章》綱領,已經浮出水面,《南方周末》編輯部文章今后沒必要再藏藏掖掖了;第二,《時代》周刊在普世價值,亦即美國政治模式向中國輸出問題上,有著自己鮮明的立場。他們也認為這是一個關乎生死的獨門穴道,死盯著這個問題不放,所以才把我的這個點擊量并不高的博客文章搜出來加以傳播,我要謝謝他們。
謝謝會議主席。
(全文完)
(2009-7-2)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